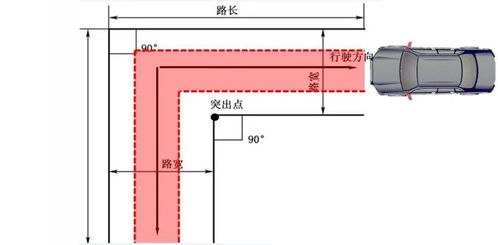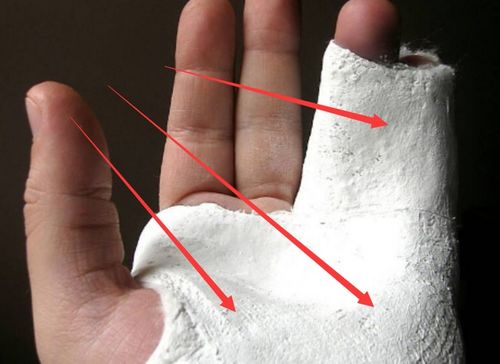一一归一 ——解读杨德昌电影《一 一》(最爱视听语言分析)
- 影视
- 2023-01-09 05:08:58
- -
一一归一。
这是在看完电影《一一》之后,我困顿思索的脑海中翻腾出来的第一句话。
“一”,这个笔画最简单的汉字,一如它简单通晓的含义,它可以是一朵云,也可以是一棵树,可以是一座山,也可以是一条河,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座坟……然而,像所有水滴石穿的典故一样,一——单薄却苍劲。
影片用历时约三个钟头的时间,讲述着一个并非故事的故事,它并没有如当下商业大片那样,要么惊天动地扣人心弦,要么缠绵悱恻撕心裂肺。《一一》摒弃了起伏激昂的宏大叙事,它没有戏剧化的故事波折,没有起承转合的情节,导演杨德昌携着《一一》继续在他的新写实主义道路上行走,并且渐行渐远。
与所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电影一样,《一一》展现的也是普通一家人的普通生活,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虽算不上富庶,却也与“上顿不知下顿”的苦难生活相差甚远,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世界上所有年龄阶段类型这里都有了。NJ——一个心中仍存有诗意的中年男人,在与世俗的碰撞中迷茫困惑;敏敏——并未如她的名字那样敏慧,围着儿子女儿老公老妈打转的的俗世中年妇女,突然某一天问自己:“我每天都在做什么?”;婆婆——在电影中一言未发的老太太,在岁月的磨蚀中蕴积了“看透”的智慧;婷婷——正值碧玉年华的纯情少女,美好天真纯粹,以为世界上除了好人就是坏人;洋洋——总是被女生欺负的小男孩,在电影中起着画龙点金的作用,喜欢用相机拍摄别人看不见或忽视的角落,用童稚的话语不经意间道出了人的永恒困境“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
我不能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来总结概括《一一》的故事梗概,因为把任何一个故事圈套强加给它都是对它的误读。诚然,只要有时间地点人物都必然会产生故事,而《一一》的伟大,不在于故事,或者说不在于一个中心故事,而在于多个散点无中心的故事浸透出的深层哲学意蕴。
杨德昌曾在一次访谈中解说过片名“一一”的含义:这部电影讲的单纯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个阶段,身为作者,我认为一切复杂的情节,说到底都是简单的。所以电影命名为《一一》,就是每一个的意思。 这意味着电影透过每一个家庭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具有代表性的年龄,描绘了生命的种种。
我想,在这部电影中杨德昌想表达的思想有点类似于庄子“齐万物以为一”,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的是非与差异。因此,智慧的婆婆曾经可能也如童稚的外孙洋洋一样,困惑于“人是否只知道事情的一部分?”,中年妈妈敏敏曾经可能也如纯洁的女儿婷婷一样,初恋在花季中开了又谢,洁净的心灵在时空行走中洒上了岁月的尘埃;被朋友誉为老实人的NJ曾经可能也如现在的小舅子阿弟一样在钱财利润欲海浮沉中哭笑交替满脑肥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我们所有的人或许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点上,从洋洋变为婷婷,从婷婷变为阿弟,从阿弟变为NJ,从NJ变为婆婆,从婆婆变为刚出生的小表弟,再从小表弟变为洋洋,循环轮回,生生不息。 这些看似精神形态各异的纵多人物,只是在人生各个不同的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或者说我们,其实最终都只是一个人,一一归一。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即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可就是不可,不可就是可。在宇宙时空无涯的荒野里,大小万物,生死轮回。与纵多表现此理的电影类似,《一一》开始于一场婚礼,结束于一场葬礼,开始于婴儿的出生,结束于老人的辞世。杨德昌的用意不言而明:电影就像人生,一生一死,即为一世。片长近三小时的《一一》仿佛是人的一辈子,电影中婆婆的一辈子刚刚结束,小表弟的一辈子则刚刚开始,而其他人——洋洋、婷婷、敏敏、NJ、阿弟、小燕、云云……他们的一辈子都正在进行中。
如果把每个人的一辈子都比作一辆公交车,那么我想这条公交线路一定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弧,无所谓起点与终点,无所谓开始与结束,恰如知名作家方方的某本小说的名字: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如果把这句话放在《一一》这部电影里,那么,此“我”便非彼“我”了,“我”,既是我,也是你,还是他,“我”作为一个能指,并非指具体的人,而是抽象意义上的万物。《一一》展示了这条公交线路,婆婆下车了,小表弟上车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开着他们各自的车,时而靠近,时而疏离,时而横眉冷对,时而招呼致意,并将会在一个个迥异且未知的站台先后一一下车,没有确定的秩序,没有确切的时间。最终,在生死轮回的这条线路上,所有的个体都一一归一。
除了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这几种共时的生命形态在人生的轨道上看似殊异却最终归一外,在历时层面,杨德昌还探讨了人的“活法”问题。
电影中NJ与敏敏这对可能不存在爱情的夫妻,因偶然的机会,脱离当前的现实,各自去过了一段新的生活,他们希望能逃离当前的窒息感。敏敏在其母亲成为植物人之后,发现每天对母亲讲的话都是同样的,一方面寡淡无味的生活毫无新意,另一方面人心的隔膜阻滞也使她无从说起,她困惑于生活的意义,于是寻求佛法,以为神灵能给予她答案,最终却发现“其实真的是没什么不一样,他们每天都要轮流给我讲同样的东西,每天都要重复好几遍,我觉得这一大堆(烦心事)……没那么复杂,哪有那么复杂”。有艺术情怀的NJ偶然重逢曾点燃他艺术火花的初恋情人,两人至今都旧情难忘,以为可以重来一次,终是无疾而终,他后来对敏敏坦白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以为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 或许他看透了人生的悲凉底色,看似涂着七彩的糖衣下是一层萧索的灰色,纵使是七彩,也一一归一 。
A one and a two ,这是《一一》的英文片名。杨德昌在一次访谈中说:“爵士乐手在即兴演奏前,总会低声数着‘a one and a two and a …… ’来定节奏,英文片名由此而来,表示片中内容并没有紧张、沉重、或者压迫感,生命的调子应该像一阕爵士乐曲。”
的确, 《一一》的美学韵味是清淡的 , 无论是它“一一归一”的主题,还是它纵多似乎静止的长镜头运用,像一杯氤氲着些许热气的清茶,不温不火,却在小酌之后,弥留一丝涩味在唇间,这一丝涩,会慢慢地、深深地流下去,从喉入心。
这是在看完电影《一一》之后,我困顿思索的脑海中翻腾出来的第一句话。
“一”,这个笔画最简单的汉字,一如它简单通晓的含义,它可以是一朵云,也可以是一棵树,可以是一座山,也可以是一条河,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座坟……然而,像所有水滴石穿的典故一样,一——单薄却苍劲。
影片用历时约三个钟头的时间,讲述着一个并非故事的故事,它并没有如当下商业大片那样,要么惊天动地扣人心弦,要么缠绵悱恻撕心裂肺。《一一》摒弃了起伏激昂的宏大叙事,它没有戏剧化的故事波折,没有起承转合的情节,导演杨德昌携着《一一》继续在他的新写实主义道路上行走,并且渐行渐远。
与所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电影一样,《一一》展现的也是普通一家人的普通生活,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虽算不上富庶,却也与“上顿不知下顿”的苦难生活相差甚远,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世界上所有年龄阶段类型这里都有了。NJ——一个心中仍存有诗意的中年男人,在与世俗的碰撞中迷茫困惑;敏敏——并未如她的名字那样敏慧,围着儿子女儿老公老妈打转的的俗世中年妇女,突然某一天问自己:“我每天都在做什么?”;婆婆——在电影中一言未发的老太太,在岁月的磨蚀中蕴积了“看透”的智慧;婷婷——正值碧玉年华的纯情少女,美好天真纯粹,以为世界上除了好人就是坏人;洋洋——总是被女生欺负的小男孩,在电影中起着画龙点金的作用,喜欢用相机拍摄别人看不见或忽视的角落,用童稚的话语不经意间道出了人的永恒困境“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
我不能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来总结概括《一一》的故事梗概,因为把任何一个故事圈套强加给它都是对它的误读。诚然,只要有时间地点人物都必然会产生故事,而《一一》的伟大,不在于故事,或者说不在于一个中心故事,而在于多个散点无中心的故事浸透出的深层哲学意蕴。
杨德昌曾在一次访谈中解说过片名“一一”的含义:这部电影讲的单纯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个阶段,身为作者,我认为一切复杂的情节,说到底都是简单的。所以电影命名为《一一》,就是每一个的意思。 这意味着电影透过每一个家庭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具有代表性的年龄,描绘了生命的种种。
我想,在这部电影中杨德昌想表达的思想有点类似于庄子“齐万物以为一”,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的是非与差异。因此,智慧的婆婆曾经可能也如童稚的外孙洋洋一样,困惑于“人是否只知道事情的一部分?”,中年妈妈敏敏曾经可能也如纯洁的女儿婷婷一样,初恋在花季中开了又谢,洁净的心灵在时空行走中洒上了岁月的尘埃;被朋友誉为老实人的NJ曾经可能也如现在的小舅子阿弟一样在钱财利润欲海浮沉中哭笑交替满脑肥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我们所有的人或许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点上,从洋洋变为婷婷,从婷婷变为阿弟,从阿弟变为NJ,从NJ变为婆婆,从婆婆变为刚出生的小表弟,再从小表弟变为洋洋,循环轮回,生生不息。 这些看似精神形态各异的纵多人物,只是在人生各个不同的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或者说我们,其实最终都只是一个人,一一归一。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即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可就是不可,不可就是可。在宇宙时空无涯的荒野里,大小万物,生死轮回。与纵多表现此理的电影类似,《一一》开始于一场婚礼,结束于一场葬礼,开始于婴儿的出生,结束于老人的辞世。杨德昌的用意不言而明:电影就像人生,一生一死,即为一世。片长近三小时的《一一》仿佛是人的一辈子,电影中婆婆的一辈子刚刚结束,小表弟的一辈子则刚刚开始,而其他人——洋洋、婷婷、敏敏、NJ、阿弟、小燕、云云……他们的一辈子都正在进行中。
如果把每个人的一辈子都比作一辆公交车,那么我想这条公交线路一定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弧,无所谓起点与终点,无所谓开始与结束,恰如知名作家方方的某本小说的名字: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如果把这句话放在《一一》这部电影里,那么,此“我”便非彼“我”了,“我”,既是我,也是你,还是他,“我”作为一个能指,并非指具体的人,而是抽象意义上的万物。《一一》展示了这条公交线路,婆婆下车了,小表弟上车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开着他们各自的车,时而靠近,时而疏离,时而横眉冷对,时而招呼致意,并将会在一个个迥异且未知的站台先后一一下车,没有确定的秩序,没有确切的时间。最终,在生死轮回的这条线路上,所有的个体都一一归一。
除了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这几种共时的生命形态在人生的轨道上看似殊异却最终归一外,在历时层面,杨德昌还探讨了人的“活法”问题。
电影中NJ与敏敏这对可能不存在爱情的夫妻,因偶然的机会,脱离当前的现实,各自去过了一段新的生活,他们希望能逃离当前的窒息感。敏敏在其母亲成为植物人之后,发现每天对母亲讲的话都是同样的,一方面寡淡无味的生活毫无新意,另一方面人心的隔膜阻滞也使她无从说起,她困惑于生活的意义,于是寻求佛法,以为神灵能给予她答案,最终却发现“其实真的是没什么不一样,他们每天都要轮流给我讲同样的东西,每天都要重复好几遍,我觉得这一大堆(烦心事)……没那么复杂,哪有那么复杂”。有艺术情怀的NJ偶然重逢曾点燃他艺术火花的初恋情人,两人至今都旧情难忘,以为可以重来一次,终是无疾而终,他后来对敏敏坦白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以为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 或许他看透了人生的悲凉底色,看似涂着七彩的糖衣下是一层萧索的灰色,纵使是七彩,也一一归一 。
A one and a two ,这是《一一》的英文片名。杨德昌在一次访谈中说:“爵士乐手在即兴演奏前,总会低声数着‘a one and a two and a …… ’来定节奏,英文片名由此而来,表示片中内容并没有紧张、沉重、或者压迫感,生命的调子应该像一阕爵士乐曲。”
的确, 《一一》的美学韵味是清淡的 , 无论是它“一一归一”的主题,还是它纵多似乎静止的长镜头运用,像一杯氤氲着些许热气的清茶,不温不火,却在小酌之后,弥留一丝涩味在唇间,这一丝涩,会慢慢地、深深地流下去,从喉入心。
本文由作者笔名:影视达人17 于 2023-01-09 05:08:58发表在本站,原创文章,禁止转载,文章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本文链接:https://www.e-8.com.cn/ys-53510.html
 影视达人17
影视达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