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眼睛 Cerrar los ojos(2023)

又名: Close Your Eyes / 告别的凝视(港) / 双眼之间(台)
导演: 维克多·艾里斯
主演: 何塞·科罗纳多 安娜·托伦特 玛利亚·莱昂 索蕾达·维拉米尔 希内斯·加西亚·米连 曼诺罗·索洛 乔瑟普·马利亚·波乌 马里奥·帕尔多 佩特拉·马丁内斯 胡安·马加略 Helena Miquel Fernando Ustarroz
类型: 剧情
上映日期: 2023-05-22(戛纳电影节) 2023-09-29(西班牙)
片长: 169分钟 IMDb: tt21284358 豆瓣评分:7.5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著名西班牙演员胡里奥·阿雷纳斯在拍摄电影时失踪了。虽然他的尸体从未被发现,但警方认为他在海边溺水身亡。多年后,胡里奥的失踪之谜因一档电视节目被重新带入聚光灯下,该节目概述了他的生活和死亡,并展示了他最后拍摄场景的独家图片。这些图片是由他的挚友,也是该片导演米格尔·加雷拍摄的。
演员:
影评:
原文首次发表于Published in Cinema Scope #95 (Summer 2023).
作者:Lawrence Garcia
翻译:雕刻时光
《闭上眼睛》是维克多·艾里斯(Víctor Erice)自三十多年前的《榅桲树阳光》(1992年)以来的首部影片,于戛纳电影节首映。然而,影片首映后立即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议。在影片放映时引人注目的是艾里斯的缺席,他在《El País》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解释了自己抵制该电影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福茂(Thierry Frémaux)及其策展团队对他的影片被列入首映单元而不是主竞赛单元的做法缺乏沟通,暗示着缺乏尊重。电影节的官方回应对艾里斯的指控表示惊讶,但这些细节值得回顾——并非因为它们可能会对艾里斯的遗产产生丝毫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与他电影实际关注的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如预料的那样,由于《蜂巢幽灵》(1973年)演员安娜·托伦特(Ana Torrent)在其中扮演一个配角,所以《闭上眼睛》是一部深深关注过去的电影,关注影片周围积累的各种实质性事实:制作细节、演员传记,还有首映地位。然而,艾里斯关心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更关心把过去转化为历史的那种视角(用黑格尔的著名短语来说)。
《闭上眼睛》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不久,地点是一个被称为“The Sad King”(“悲伤的国王”)的法国庄园,一位富有的西班牙犹太难民和他忠诚的中国仆人一同居住。这位男子接待了一位来访者,一个满脸皱纹的西班牙反对佛朗哥者,他雇佣这位来访者去寻找他那半中国血统的女儿乔舒。女孩在中国某处迷失了踪影,只能通过一张照片和她能否表演她母亲教给她的一个戏剧动作——“上海手势”——来确认身份。这位男子的唯一愿望是在自己临终之际再次见到她。在一番考虑后,这位来访者接受了这个任务。

影片的开头情节在其时代再现方面非常吸引人,在叙事细节上也极具吸引力,当一段旁白介入时,它让人感到震惊:我们其实一直在看一个名为《告别的凝视》的未完成电影的第一卷。这部影片在90年代初被搁置,因为主演胡里奥·阿雷纳斯(José Coronado)突然在神秘而至今未解的情况下消失了。现在是2012年,曾是《告别的凝视》导演和阿雷纳斯最亲密的朋友米格尔·加拉伊(Manolo Solo)生活在靠近海岸的一处简陋拖车公寓里,钓鱼、照料番茄园,并以一位名气不大的小说家为生,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拍过一卷胶片。然而,当他同意参加关于阿雷纳斯神秘失踪的电视节目时,米格尔开始寻找失去的时光。他去了一个旧的储藏室,那里放置着多年的电影制作材料;他拜访了他的老编辑和朋友马克斯(Mario Pardo),现在是一个胶片档案管理员,他一直保留着《告别的凝视》的开头和结尾;他还寻找他的前情人,一位名叫洛拉(Soledad Villamil)的歌手,她因阿雷纳斯而离开了他。
这些相遇或许看起来是对电影开头所承诺的异国之旅的可怜替代品——或许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受骗,好像被拒绝了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失落杰作,也许是奥逊·威尔斯的《不朽故事》(1968年)的重现姊妹篇。然而,正是在这些外表平淡无奇的场景中,《闭上眼睛》累积了它的力量。米格尔在某个时候将《告别的凝视》描述为“一部经典的冒险故事”;通过《闭上眼睛》,艾里斯有效地探讨了在当下是否还可能制作这样的电影而不陷入时代错乱。当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让人想起例如雅克·特纳的《东印度群岛上的安妮》(1951年)、弗里茨·朗的《慕理小镇》(1955年),或者任何一个人偏爱的电影历史参照点时,当代的冒险电影是否注定要成为一个反思性的进入档案的旅程?

这些问题贯穿整部电影长达169分钟的时间,但当米格尔与邻居闲聊的场景突然过渡到《赤胆屠龙》(1959年)中“我的枪、我的小马和我”的美妙演绎时,这些问题显得特别切中要害。尽管这个场景直接的怀旧吸引力在戛纳电影节上引发了一阵自发掌声,但让它超越卖弄电影知识的引用的是艾里斯对这种怀旧所带来的艺术负担的理解。在猜测他朋友消失背后的原因时,米格尔评论说胡里奥“无法应对这个至高问题:变老”。对于艾里斯来说,至高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一个老龄化的艺术形式——在这种媒介已经获得某种历史性的情况下如何拍摄电影。
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一幕中,米格尔将胡里奥消失的那个晚上想象成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一辆车,车灯亮起,被黑暗吞噬;一个人在悬崖峭壁上栖息;一双湿漉漉的靴子在崎岖的岩石旁边。这一段不是因为其叙事内容而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它的节奏和剪辑方式与米格尔所崇拜的经典作品,或者他自己的《告别的凝视》有多么不同。事实上,当米格尔发现一本描述卢米埃尔《火车进站》(1896年)的小翻页书时,人们或许会想知道上述场景对早期观众的影响。尽管有一群批评家声称艺术既不进步也不演变,但如果我们能够提出电影“进步”的概念,那么这是因为这个媒介已经获得了一种记忆和历史。如果我们谈论电影观看方式的真正改变,那是因为观看现在伴随着记忆的责任。
记忆的问题在《闭上眼睛》的最后阶段得到明确呈现,阿雷纳斯被发现在一家老人院里,他在那里做着杂活,换取食物和住宿,保留着身体能力但失去了记忆和身份。由于他喜欢唱探戈而被院中的修女们昵称为“加尔德尔”,他有着过去,但没有历史。米格尔试图拜访他的朋友以唤起他的记忆,阿雷纳斯的女儿安娜(托伦特饰演),但他们都无法从他那里唤起任何认知的闪光。然而,我们得知阿雷纳斯仍然保存着一张来自《告别的凝视》拍摄时期的乔舒的照片。他显然无法区分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他已经失去了两者的感知。(在这方面,托伦特在影片中的出现不仅仅是装饰性的:《蜂巢幽灵》展示了一个仍在学习如何区分艺术与生活的小女孩,而《闭上眼睛》展示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男人。)
为了最后一次试图恢复阿雷纳斯的记忆,米格尔决定让他看《告别的凝视》的结尾。显然,他期望有类似奇迹般的事情发生——尽管,正如一个朋友提醒他的那样,“自从德雷耶逝世以来,电影中就不存在奇迹了。”可以肯定的是,《闭上眼睛》的结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也没有类似《词语》(1955年)那样的神圣结局,只有在黑暗的剧院里的特写镜头。但尽管这个结尾不像奇迹一般,却是对电影历史的一堂课,同样也是深刻动人的。胡里奥·阿雷纳斯的奇特案例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的生活可能与电影紧密相连,但这个媒介有一个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无法归纳的历史。实际上,或许只有通过认识到这种区别,电影才能成为我们所说的艺术——它的影像才能超越简简单单的影像,拥有世界的厚重。

这部影片在戛纳首映时,尽管其中的一些直接怀旧的场景引发了现场观众的欢呼,但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超越了对电影知识的追捧。它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时代在变迁,电影艺术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和记忆?艾里斯在影片中将这些挣扎植入故事,展示了电影艺术与时间之间的纠葛。
整部电影围绕着寻找失去的时光、回忆以及随时间而逝的经历展开。它通过故事中的角色和情节,深刻探讨了记忆、历史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媒介如何在这些元素之间发挥作用。在展示了角色因失去记忆而失去自我认知的情境中,《闭上眼睛》呈现了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关于时间和艺术变迁的沉思。
以上是对这部电影的大致解读,它呈现了艾里斯在作品中探索的复杂而富有哲理的主题。
通常来说,一部电影以使命的完成或多年遗憾终于夙愿作为落脚点,总是伴随着一段近似于类型化的,猛烈磅礴的高潮。在瘦高老人踏入电影院,银幕的光反射在他迟钝的脸上时,我想这个场景应该也符合这样的定义,对他的救赎,或者说对他的救赎这种尝试本身,本应当在情感上具有相当的感化力。不过,如果只简单地看它在基础叙事层面所实现的,不论是故事的完成方式,还是突出的扣题意识,我会觉得它在情感表达上显得有些迟钝、老态,有一种要素都齐全了但是表达不够充分的感觉,至少肯定没有形成类型化的,猛烈磅礴的高潮。但在此之上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体验,刚看完电影的时候只从结构上做了最基本的认识,这些天来一直在思考。
主要谈一谈它的形态。从阿巴斯开始,观众们对电影内创作电影从而指涉电影本身的结构应该都见怪不怪了。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部电影最核心的概念,就在于将片中片里的开头和结尾作为电影本身的开头和结尾。概念本身是非常清晰的,关键在于我们从怎样的角度去理解它。
简单地,把电影的基础叙事称为外层,把电影内的电影片段称为内层。不可否认的是,当电影的外层呈现出更为平和、自然的形态,在其中构建一层更为戏剧化、抽象化的内层,会增强外层的所谓“真实性”,就像将一件黑色衣服放在灰色衣服旁边。观众的共情中枢也会随之移动到外层,在《闭上眼睛》中,这一部分似乎承载不起观众对“真实性”的需求,将它作为更现实的一层去观察,简单地看由戏中戏向外的延伸,基本上没有更复杂的体验,“一个老头失忆了,看了一部他演过的电影,导演想让我们感动,哦就这样了”。这可能会是前一段所提到的“迟钝、老态、表达不够充分”的观感的形成原因(之一)。《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实际上也是内层。
在影片的推进过程中,要让观众认识到基础叙事同样有站到外部去观察的必要性,通常需要一些更外部的指涉,关于电影本体或者关于现实身份,也就是短评中所提到的,要形成关于“电影之所以为电影”的思考,回头想想,我写过的大部分长评都是关于此的,提几个例子和方式。《拜访小屋》《魔盒》都是由内向外,从方法的共性上对外部导演的自指产生联想,《驾驶我的车》将基础叙事层面的空间和动作抽象化并赋予额外意义,向内形成更丰富的层次。这些电影结构的融合程度比较高,没有《闭》中素材介质的分野。关于这一点,短评区有条一针见血的中差评,“为了这碟醋包这顿饺子”。从这点出发去讨论,一定要提及《小说家的电影》。洪为一段现实中偶然拍下的vlog重新创作一整部电影,并让它成为作品内的作品,将完全外层的现实素材置于“虚构”的位置,同时让《小》充分利用自己在现实中广为人知的情感关系在感性上发力,非常完美的构想。整体想下来,对电影基础叙事进行整体抽象的方式,不外乎以上几种形式及其变体。
当然了,《闭》中的片中片并不是什么现实素材,应该也不是某部老电影的片段(未考证)。艾里斯作为隐世导演,观众对他一无所知,虽然片中的导演角色有一定的自指属性,但也仍距离遥远,不可能形成什么关乎现实的共鸣。假使有一部分观众(至少包括我)自认为看到了《闭》基础叙事的抽象化,如前面所说,它缺少从素材或方法上实现导演自指的可行性,那么可能性就只剩下近似于《驾》的内部方案。
回到电影本身,“为了这碟醋包这顿饺子”,从电影开始讲述故事的那一天起,观众走进电影院期待的就一定是《闭上眼睛》中这样的开头和结尾,明确且锋利的剧情节点,男二(真正的男主)也有着一个明确且锋利的个人形象(与之对应的,钝感的基础叙事和人物形象)。这样的戏剧性和锋利感,为《闭上眼睛》的结构带来了无穷的可能。我们当然可以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从它的虚构属性出发,将自己的共情中枢调整至外层。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角色的完成度出发,拥抱片中片作为基础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看过太多《绿野仙踪》《E.T.外星人》《纳尼亚传奇》《超级八》一样的电影,体验过无数次由现实向虚构投射的探秘之旅,每一位接受任务的主角都要历经磨难,最终完成使命,认识了世界的美好。而这一次,艾里斯带给我们的,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反向旅程,我们由虚构进入现实,但对谜底的探索精神,对爱和生活的向往没有变。
这或许可以解答片中的另一个谜,为什么第二个片段一直不被导演允许播放。无论如何,男主历经了三十年的磨难,甚至像《黑暗之心》一般自我迷失,最终还是将女儿带回了爸爸身边,履行了受托的使命。我想我有理由为此而感动。
但它还有着更为理性的另一面。当我们把两层结构并行起来思考,既然在电影内是一位演员履行了他的使命,那么其实,它终归也只是一位演员履行了他的使命。只有理解了这一点,电影才有必要在最后再回到外层的角色。他的闭上眼睛,是基础叙事的扣题,也是电影主旨的落脚点。这或许是电影节的意义所在,当灯光亮起,演员们站到台前向大家致意,想必电影的外部性也会因此不同。
##LFF #Create 伦影节第二十二场,目前最佳。一部讲述时间的电影,而电影也恰恰是时间的“游戏”。开场和结尾出现的两面雕像是罗马神话中的时间之神雅努斯,一面看向过去,一面看向未来,是开始也是结束,我们仿佛被拉进时间的洪流中,感受着由导演构筑起的时间漩涡。究竟是现实映照了电影,还是电影引导了现实。
剧情上,刚看开场非常担心这种烂俗的剧情会无法有一个好的收尾,但看到拿出胶片灯光熄灭那刻我悬着的心也才放下,感慨导演果真不会让人失望。最精彩的就是这个结尾了,以时间串起了所有的记忆元素,火车进站的小本,关停的影院,电影海报,胶片,放映机,钢琴曲,双人对唱记忆中的歌曲和绳结等。影片戏内外与观众三方的对照明显,QiaoShu听着钢琴曲,Gardel看着电影,而观众也看着电影,QiaoShu唱个歌谣,Gardel也跟Miguel唱着歌,而在你心中是否有想到什么?
视觉上,大量的固定镜头和摇镜头,缓慢拉近很多,像是对角色内心的一种侵入,最喜欢的镜头是脸部特写镜头,出现的时候不多,但每场都极为重要,角色对于形而上的探讨都似乎在次镜头下。结尾处还有一场手持的前跟镜头,把他内心的起伏表现的很好。光影上户外的自然光一般,但是室内的光影做的太好了。还有结尾处幕布的光线反射到角色的脸上,那一幕也同样映射了坐在影院中的我们,我们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切。
听觉上,开场的钢琴曲非常轻盈,后期的“悬疑”部分的弦乐也处理得很好,在到后期由于元素多了,也采用了交响乐,而到结尾时则是舍弃了华丽,以较朴素的形式呈现。整体台词效果很棒,就这样导演在开场还给大家在Intro道了个歉。
今年看了两部最喜欢的片子都是在这个破影厅…真的是闹心。顶上的灯真的就不能控制关掉吗?
 Victor做Intro
Victor做Int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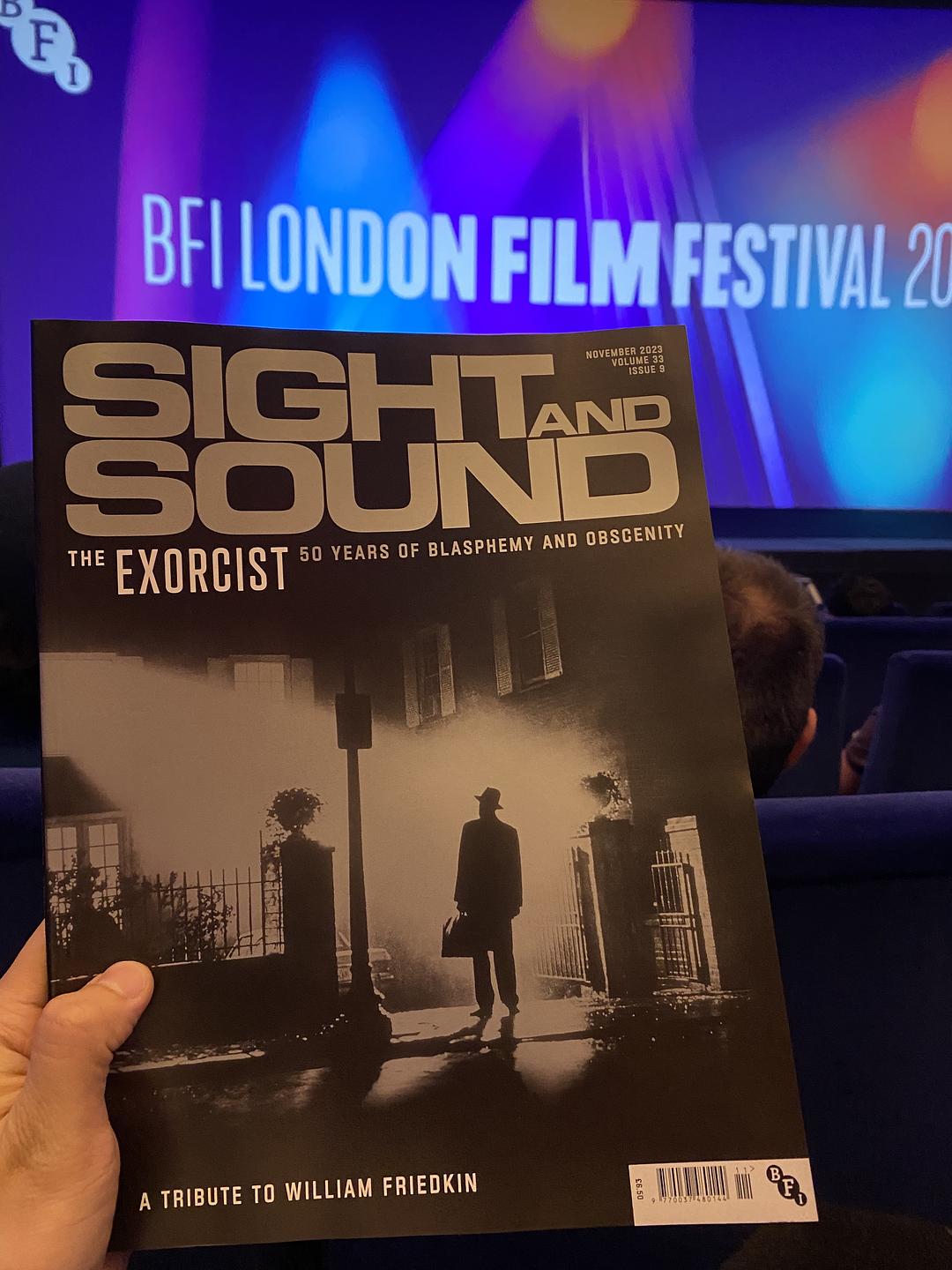 豪横……全部免费发
豪横……全部免费发电影已是行将就木的艺术,我们也无法换个地方重启人生——枯萎与虚空,唯有尽力面对。情感,在胶片的最后一格存蓄,回望打开了整篇河流,已是告别之时。凝视,永恒的瞬间,再次凝视。
德莱叶死后电影就没有了奇迹,可是主人公仍然想放映残片,唤醒昔日的好友(无异于制造一场医学传奇)它承载了艺术家的人生记忆。电影讲述具体的创作者,自我的故事。人没有永恒,更不存在神迹。
“主角是‘电影’”吗?也不是那位昔日的演员。我更认为导演米格尔是第一主角,或许同胡里奥一起,是某个艺术家(双重的)投射:苟活于人间市井,或中途易辙——随一种更本质的活着去存在。
米格尔在人生仓库中选择,丢弃,重蹈生活。蓦然回首的一本签名书,旧衣旧物,相片和一只手表……过往的所有,通过一次采访被重新发现,使用,怀念。这一次,将一些东西扔进垃圾桶,又把另一些装进了背包。某次的当下,我们都会体悟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哪些则不是。
而正有无数次的,对抚慰生命的选择,重新选择,组成了他的生活轨迹。来到海边,在每个阶段带着不同又相似的感受,进行着本质的呼吸,弹琴,出海,睡觉。
胡里奥的演员生涯在一场球赛终结,丢下皮鞋,拿着香烟,在生命后一半来到另外的轨道。即使抛却感情,朴素活着,仍也带了剧组的旧照——人生前段的临时特征。他意外或有意地抹掉了情感记忆与生平所有,又简化地重复世人的一切,吃饭,劳作,睡觉。
缅怀友情,探访旧友,回首过去只是自我安慰。惨淡经营的生活需要一次意义的赋予,需要意外来填充生活,通过影像的介质,通过艺术。更可能的是,一场临时发现,从好奇心到平常心——不同的生活没有更多的不同。最少环节的生存步骤,实际上他们在过一样的生活,只是在哪次硬币的瞬间,不同倾向性的决定。
如果没有结尾的放映,形式还不会完整,但关于人生主题的表达,在养老院就已经结束了。
整部电影可见的美的呈现,从手电筒,篝火,到任何一处的光与影。更重要的,这只影片用最简朴的方式、平实的语言漫过生命,细微地讲解每一段有着汹涌力量、又实际平淡的故事。
球门与银幕,重叠了一个中点与另一个中点。可前后仍是开端到结束,从首至尾,不管是一条胶片,一笔河流。生命在其间次序流动,留下磨灭之前的一点痕迹。
唯有一瞬,可以光速穿过一切,直抵(人的)灵魂与所有——转身,直视的目光。
确实就像一个牛仔,梦间的峡谷中紫色的光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