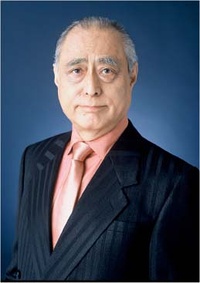疯狂的果实 狂った果実(1956)
简介:
- 泷岛家的两兄弟年龄相仿,性格迥异。哥哥夏久(石原裕次郎 饰)风流倜傥,浪荡不羁;弟弟春次(津川雅彦 饰)则温柔腼腆,内向老实。某日,兄弟俩乘火车前往逗子度假,出站时遇见了美丽的少女天草惠梨(北原三枝 饰),春次登时为其所倾倒。不久,他们在乘船出海时再次邂逅游泳的惠梨,三个年轻人相谈甚欢,春次最终鼓起勇气邀请女孩参加他们的舞会。惠梨曼妙的舞姿成为当晚的亮点,所有男孩都目瞪口呆,连夏久也心有所动。又一天,夏久和一众好友在俱乐部歌舞时,看见惠梨和外国人翩翩起舞。张扬跋扈的他强吻惠梨,两人纠缠在一起。从此,泷岛兄弟和同一女孩的关系变得愈加微妙……
演员:
影评:
- 从日本战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引发的社会心理来读解这部片。。
重读《疯狂的果实》,富裕社会的旖旎幻影
a、“太阳族”享乐放荡的土壤
自从明治维新,日本进入近现代化的进程之后,因20世纪中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归于失败而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战前极端天皇国家主义随着战败而彻底崩催。旧体制被摧毁,新体制起而代之。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国家主权和政治遇到挫折的十年;也是经济在美国扶植下突飞猛进的十年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在日本社会政治领域“反核和平运动”的全民化和“55年体制 ”(“55年体制”,指的是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一般认为该体制结束于1993年。 百度百科)形成,时代转换的另一个标志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温饱已不成问题,奢侈品消费开始流行。而1956年盛行于日本文化思想界的“战后时期终结论”开始,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日本同时步入大众化社会。而“太阳族”电影集中崭露头角的56年是相对特殊的一个时间段里的特殊时间点。日本不同于刚刚战败后的断壁残垣,又尚未达到富裕社会的程度,加倍的彷徨、迷茫和美好的幻想得以并存。
如果说“太阳族”外显的放肆的浪漫是极为私人的体验,那么其背后经济底气则是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如《疯狂的果实》那般充满想象力、多姿多彩的描绘着的理想中的生存状态,侧面映照的其实是一代人情绪上的逃避——即极端排斥即将要进入的被规训的、无自由的正统经济体制,成为社会大机器里无情链条上的一个咬合的齿轮(类似于增村保造在《巨人和玩具》里所展示的那种忙碌而冷漠的成熟商品社会里麻木的个体)。而这种逃避的前提则是新的宗法体制的完善化,市场机制的成熟化,物质生活充裕化。反观岩崎昶所说50年代“日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的实际感及其反面的经济上的安定感”,使一部分人产生了“天下太平”的心理,而另一部分人则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太阳族心理”,即“从对一切进行反抗到全面加以否定,急躁的乱闯一阵。” 而我则认为,“太阳族心理”本质上就是根源于“安逸心理”,两者实质上并无区别。影片中自恋、自怜、扭曲、沉溺于舞会与性的年轻人,恰恰与现实中野心勃勃等待着进入新兴资本社会市场的年轻人的健康积极形象成鲜明对比。正是那些在严格社会阶梯上攀爬的新生年轻群体在狂热追捧太阳族,与其说是为了用那种放荡方式生活,不如说是为了在荧幕上观看一种重建的纯真梦幻的神话。而“太阳族”所勾勒的广博到可以任意漂流和享乐的“海域”,恰恰是他们高压下所追寻的乌托邦式的避风港。
在另一方面,成人世界的“伪善和保守”,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停滞和腐败”,让很多在现实中受挫的人,在精神上渴求于成为现代社会的“零余者”,即那些现实社会中可有可无的人,遂“把自己本身的不满和反抗和这些影片中所表现的不满和盲目的反抗结合在一起了”,是对高度体制化的表示抗拒的一种形式。同时说明这些作品并非只是一味的低劣和颓废,还有更多微妙的“正统”价值观。比如《疯狂的果实》里的主角春次,瞧不起哥哥夏久等一伙人游手好闲的生活,说要更有理想的努力生活,还引发了别墅内一场风格化、政治性的群体辩论(通过面部特写的交互剪接,众人喋喋不休的说着反政府、反社会的言论) ,但是事实上,春次游离在出海、滑浪、舞会中的生活依然是奢侈享乐的,并且最后他还在惊人的狂怒下撞死了自己的女友和哥哥,更显露出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人物设计。换言之,春次是一种极易于普通青年自我带入的角色—— 一方面满怀理想、勤奋学业或工作、不忤逆长辈、纯情正义;另一方面,则轻易就被带入一种奢靡放荡的生活并深陷其中,随之爆发出超常的颓废病态情绪,干出惊世骇俗之恶事。在其中更为隐喻的意味则是,每一个正常的年轻人都是潜在的犯罪者,而促使之犯罪的理由可能只是一种占有的欲望。而战后日本社会“物质”和“欲望”正是交互产生、并持续膨胀,其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深深的渗入到“太阳族”叙事内部,不妨称其为“太阳族”享乐放荡的土壤。若分析这种土壤产生的根源,并放置于更宽广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中去看,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三方面。
第一是大众生活的逐渐富裕,社会环境和平安逸。脱离了战后的食不果腹、忍饥挨饿的苦难生活,以及社会生活在政治军事环境高压下的恐慌。日本经济起步实际上的起始点是20世纪50年代初,确切的说是朝鲜战争给予的“天赐之机”——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作为美国军备在亚洲的生产供给基地,绝大多数产业部门都受到战争“特需”的刺激,且短短3年日本大赚了23亿美元。从1913年到195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左右,而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就以9%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王德文、蔡昉 )。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日本,经济极端贫困并且在战后非常依赖于美国。收入分配、教育、健康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直到50年代才有所上升。从1955年开始,日本就拉开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幕。1956年,日本在《经济白皮书》中宣布:“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战后的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今后则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时期。当时日本人的心情一点儿也不亚于决心打一场“蓄意的、认真的和无情的经济战争”([美]米尔顿.艾兹拉蒂著《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 新华出版社 2003年 沈建译)。 后来,经历了1956到1957年的“神武景气”,以及1958年6月到1961年12月的“岩户景气”两次高速发展以后,整个6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更是可以用“风驰电掣”来形容。
第二点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外来文化的融合,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西式生活的渗入,由舞会、敞篷车、帆船冲浪、手提收音机、洋装、爵士乐、混血儿的花花公子和美国人丈夫等具体的实相,呈现出一个西方化乃至世界化的日本海域风情。可以说正是日本战后受到欧美文化的强烈冲击,各种西方文化思潮铺天盖地而来,制片厂专门针对年轻的一代的趣味而描摹出的新的生活图景。我个人就觉得《疯狂的果实》里不仅仅对西方文明的物质方面细心的描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人一直相当注意对西方物质器具的追赶),而在西方式的 “人性、人格和个性”方面也做到了一定的自我否认和竭力模仿的程度。比如狂放、纵欲、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角色性格(以夏久等人的性格最为显豁)的西方化特征,这种模仿让他们从国族身份不断游移而引发出焦虑中获得了一定的解脱,一个在西方世界怀抱中的东方民族不用去记忆自己自身的东方属性,是无比轻松且又脆弱虚幻的南柯一梦。如果说《处刑的房间》是集中承载了所有贫穷和压抑社会负面情绪,那么《疯狂的果实》则以反转的姿态刻画了真空状态下的奢侈、自大、富裕之余可尽情纵欲的大众想象。
最后一点,则是政治上的嬗变,一个自由新世界的出现。自从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革命成功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日]丸山真男《日本的国家主义——其思想的背景和展望》 ),到“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像污迹一般在地图上蔓延开来,国民就一直在“一亿一心”国家主义的监控下被严格管制,既没有生命保障更没有表达自由。战败后又遭到美国占领军的“殖民化”控制,丧失主权和自我(占领期内,日本被美国人强加于一套傲慢自大、西方中心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占领即将结束后,却又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给日本强制军备与扶植右翼拉拢其为冷战伙伴)。以1948年的时间为界限,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从“激进”的改革时期进入了“动摇倒退”的时期 。直到55年,民众情绪和民众意志才得以空前广泛的自由表达,则一开口抒发就是“太阳族”这般夹杂着扭曲暴戾和恬美幻想的作品。同时,在1955年,因为经济复兴和朝鲜战争而苏醒过来的日本财界和各大企业,为求政局安定,在背后对保守联合势力施加强大的压力,促成了日本战后政治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保守势力的合并——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随后有了“55年体制”)。后来,岸信介政府上台,追求以大国主义为目标的新国家主义政治,把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归咎于与英美帝国主义阵营作对,于是战后为了追求日本复兴必须与英美尤其是美国协调,积极反共,着手建立强权的国内政治体制,力图回复战前国家主义政权——正是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占领军、民主运动受挫等等诸社会问题,给日本敏感的年轻一代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日本电影史》岩崎昶 中国电影出版社)。 同时没有了战时军国主义政权的严苛管束,战后美国人强制占领下的压力,消失的管束带来的行为思想的巨变,这些都意味着全然解放的个人主义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断的放大感官的体验,在肉体面前,抽象的“国体”变得没有意义——当流动的、自由的和开放的时刻来临,“太阳族”影片惊人的票房,其实应证的是这些放荡不羁的人生态度在当时并不是某种精英主义式的亚文化群落,而是日本青年一代主流思潮和思想状态中的真实印刻。
b、细读《疯狂的果实》,隐匿的表述
《疯狂的果实》从开篇到临近结尾的几分钟,都一直在竭力渲染一种无忧无虑、悠闲美好的生活状态,无论是乘船出海、滑浪、别墅聚餐、酒吧、舞会、游乐场以及夜会海滩,都呈现出“真空”般无拘无束的图景。而现实的幽灵渗入则是通过另一层更为隐蔽的方式(尽管我认为导演有心全然遮蔽现实,而这种渗入却是无可避免的)。比如在众人滑浪一场戏当中,配合华丽悠扬的管弦乐曲,摄影机一直用近景和全景交错剪接的方式组织镜头,为了表现人在水面上的滑动感摄影机几乎是静止不动的,而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有全景的背景稍微有展示出海岸边破败的建筑时,镜头在下一秒就立刻切换成滑浪者的笑脸或者水面上被旋起的水花,无疑是刻意隐匿住岸边残留的平房和被破坏的建筑,因为它们显示出贫穷和生活的艰难。当然,这种对贫穷的掩饰并无任何类似于我国文革电影中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是单纯为了维护片中小资格调的风格美,即破败的建筑、贫穷和苦难的大量展示破坏了画面、整体风格的超凡脱俗,才让创作者在直觉上刻意回避。
这种刻意的隐藏还显示在影片中不断寻找“空无场景”或者小场景进行叙事的模式当中,其中以辽阔的大海上的漂流最为显豁。“海”一方面呈现出极为广阔的大空间,与日本人日常狭小的空间互为强烈对应,可以看成某种心里慰藉式的反向投射;另一方面,海洋的不稳定的流动性又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和“疯癫、抑郁和狂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边的隐喻则有点类似于《饥饿海峡》中让人惊恐的犯罪之海,和正好契合了“太阳族”内含的神经质气质。其实,如果把《饥饿海峡》中带有更多现实意味的津轻海峡和《疯狂的果实》中的近乎“真空”的海域 放置在一起比较,会产生冲击性的对照。首先,津轻海峡在影片中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贫富”分界线的暗指,即越过这道海,不但是越过生死的屏障,更是改写了国族历史下的个人历史的凄惨和穷途末路。其次,这道怒涛滚滚的无情之海,一方面承载了历史、社会和底层个人命运的悲剧,另一方面,带有天谴罪恶式的冥冥之中恐怖的神秘力量,即“人在做天在看”和“恶报终有”的意味。换言之,这种厚重的海的意涵所映照出的历史的真实,是《疯狂的果实》中那虚无缥缈、充满了历史和现实逃避主义的“真空”海所远远达不到的。
反观《疯狂的果实》,海洋如母体一般带有色情想象意味和包容感,这都清晰的呈现在原著小说中内部,几乎随处可见。如“耳畔仿佛还听见船舷冲击海水的声音。假如没有微微的冲击船舷的水声,海就成了他们两人磨光了的舞池。”或是“船逐渐恢复平静,可是却在摇动着。变成了他们过去不能知道的深沉的陶醉和无比欢乐的摇篮。”这种略带色情隐喻的广博宁静感的海,在影片中被呈现为更为感官性质的欲望,海浪、静海和潮水不止一次直接以替代赤裸裸的“性”的形式出现。当春次和艾丽躺在大岩石上休息的时候,摄影机贴近两人欲动的面部时,当两人各自吞咽唾沫,镜头随之都切到岩石边缓缓涌动的海水;又比如两人晚上在海岸边接吻时,背景是闪烁着磷光的暗海,而当想暗示两人海岸边做爱时,下一个镜头又再次切到茫茫大海和海岸边的浪花 ;当夏久和艾丽漂流在海上的船中做爱时,也是以流动的大海来做“视觉替代”;当春次在海上开着汽艇追踪夏久和艾丽时,海则承载这愤怒和疯癫。
拍摄此片时年仅30岁的中平康,与后来的增村保造、藏原惟缮等同为战后新人导演,他的“新”正体现在他的镜头内部的敏捷节奏、富有韵律的滑动、洗练简洁的意向以及所谓“触摸的技巧”的使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上述海水的呈现和人的欲望萌动的神秘主义联结和展示上,便能发现他一直把影像当作纯粹视觉艺术的信条,即一直认为细致的“描绘”表象即为他作品的全部题材、风格和技巧。
据说石原慎太郎的原著小说,有相当激烈的反美情绪,而这一点在电影当中则被彻底弱化了,但是仍有残存。当美国人出现在《疯狂的果实》中,是一个被放置于边缘和空虚化的家长,妻子与别人偷情却毫不知情,影片中的任何人都几乎忘记了他这个真正丈夫的存在。而这个美国人的日本妻子的介入春次和夏久的世界,让本来和谐的兄弟情而产生的裂隙(暗示跟着美国人紧密挂钩的概念是“欲望”和“占有”,而最终得不到的一方则选择用犯罪来彻底毁灭)。而一起和夏久等人鬼混的弗兰克则一直想竭力抹去自己的混血身份,强调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比如在酒吧一群人和几个女人搭讪,当酒吧服务生用英语问弗兰克喝什么时,他故意用日文点了一杯日本酒。与之成具有讽刺意味对照的是中平康完全欧美化的导演风格,尤其是那几场海上滑浪的呈现,自由洒脱的气质和海域风情的展示和法国新浪潮名作《再见菲律宾》的非常接近,而影片中的舞会场景几乎完全是法国式的情调,中平康也曾说他自初中时代热衷于电影,最喜欢的是雷内.克莱尔的作品,“不知反复研究了多少次”。 - 石原慎太郎将他的《疯狂的果实》剧本再交由日活公司拍摄之时提出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换和上次(《太阳的季节》)不一样的导演来拍”,另一个则是“让他的弟弟石原裕次郎 演主角”。制片人他还是坚持要用水之江泷子,正是具有敏锐的识人能力的她发现了中平康。于是随后这一部片头就用爵士乐、茫茫海洋和汽艇的马达声构筑的天才之作,让“太阳族”电影终于能够在其小说母本的压抑下,开拓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视觉和声音的空间。
两个兄弟在海边度假时,都迷恋上了一个年轻女人艾丽,弟弟春次一直以为艾丽是一个纯情少女,对她灌注深情;而哥哥夏久则清晰的知道她早和一个美国人结过婚,自己还曾是她的性伙伴之一,却也无可自拔的沉湎于对她的占有欲中。后来,夏久瞒着春次带艾丽出海远游,春次知道了真相,极端愤怒的开着汽艇追寻了他们一晚,次日找到了两人,却把他们都撞死在海上,独自一人漂流远去
——这部中平康1956年执导的、仅用17天拍摄完成的《疯狂的果实》 ,讲述了这么一起极端情绪下非理智的青少年杀人事件,片头处就用摄影机对准少年惊恐的眼部特写来表达这一不稳定情绪,而随后的回忆段落则是由奢华的舞会、海上滑浪、游乐场与海滩幽会构成的“人间天堂”,配合着萨克斯管、小号等合奏出的颓废悠扬的音乐(此片的音乐制作者是日本战后最有盛誉的作曲家佐藤胜和与武满撤)。
这些元素的混合,让这部电影在日本国内好评如潮,一下就拿到了5亿两千万日元的票房,观众人次更是达到了470万。不仅仅是票房的成功,同时还带来的是艺术风格上的清新自然——该片中轻快自由的摄影和剪辑风格,以及崭新的视听呈现,让它成为了一部在格调上美的惊人作品,特吕弗等法国“电影手册派”对该片亦是赞不绝口。
我之所以用“格调”,即美学风格上对其进行褒扬,因为它只是在自我构建的封闭小世界里讲述了一个甜美幻想和无情幻灭的故事,并没有试图进行更为深刻或广博的社会性思考,同样是把国族叙事缩略到极为闲散的个体叙事当中,却并没有包含的更广阔社会图景的《处刑的房间》做得深刻。
因而这个叙事空间的“狭小”让它成为极便于移植的空间,即无论放置于现代的哪一个海滨都可以接合的缝隙全无——中平康1967年为邵氏公司拍摄的《狂恋诗》,就是完全翻版的《疯狂的果实》的故事,场景搬移到香港海域并无不妥,更是说明了它叙事核心中所具有的孤芳自赏的内囿特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一个纯封闭空间里描摹了青年一代旖旎的梦幻建立的过程以及随后而来的残忍现实的介入带来的恶果(尽管这种残忍的恶果也是包裹着一层幻想的外壳)的手法却是卓越的。借用增村保造的话来说就是“新鲜浓烈的感觉描写,自由奔放的镜头。精细的描写人和事,把人降低为物,冷静、无感情的分析”,以及“把人拉到感觉的片断中去,把人拉回动物,否认人物古典的形象,有一笑了之的活力”
这种对古典形象的颠覆呈现在影像上就幻化成一系列带有细腻欲望的镜头,和随时能掺入别的镜头(比如潮水、暗海、天空等)的自由剪接,让中平康成为一个有意识的革新者,一个新派电影风格的始发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笠原隆夫的《日本战后电影史》中没有提到“太阳族”电影这个概念,却提到了中平康和他的《疯狂的果实》,并将其归入“战后日本导演的新人”中。在对这些新人导演风格的归纳上,认为是人物被突出、被挖掘、被从内部放大,而不是老派导演那样用环境压抑人物。增村保造也提到旧时电影里没有描写到的强烈人物形象和人生斗争,说出中平康创作的理想是“背离情绪、真实和氛围,只把活着的人类的意志和热情,进行的夸张的描写作为目的” 。
这些人性夸张的描写,其实着眼点是在于几个演员肢体本身具有的张力上,无论是扮演艾丽的北原三枝 ,还是之后爆红了几十年的石原裕次郎,都是由修长的四肢和灵敏的动作而出名。所谓“肢体派”男优女优,配合中平康灵活运动的中远景镜头,把优势发挥的更淋漓尽致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日本诸多电影导演通过优秀的作品奠定了自己在日本电影行业中的地位,比如沟口健二、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都是这一时期优秀导演的代表。
尽管五十年代的日本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两方面都达到了鼎盛,但在整体电影内容的表达上还是比较死板。大多数五十年代早期的电影都在为穷人发声,因为这个时期的电影人试图通过对真实生活的再现来实现电影的批判意义。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一些日本作家率先开始对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进行批判和怀疑。他们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千篇一律的表现形式表示不满,并对进步主义表现出来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表现出怀疑。石原慎太郎率先将这种怀疑变成了自己的小说《太阳的季节》。
1956年,《太阳的季节》获得芥川奖,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乘着游艇到处寻花问柳的年轻人的故事。在此之前,日本民众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美国式的花花公子般的生活也会出现在日本。小说问世之后,这种不良学生的形象以及生活状态成为日本社会的新风潮,此后,像小说中的那种少年也被称为“太阳族”。

日本电影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新风潮,开始着手“太阳族电影”的拍摄。其中,由中平康在1956年拍摄的作品《疯狂的果实》可以说是“太阳族电影”的代表。
《疯狂的果实》是一部故事情节很简单的电影,一对高中生兄弟,经常在海边划船游玩。哥哥夏久是运动型的少年,对任何事情都充满激情和好奇。弟弟春次眉清目秀单纯善良,总是跟在哥哥身后。有一天,两个人认识了年轻的女孩惠梨,春次爱慕着惠梨,但哥哥却让惠梨变成了自己的爱人。
如果仅凭简单的情节介绍,《疯狂的果实》的确是一部平庸的电影。但中平康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叙事节奏来拍摄。而是通过快节奏的台词和动作来加快电影的节奏,这对传统的日本电影叙事节奏是一个挑战。当剧中人说出台词的时候,我们从中感觉不到任何情感流变,而是一种很随意的感觉。
电影本身是一个悲剧,中平康用这种快节奏的叙事方式削弱了这部电影的悲剧性,而是将电影变成了一种激烈的反抗,是一种只属于青年的反抗形式,这就是“太阳族”电影的典型特点。

横空出世的“太阳族电影”。
“太阳族电影”并不是一种风格或者流派,它是一种电影类型。在日本电影史上,“太阳族电影”就像一阵强风,搅乱一池春水。尽管真正属于“太阳族电影”的作品只有五部,但这股风潮却是日本电影史上的华丽篇章。
日本电影史学家四方田犬彦给于“太阳族电影”的评价非常高,他丝毫不掩饰对“太阳族电影”的热爱,甚至在他眼中,日本百年电影史还不如“太阳族电影”来的酣畅淋漓,可见“太阳族电影”在日本电影界的影响力。
“太阳族电影”的出现和日本的一家电影公司日活电影有关,日活电影公司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司,经过战争和美军占领时期的各种限制之后,日活公司已经处于崩溃状态。1954年,日活公司卷土重来,重新开始进行电影拍摄。此时,日活公司需要面度一大堆问题,人才流失、技术薄弱、财政赤字以及其他电影公司的竞争。
在这种内忧外患中,日活公司将赌注全部压在了年轻的作家石原慎太郎身上,当时,石原慎太郎已经凭借《太阳的季节》成为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日活公司正是看中了这点,开始对石原慎太郎的两部小说《太阳的季节》和《疯狂的果实》进行改编拍摄。
《疯狂的果实》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电影打破了日本传统电影类型,用轻松简单的情节取代了厚重沉痛的现实主义电影。而且“太阳族电影”在社会上引起的舆论和关注也多过日本传统电影,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太阳族电影”就是五十年代日本民族的“热搜”。
说“太阳族电影”横空出世是因为这种电影类型并没有继承日本传统美学特点和叙事特点,电影本身就是一种现象,导演中平康的作品《疯狂的果实》并没有加入导演的道德批判,只是客观性的阐述,将思考留给了观众。
对日活电影公司来说,“太阳族电影”拯救了他们,让这家历史最为悠久的日本电影公司重新回到了行业的中心位置。

不是只有暴力的“太阳族电影”。
很多关于“太阳族电影”的评价都绕不开暴力,很多电影评论家在谈论“太阳族电影”的时候,都表示这类电影并没有突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它仅仅是一种商业电影类型,是另一种模式的风俗电影。
的确,暴力是“太阳族电影”的核心词汇,这也是后来“太阳族电影”饱受批判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仅仅凭借对“太阳族电影”的粗浅了解就来下定义,这未免有失偏颇。“太阳族电影”的确有暴力元素,但暴力并不是电影想要呈现出来的重点。
在《疯狂的果实》中,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些暴力场景,但这些暴力场景的设定主要是为了凸显出当时日本青年的精神状态。战后日本动荡不安,日本青年需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日本青年丧失话语权,于是,他们不得不通过暴力这种行为来彰显他们的不满。
《疯狂的果实》是一部围绕着兄弟二人的感情世界为主的电影,截然不同的两个兄弟对待爱情也有不同的态度,这一点恰好可以代表日本青年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哥哥喜欢寻花问柳,弟弟始终如一,前者代表了开放自由的日本青年,后者代表了稳重内敛的日本青年。
如果对《疯狂的果实》进行更细致的解构可以从中窥探到战后日本青年的精神状态,他们一方面渴望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需要借助暴力这种行为来保证生活的稳定。比较典型的就是电影中兄弟两人的冲突。弟弟用暴力手段惩治了不安分的哥哥,从此,弟弟的生活也无法再安定下来,这种感觉就像一种宿命的循环。
谈及“太阳族电影”的暴力,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和“暴力”这类显而易见的词汇来做评价。“太阳族电影”在当时能够成为一种流行风潮,绝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电影可以满足人们对视觉刺激的要求,而是在这种暴力的表象之下,有更具内涵的东西。

展现战后日本青年精神的“太阳族电影”。
日本文化是“菊”与“刀”的文化,前者是一种幽玄、静寂的美学特点,后者代表尚武精神。在《疯狂的果实》中,兄弟二人便是“刀”的代表,尽管兄弟二人在性格上有些不同,但两个人都喜欢比较激烈的运动。爱上了同一个女孩惠梨之后,兄弟二人开始暗暗较劲。哥哥通过暴力手段得到了惠梨,而弟弟却用更加极端暴力的手法终结了哥哥的生命。
在日本文化中,尚武精神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战争之后的日本,尚武精神被物质需求和社会发展所瓦解。曾经激励了无数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此时成为历史中的符号,多多少少有些惋惜。
导演中平康在《疯狂的果实》中将尚武精神变成了一种悲壮的情感内核,让兄弟两人的情感走向和行为走向都建立了新的“尚武”精神之上。电影中的兄弟俩人本是积极向上的青年代表,然而现实和社会让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报复,所以,他们只能空挥拳头,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宣泄在无意义的暴力之中。
如果说,战争之前的尚武精神是尊严和希望的象征,那么,《疯狂的果实》中的尚武精神则是一种失落和迷茫的象征。“太阳族电影”的内核其实还是日本尚武精神,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尚武精神有了不同的表述。

在当时,人们对于“太阳族电影”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部电影中隐藏了没落的尚武精神,更是因为“太阳族电影”抓住了日本年轻一代的心理状态。
战后的日本青年对父辈极为不屑,并将日本战败的原因归结于他们的父辈。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企图颠覆父辈的思想和即成的道德规范,于是,他们不断地否定自己的父亲,在心理上完成“弑父”。这种对传统父权的反叛是当时日本青年的主流思想。
遗憾的是,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他们反抗父权,却又不得不依赖父权。尽管他们有一腔热血,却无能为力,只能依靠暴力来宣泄。
我们在欣赏“太阳族电影”的时候,没有必要一定要求这种电影具有美学价值或者艺术价值。任何电影类型的出现都和当时的时代有着直接联系,很多日本评论家、史学家都刻意忽略“太阳族电影”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太阳族电影”的确不符合日本电影传统。

但是,“太阳族电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一种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并且这类电影中蕴含的精神特质得到了观众的肯定。他们需要这样的电影,需要通过这样的电影来怀念武士道精神,而这也是当时日本社会最需要的东西。
- “太阳族电影”
“太阳族”的出现首先是一次文学事件。年轻作家石原慎太郎1955年凭借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了芥川文学奖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轰动。故事中同主人公聚集在一起的年青人都出生于富裕家庭,自幼娇生惯养,不学习、不劳动、生活奢侈放荡,不遵守社会秩序。从此,同《太阳的季节》中刻画的人物相似的青年群体被统称为“太阳族”。
随后,1956年5月日活的导演古川卓巳把《太阳的季节》改拍成了电影,取得2亿日元的票房。接下来在同年推出的,石原慎太郎编剧,由他弟弟石原裕次郎主演的《疯狂的果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导演中平康的作品甚至在西方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法国电影人特吕弗撰写了影评高度赞赏了《疯狂的果实》,称其虽然对该片的导演中平康一无所知,甚至分辨不出石原兄弟的差别,但却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导演中平康年轻,技巧纯熟,“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常务校长泰索诺应该买个《疯狂的果实》的拷贝,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放给学生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什么才能成为一名有自主想法的导演而不是只想着学会当助手的思维。
从小说到电影,“太阳族”的出现和它引起的轰动成了超出文学范围的社会事件。高额的票房成绩代表着的社会共鸣却也说明了大众社会心理的转变。日本电影人岩崎昶认为日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的实际感及其反面的经济上的安定感”,使人民群众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太阳族心理”,即“从对一切进行反抗到全面加以否定,急躁的乱闯一阵。”
“太阳族电影”以石原慎太郎编剧的《太阳的季节》、《疯狂的果实》与《处刑的房间》为代表,尤其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太阳族电影”一个个看似堕落又无聊的故事,没有了感伤的道德主义情怀(小津和成濑电影的特点),也没有对现实社会进行任何的批判(山本萨夫与今井正等共产党员创作的左翼独立电影),年轻人现时生存状态以一种完全不用粉饰的讲述方式得以展现。在《太阳的季节》中,即使爱情在某个电影段落中被诗意的描绘,最终却也逃不过虚无幻灭的残酷归属;而在《疯狂的果实》中,兄弟两人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在海上决斗的场面更是突破了当时的道德底线,展示了一种赤裸裸的真实。这种直观冲动的电影表达方式打开了日本大众电影发展的另一种文化空间。增村保造在一篇题名为《新人作家的主张》的文章中提到:“日本电影的青春,在中平康导演的《疯狂的果实》中对这以前日本电影沉闷的客观描写进行正面挑战,否定了小市民的道德和伤感,进行新鲜浓烈的感觉描写,开始自如奔放地驾驭镜头,这种运用开始萌芽、开发。”正是以“太阳族电影”做为转折点,日本新浪潮运动才得以承接。虽然在整个60年代,日本国内电影市场由于受到电视普及的冲击陷入了低谷,但大岛渚、今村昌平、筱田正浩等新浪潮健将在接下来的10年内维护了日本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