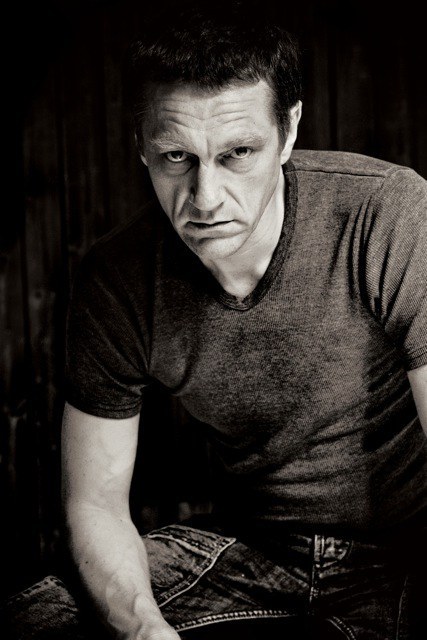希望的另一面 Toivon tuolla puolen(2017)
简介:
- 一个叫做哈立德的年轻叙利亚难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家人。近乎偶然之下,他藏在一艘运煤船里流落到赫尔辛基成了一个偷渡客,并在当地寻求政治庇护。维克斯特伦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他在牌桌上赢了一大笔钱之后在赫尔辛基的一条后街买了一家不赚钱的餐馆。在当地政府作出要将哈立德遣返回阿勒颇的判决后,他决定非法留在这个国家。最终,维克斯特伦发现哈立德睡在他餐馆的内院里,并聘请他到自己餐馆里做清洁工和洗碗工。生活会短暂地向我们展示它光明的一面,然而命运很快就会插手其中。
演员:
影评:
 年初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因禁穆令拒出席颁奖礼
年初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因禁穆令拒出席颁奖礼2017年初,特朗普颁发一纸入境限令,在全球引发同步振荡。这股风波一直延续到2月底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为上半年的魔幻现实主义气候嵌入了基座。自2015年以来,面对持续发酵的难民危机,欧洲各国在人道与国情之间左右摇摆,加上各地频发的袭击事件,合作进程屡屡中断。原本开放包容的一体化格局陷入泥淖。边境管制加强,社区冲突不断……特朗普对本国非法移民的驱逐,足以视作矛盾蓄积日久后的集中爆发。

在接收政策遭遇冲击的当下,还有多少善意能冲破纲领的障碍,来自民间的温情能否融化冰冷的司法秩序?阿基·考里斯马基在其最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中,以一个盛满暖色调的故事,向我们抛出了他的回答。
影片前半段由两条故事线构成:与妻子分别后的服装商维克斯特伦,在赌场赚得盆满钵满,成功转行踏入餐饮业;叙利亚难民哈立德在逃难途中和妹妹走散,偷渡至赫尔辛基寻求庇护,一面申请移居一面苦寻亲人的下落。命运的落差与戏剧性在此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展现,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同时映入观众视野,二者身份上先天与后天形成的鸿沟,在一幕幕画面的切换、对比中被不断放大。

评论界常将阿基的电影比喻为“沉默的诗歌”,他对台词的运用格外节制,仅靠镜头中的一系列人物、冲突来完成衔接。在《希望的另一面》开头,维克斯特伦拎着皮箱出门时,不与妻子道一声别,隔在二人间的只有沉默,与桌上的烟蒂、伏特加酒瓶、钥匙、戒指等物件。通过高度简化的创作宗旨,影像如精练的诗歌一般,于留白深处尽显从容,缔造无限的冥想空间。
而这也成为阿基的电影难以被部分人接纳的原因所在。冷淡如舞台剧的转场风格,常使习惯了好莱坞式快节奏剪切、叙事的现代观众陷入昏睡。和制片厂垄断下的流水作业相比,他所奉行的原本就是另一条道路——与欧洲风格化、古典化创作精神相契合、带有作者印记的拍摄方式。当人们沉下心来,便会瞬间浸入一种静默舒适的氛围,仿佛穿梭于赫尔辛基这座老旧的城市,被其中复杂的社会风貌,及一群善良的底层民众所触动。
这样的城市,注定与超级英雄出没的纽约等现代化都会不同,更适合于讲述小人物的故事。落后与乐观,也一并烙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交相映衬的两面。
 电影《勒阿弗尔》
电影《勒阿弗尔》2011年上映的《勒阿弗尔》,记叙了一出平民合力帮助黑人男孩的故事。而作为“港口三部曲”系列的第二篇章,阿基在《希望的另一面》中再度着眼于难民题材,不难看出他对这一现象的积极关注。选用阿勒颇作为主人公身后的家乡,更具有尖锐的写实意义。
与前作相同,故事聚焦的出发点不在于危难本身,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集、碰撞。和视角交杂的同类作品相比,影片以分外冷静的笔触,完成了对身份焦虑、文化融合等话题的抽象解读,就连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也仅是一笔带过。通过哈立德在警局对逃亡经历的断续回忆,电视里模糊的新闻图像,导演间接挑明了战争给人最大的伤害:并非肉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无法抹平的创伤。
 德国民众涌入街头,抗议默克尔政府对中东难民的接收政策
德国民众涌入街头,抗议默克尔政府对中东难民的接收政策从以德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放宽难民接收政策以来,街头抢劫、伤人等恶性事件频繁见诸报端。政府提供的各项就业和医疗保障措施,非但没能解决双方分歧,反倒加剧了种族之间的仇视和情绪对立。追根溯源,流落他乡的难民在接触社区、建立新生活的过程中,面对语言文化截然陌生的环境,心理滋生隔阂。受社会地位低下的牵绊,他们难以觅得稳定的认同与归属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外来群体与当地居民间的融合。
电影中哈立德身处异国的遭遇,便极具说服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他操着别扭的口音和人打交道,被街头挑衅的混混围殴……远离战火和硝烟的宁静街巷,似乎并不能施予他避风的港湾。从伊拉克来此避难、经验更为丰富的友人同样无奈地告诉他: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一年,但我的生活毫无起色。”
“悲伤的人会首当其冲被送回去。”

要想融入当地,就要学会掩饰悲喜,假装自己过得很快乐,这是难民潮孕育出的隐性规定。而当移民局冷酷回绝了哈立德的庇护申请,决定将他遣送回国时,法理与人伦间的对抗立时浮现出来。
当多种标准难以共存时,人们如何谋求平衡,打破眼前的困境?导演提出了一个简洁,大胆,而又具有普适性的答案:跟随人性中良知与善意的指引。

正是这种脉脉流淌的温情,将两条平行的叙事轨道缝合在了一起。两个国家,两个大陆,两种文化,对应着无数独自游逛、渴望安放的灵魂。维克斯特伦和餐厅众人达成默契,促成了哈立德和妹妹的重逢。在黑白交替的光影间,人文关怀不再仅是句空洞乏力的口号,而是邻里慷慨伸出的援手,是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的情感力量。
在阿基的作品中,似乎总存在一段离奇的际遇,和光明向上的结局。尽管不时有评论家指出,这种对于人性美好、高贵心灵的颂扬,终不过是理想化的世俗愿景,显得过于顺畅,缺少层次性。而对于种种不可能性的颠覆,正巧凸显了创作者执着的道德信念。这种发自内心、纯洁无私的赞美,不啻为寄予在底层群体身上最朴实的希望。

影片结尾,哈立德的妹妹步入警局,决心为自己争取一个全新的未来。被捅伤后的哈立德倚坐在河畔树下,被小狗蹭着脸,背景响起节奏轻快的音乐。影片最终定格在这童话般温馨惬意的一幕,而导演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分裂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我们如何读懂、理解来自另一世界的人?回音纷乱交织,又似乎很简单。
希望的另一面并非绝望,而是灰暗中隐约透出的希冀。只要漂泊的温情不被固执卷入涡漩,漆黑的海面上总会亮起灯塔,为无数流离失所的异乡人捎来黎明。
- 可知道,有的餐厅并不发放菜单,因为厨师只做一道菜——就算有菜单你也没得选。“作者导演”圈里,阿基·考里斯马基就是一位这样个性厨师,他不像其他有些大导演,想办法从技术或题材上实现突破和对艺术生命的延续——而是恰恰相反,把对自己已有风格的坚持作为“突破”和“延续”本身。参加2017年柏林影展(并最终荣获最佳导演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依然是阿基对底层阶级,社会福利机制,移民等敏感问题谱写的另一部变奏曲。
喜爱这位芬兰导演的观众,首先一定是“阿基美学”的拥趸:以胶片为载体的明暗和色彩,极简布景,不苟言笑的人物,和舞台剧效果的对白,还有动听醉人的摇滚乐。这些元素在《希望的另一面》里都轻易找得到,并有增无减。略有新意的是对故事线的处理,在剧情并不以 Wikström (餐馆老板) 和 Khaled (叙利亚难民) 两位男主角中的一人为中心时,导演巧妙地在影片的第一个小时里让毫不相干的两条线索并行——此时,整部影片的调子是十分舒缓的。而在观众对情节和人物的把握逐步清晰之后,两条线开始汇合,同时,影片的节奏也开始加快,随着两线相合带来的张力最后一气呵成,看起来十分舒服。
这样工整讲故事的方法其实十分古典,而阿基则再一次用实践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形式本身就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布景,色调,幕与幕的切换,叙事的章法,还有配乐做得都足够完美的情况下,其他元素——诸如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对白,甚至表演本身——都是可以退而求其次的。 这也是在我眼里,《希望的另一面》超越了阿基本世纪前三部作品(《勒阿弗尔》《薄暮之光》《没有过去的男人》)中最主要的一点。作为本届影展开始前最受关注的一部影片,至少从纯粹的观感来讲,相信每一位去现场的人都和我一样,不会失望而归。尤其值得一提是导演在这部电影中对配乐的使用,除去歌曲旋律的动听和应景,其中几处甚至通过音乐本身实现上下幕的切换(例如在音乐演奏了一阵之后,路边的摇滚歌手从画外进入画内),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回到内容上,导演在本片里对社会问题的视角和分析架构,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后面会详述)。这是既《勒阿弗尔》之后连续第二部着眼于移民这一(相对较新生的一类)社会底层人物的作品,有人也把它和《勒》一起归入“港口三部曲”系列。上一部是围绕着“Haven”(庇护所,也是 Le Havre 里后一个单词的变体)这一母题展开,这一部则是另一个“H”开头的单词——“Hope”(希望)。
和在《勒阿弗尔》里由“Haven”而带来的追,躲,逃等一系列紧张激烈的交锋不同,这部以“Hope”为题眼的《希望的另一面》则要温和许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Khaled 和他兄弟之间的“战壕情谊”,收容他的 Wikström 虽然穿着资本家的外衣,却也以资本主义的“务实精神”为 Khaled 提供帮助——眼前一副“世界大同”,但导演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刻画去强调这“大同”背后权力机器的冷漠与社会生态的“非人”。和《薄暮之光》里的科斯蒂宁以及《没有过去的男人》的 M 相比,本片里的 Khaled 至少看上去要幸福一些,哪怕实际上他来自一个更苦难的国度,而他在赫尔辛基面对的遭遇可能也会更为残酷。在故事本身的力度上,我认为本片是不及上述两部的。
在我眼中,阿基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视角基于一种稳定的“三角结构”——施暴者,受难者,调和者。这部影片里,Khaled 自然是受难者,掌握他留居大权的移民和福利机构则是施暴者,而餐馆老板 Wikström 就是调和者。三类角色中,调和者无疑最为重要,也是阿基电影母题中最值得细看和反复玩味的地方。《没有过去的男人》中,主人公 M 一人同时肩挑受难者和调和者的角色,是一位“强势”的“弱势群体”;而《薄暮之光》里,调和者的身份是相对较缺失的,只有那位一直默默关心和爱护科斯蒂宁的女商贩勉强称得上,但爱情终究不是调和者的有力武器;来到《勒阿弗尔》,调和者一下子变成了整条街上的所有群众,他们以马塞尔为核心,用各自的“微薄之力”协同面对掌权者的施暴。最后,在《希望的另一面》里,资本家 Wikström 也成了调和者这一“大家庭”的新成员。
Wikström 这一角色的设置为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完全是 M 样的英雄主义,也不是《勒阿弗尔》中自下而上和“自卫式”的群策群力,而是像在本片里这样,归根结底需要借助底层和中产(甚至掌权者)阶级之间真正的有机融合。当然,这种设想本身是否更为实际,大家扪心自问是更喜欢本片还是《勒阿弗尔》就会有答案了。
其实,相较于调和者的不同身份,我个人更想看到的是在这“三角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会不会有“第四种身份”存在?影片末尾处 Khaled 的妹妹这一角色出现之后,我的确产生了希望。她一开始并未作为纯粹的受难者角色出现,在短暂的兄妹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并不统一。哥哥已经认清了现状和施暴者的面目,而初来乍到的妹妹依旧抱有幻想,或许还由于个人信仰的因素,完全秉持着与哥哥不同的价值观和面对权力机器“施暴”的态度。当然,遗憾的是影片没有就此展开,我们对这“三角结构”之外的“第四种身份”意义何在也就无从谈起了。
妹妹这一角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遐想的可能。社会本身毕竟是流动的,多元的,异质的,在阿基精彩的艺术处理下,如果人物之间有更立体的碰撞,我们一定会更呼过瘾。 - TRACKLIST
"Oi Mutsi, Mutsi" - Tuomari Nurmio
"Soi Maininki Hiljainen" - Olavi Nyrhilä
"Midnight Man" - Ismo Haavisto
"Syyspihlajan Alla" - Henry Theel
"A night without moon" - Sherwan Haji
"Tämä Maa" - Timo Kiiskinen / Harri Marstio Ja Antero Jakoila
"Kaipuuni Tango" - Marko Haavisto Ja Poutahaukat
"Skulaa Tai Delaa" - Dumari Ja Spuget
"Takedan Kehtolaulu" - Toshitake Shinohara
"Hoshi O Mitsumete" - Toshitake & Old Boys
"Mortadella" - Jukka Salmi
"Illan Suussa Kun" - Jukka Salmi
"Kurjuuden Kuningas" - Dumari Ja Spuget
source: Sígur Le Naif@facebook 小津安二郎、罗伊•安德森和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角色人物的表演都可以用“僵硬”来形容,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小津安二郎的是“僵而不硬”,演员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带浅浅的笑,没有大的感情起伏,面部表情变化很小,其背后蕴藏着些许无奈,但保有温情,小津的风格完美体现解构主义的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无指向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锚定,但细品觉涵义隽永,他的影像中最平淡的生活原生像却使观者有其各自的解读和感悟,孰对孰错本无定论,生活的真谛在被濒临把握时又被重新解构了,导演没有有意识地传递给观众以某种意义,因为传递的信息不是导演艺术的单一表达,而是日本家庭文化的各种冲突的体现;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是“硬而不僵”,剧中人物面部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双唇紧闭,言语交流生硬而缺少感情,语言交流剔掉所有无用寒暄的修饰枝节,减除圆滑、世故的用语和行为,这样增加了交流的有效性,去除了表达的多义和含混性,阿基的影像特质是结构主义最好诠释,人物关系看似松散、孤立,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严实、紧密的整体,孤独的个体也是社会整体的镜像和浓缩,个体是与他人的同一合作中形成并不断地完善自我;而罗伊•安德森的是“既僵又硬”,人物面部涂上油彩,已难看出喜怒哀乐,他们行动迟缓如僵尸,去情感化的生活呈现出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氛,安德森的影片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被抛,沉沦和向死而生。 阿基的影片以七十分钟左右居多,但这部影片却超过了一百分钟,算是阿基影片中的一个异类。阿基电影的一大特色是色彩的运用,他的色调是暗色系的,忧郁的,古典而怀旧的,大范围的偏暗色块运用衬托着人物角色与现代时代的隔离与滞后感。影片色调非常贴合西班牙画家里贝拉画作的暗色调,阴郁而庄重,但影片的内在形式却是印象派的,导演主观经验来迅速捕捉生活瞬间,影片呈现的生活是采样化和粗线条的,导演的目的意不在将生活刻画得精致或苛求逻辑上的严密性,人物偶然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例如影片中开餐馆的芬兰人对于叙利亚难民的出手相助,更显弥足珍贵。人物的交谈简洁和直接,即使是得到对方的帮助,也很少说“谢谢”,客气的寒暄在影片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此的交流更显真挚。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已经高度发达和全球化的社会的今天,表面上生硬的言语,实际上是摒弃了人们惯常的搪塞、推诿、恭维等假情假意,而还原了语言创立之初的本质。 阿基影片中的芬兰人多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现实世界中的芬兰人是否也是这般模样?本人和一些芬兰人有过一些接触,的确他们多是比较严肃,不喜欢开玩笑,通常嘴唇都紧闭着,而且在酒店大堂等处相遇他们通常不会和陌生人打招呼,对于你的问题,会做简短回答,不喜欢聊天和闲谈。既然说到了芬兰人的性格特征,下面就再闲聊一下其它几个国家的,首先说明,我只是接触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具体都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并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评论也力求客观(100%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受评论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所影响),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言行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整体,但是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每个个体所有的特质都会在其代表的整体中找到多个类似的样本,因为个体的特性都来自与他的群体的遗传性和社会性,而不会凭空出现,因为其行为多是由其在群体之间交流中产生的,不被理解的行为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见一斑,可大致窥全豹。首先说一说美国人吧,毕竟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无处不在,考虑到美国短暂的国家历史,加上其复杂的国民组成,可以说美国人是没有统一的民族性的,作为一个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都有一定的接纳性,但整体上,美国人是看不起黄种人的,但表现是非常隐蔽的,多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旅游场所或餐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对于白人是面带微笑的,对于黄种人表现不卑不亢,即使有笑容,也有种皮笑肉不笑之嫌。当然大家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你自己玻璃心,一边向往美国,一边又总觉得自卑和自尊心受损,酸葡萄的心理作祟?” 那估计您会错意了,因为本人一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样有龌蹉的思想,一样的吃喝拉撒,皆是自私自大的一团团活动的肉而已,而且我也不向往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因为看过了解过之后,发现各有各的光鲜和污秽。下面说一下日本人,基本上我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的有礼貌,做事情讲究遵循原则,即使是某个事情做了无数遍,他们都不会走捷径,当然他们对于国人喜欢抄近路办事方法比较不喜欢,他们也非常的爱干净,还有他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去喝酒都非常的实在,与国人都想让对方多喝不同,他们喝起酒来毫不谦让,每次都以喝多喝吐告终。日本人由于民族组成的纯粹性,所以他们的民族的特性也非常的明显,固执而执着,并且他们对于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轻蔑,但他们对于不符合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言行是看不起的,其交谈的话语的语调和面部微妙的表情已表明了他们的内心。再聊一聊韩国人,他们也是比较的讲礼貌,见面非常谦逊地打招呼,他们做事对于规矩的遵守介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做事遵循原则也有时不排除走捷径,而且他们好多人都可以讲一些中文,而且他们也比较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中文表达,不是为了简单地秀一下他们会了几句中文而已。下面看看印度人,他们有时会非常明显地表示出来看不起中国人,估计自己一直为自己自诩的白人身份不被认同而愤愤不平有关,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喜欢夸夸其谈,大谈心灵鸡汤,说的多做的少,是镶金边的尿壶-嘴好,眼高手低,作CEO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现实也的确如此。 接着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他们做事情没有美国人的严肃性,行事有时偏随意,即使是工作上的事也不例外,有时他们显的比较自大,估计还是吃着以前拿破仑的老本的缘故。说到英国人,他们多表现温文尔雅,讲话句式比较复杂,用词比较美国人考究,交谈时比较尊重对方,会聆听对方再作回应,不似美国人多喜欢夸夸其谈。英国人与国人交往,非常礼貌,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傲慢的,他们总是抱着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最后说一下德国人,他们做事严谨,但表面不像芬兰人看上去那样冷漠,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比较热情,为人谦逊和对人礼貌,他们的自豪和优越感是不外露的,这是最高层次尊贵感,不靠轻看和贬损对方而彰显自己。而低层次恰恰相反,人们最看不起的是和自己相像的同类人,因为他们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恼火,基于库利的“镜中我”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觉得人们逐步地形成自我的过程也是渐渐厌恶自己的一个历程,所以他们才选择轻贱“像自己”的他者来排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