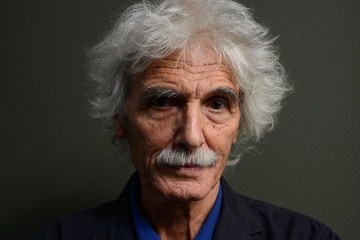哦,人呐 Oh! Uomo(2004)

又名: Oh! Man
主演: Benito Mussolini
制片国家/地区: 意大利
上映日期: 2004-05-21(戛纳电影节)
片长: 71分钟 IMDb: tt0431958 豆瓣评分:0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 也许,如巴赫金曾经实践的那样,我们总可以在若干本书中抽取出毫无关联的若干语句或者章节,然后将它们组合为一本新书。新书具有崭新的字句排列,却如待开采的矿产一般等待我们用阅读行为使得它的新叙事与新含义获得成立与价值的可能。阅读便是缝合 、治愈新书文本秩序与结构中无理性 的手段:借助于互文性 的宽广 ,合理性成为了阅读行为的派生之物,一种意识形态的自发生长 。阅读使这本书不再是一本“引用 ”之作,而是成为其自身。但当我们面对的是图像呢?也许“观看”就是解决之道。观看戈达尔的电影,便是观看“引用”影像转化为自主影像的过程。最显著的例证便是戈达尔的《电影史》, 在那里记忆-影像(包含电影影像 以及其他各种影像 )通过一种个人化的编码手段构建出一座电影性的“想象的博物馆 ”。
而在《Oh,Uomo》中,Yervant Gianikian与 Angela Ricci Lucchi面对的却是历史-影像,他们的工作即是对“过去”进行直接的拼贴与组接。与《电影史》不同,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察觉到的是对于引用图像的一种冷静的、忧郁的蒙太奇,而非批判式的、杂种式的;戈达尔严苛的句法体系被更加自然与和谐的衔接所取代,但这种衔接明显具备一种更鲜明的、锋利的“情感”层面。互文性也不再是强制的,而是伴随着 保罗•维特根斯坦 的钢琴舒缓的进入我们的精神。透过“la caméra analytique”的重新取景 ,我们观看到图像与历史的诗意的和解,而不仅仅是它们在剪 与辑 的操作下生硬的碰撞。总之,我们不再被催促着去认知 与认同,反而是在安静的观看中,在人的形象与战争的形象连续呈现中,仿佛置身于德勒兹式的时间-影像中,直接抵达记忆的彼岸 ——产生了对于那场恐怖战争的“记忆”。
而在整部电影临近结尾的部分,这种流畅的感知却戛然而止,这是因为银幕上出现了骇人的残缺 :士兵们手术后的脸以及假肢。这两个部分似乎外在于整部电影,成为一种褶皱 性存在,从中我们却可获知到一种“不真实”所及的维度。这种不真实恰恰代表了乌托邦名义下的一种福柯式的治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学将士兵受伤的身体规划入一种已命名的医学权力关系(象征秩序)中,治疗成为完满一种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手段。例如,在人道主义的名目下,我们“有权”将人制作成一种怪物,一种弗雷根斯坦 式的合成人。而在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画面,面对这样的面孔或假肢的特写,我们面对却是一种历史性的污斑 ,而透过这片污斑遭遇的则是那些士兵的凝视,让我们突然感受到历史的沉降是如何关照当下的。
士兵们手术后的脸是一种“变形 ”(或者用另一个词:不定型 )。从这些变形的形体 上直观联想,无疑会牵扯到电影中那些著名的怪物的形象:夸西莫多,歌剧院的幽灵或者象人 。只是这些士兵的肉体是真实的,他们规矩的站立在镜头前,并非在表演,而是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检阅。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参照当时的观念,摄影机镜头与他们的脸的对视正代表了不同的文明成就之间的对话。而如今,在电影院中的我们取代了摄影机的凝视的地位,却只能感到战争之罪 。“变形”已成为以电影的专利,或者连环画的主题(在最近的连环画《战争的婊子 》中有非常类似的图像),而不可以再在生命实体上得以实现。
齐泽克对于不定型有一段描述:“‘活死人’好象是死的,死亡——恶臭已四溢,但死只是面具,下面却藏着一个生命,一个远比我们一般生命更加鲜活的生命。‘活死人’并不处在死和活之间的某地,他们的死恰恰是一种‘比生命更鲜活’的死,他们在生命的符号性屈辱之前便已触到生命实体”。 根据拉康主义,无定形凝视 便是一种禁忌的镌刻,一种创伤的呈现。“活死人 ”的生命事实上已经经历了一种符号性死亡而转化为一种真实的生命,而他们的存在亦成为了对于某种隐蔽的、制定禁忌大他者 的揭发与批判。在这部电影中,与夸西莫多或者歌剧院的幽灵不同,浪漫主义的不定型已经转化为一种超现实主义或者未来主义式的不定型,代表了资本主义到达帝国主义阶段后某种野蛮的倒错性情趣 ,一种将机械植入、代替人体的乱伦快感 :身体可以成为某种可炫耀 的工业成品。在银幕上,士兵的特写所揭露的这种禁忌使我们感到恐惧,是因为这种“凝视”强迫我们去思考自己的身体是否会遭到这种整饬的可能,亦即我们与“活死人”之间的某种历史符号性距离 。
从而,我们从不定型回到了拉康的凝视 。对于拉康而言,不定型造成了眼睛与凝视的分裂,并提供给了凝视一种反思的时刻。如拉康所言,“我所遭遇的凝视,不是被看的凝视,而是我在大他者的领域所想象出来的凝视 。” 这种凝视使我进入画面并成为画面 ,使我感到大他者无时无刻对我施予的监视。最著名的变形要算作荷尔拜因 的《大使 》中的那枚污斑:变形的骷髅成为了颠覆全体的“坍陷 ”。而从这个坍陷出发,我们便可以怀疑经验世界 ,可以开展意指过程 并开始探寻这个混沌世界背后的真实的含义。按照齐泽克的解释,透过这块污斑,“我们看到的图画被主体化了,此吊诡之点把我们从中立的、客观的观者的位置上赶下来,并把我们囚禁在被观看的课题的位置上。正是这一点,观者被吸纳、被誊写入他正观看的场景,也就是说,正是在这一点,图画本身回看我们。” 这种回看无疑带有着蔑视与恐怖的意味,仿佛大他者的一种威胁,却也激发起我们对于大他者的反思与抗拒。如同面对士兵的变形的面孔时,我们便可以反思战争之罪、之痛与荒谬性。在银幕这个镜面上,《Oh,Uomo》提供的反思型的图像不再劫持 我们,而是使我们的观看行为获得了某种权力与解放,这也是历史图像相对于虚构图像 所独具的某种特殊的启示意义。
而作为这些图像的发现者,两位导演却率先为我们承担了这种开启观看的痛苦。他们将尘封在各种档案中的罪恶与伤痛发掘出来,他们观看的苦难数倍于我们。故而他们也就有权发出这样的诘问:“Les images sont à notre disposition pour être touchées des yeux, du cœur, de la raison. Les images reviennent pour nous depuis fond obscure du passé. Elles nous reposent le présent. Comment avons-nous pu oublier ? N’avons-nous rien app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