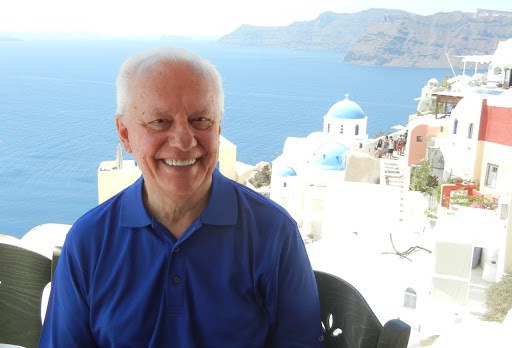错误的举动 Falsche Bewegung(1975)

又名: 歧路 / The Wrong Movement / Wrong Move
导演: 维姆·文德斯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西德
上映日期: 1975-03-14
片长: 103 分钟 IMDb: tt0071483 豆瓣评分:7.5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本片是文德斯“公路电影三部曲”之一,在1975年荣获德国电影奖多个大奖(最佳导演、剧本、男女演员、摄影、剪辑及音乐等)。
演员:
影评:
继爱丽丝城市漫游记后,在电影鉴赏课上看了文德斯的公路三部曲之二。
这种几乎没有连贯故事的电影,课后我们总是会多花点时间进行讨论。有人质疑,这到底是在拍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传达到。而我却认为在这部片中,导演似乎想传达的信息太多。即使有一个主人公的存在却没有刻意倾向一个侧重点,因而显得分散了。而当我把这些碎片一般的信息拼贴起来,我不禁感叹导演能观察人至此、能拍出这种形态的电影,实属不易。
日文的标题是「まわり道」(绕远路),经过了100多分钟之后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标题,可回过头再想,题目早已经概括了整部电影的核心。
我从我个人的理解,给予每个人关键词来说明他们各自绕的远路。
【以下均为个人解读】
男主角的关键词是【梦想】。
他渴望成为作家,但他不去动笔磨炼,而是踏上旅途,生命中不停地出现更多的戏剧性,渴望因此得到灵感的刺激。这部故事可以说就在他这样的期待下,一步步推进着。很显然,只将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的人无法成为作家,灵感也很快会被掏空。于是当他们一行人在公寓里住着,一切不再浪漫而是一地鸡毛,不再充满不确定而是重复漫长,他再次提出了离开,这一次是去登雪山。(其实去哪儿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去到任何地方都无法成就他的梦想)
女演员的关键词是【爱情】。
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体现出她工作场合的状况,也说明并没有要着重表现女演员这个身份,而是作为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大多数时候看起来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然而她对命运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偶然邂逅到了作家,第一次单独约会后面就跟着两个电灯泡,开始还提出了希望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要求。之后却慢慢习惯,开始和这几个人一起行动、生活。
刚开始还觉得作家的冷漠让她着迷,而当工作失意的她在倾诉时,作家仍旧听不到似得地埋头工作,甚至于说:“你要是想杀人的话,就动手吧。我正好可以当写作的素材参考。”她撕碎了他正在打的文章,拿着刀对着他。在作家眼中,从来都只有他自己和他的作家梦。他与她在一起,也不过是为了体验“与萍水相逢的女演员坠入爱河”的情节。就好比他第一次拨通她的电话,只是忐忑地期待着一个女演员会有着怎样的声音。
老伯的关键词是【战争】。
又是一个谎报身份的人,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歌手,身边跟着的小女孩是他培养的艺人。在任何不合时宜的场合都会开始他的口琴表演。无论是火车行驶中还是熙攘马路上,亦或是企业家自缢在屋内时(被男主一巴掌打断)。在某一个清晨他又不合时宜唱出了一首民谣,他说那是犹太人唱过的歌曲,而那唱歌的人被他杀死了。火车上唠唠叨叨的列车长曾经是他的部下。浑浑噩噩地生活,对死亡或者人际关系统统麻木,似乎成为他战后的一个精神状态。这里没有忏悔和反思,可隐隐道出战争对每个人的影响。战争与人类文明饶了远路,带来的只有一大批受创的灵魂。
小女孩的关键词是【成长】。
女孩的台词不多,不确定我有没有中间走神,因为似乎也没有交代她的身世。看起来是这一群人里最身份不明的人,但因为对任何人都毫无威胁也没人特别关心。她可以毫不顾忌地在火车上开始倒立,大街正中表演杂技。得来的钱尽数交给老伯。深夜里她假装是女演员与作家亲吻,作家发现后扇了她一耳光。但似乎没有使她改变分毫,还是那个轻松自在的女孩。很明显,没有人去教育她是非对错,这一群人允许她看电视到睡着,也允许她随性而为。
眼镜小胖的关键词是【胆怯】。
这里有点意思,之前几个有梦想、爱情、成长,这里要说的却是性格使人饶了远路。小胖因为个性胆怯,每次总是慢别人那么一步。
当他听到男主的诗很是惊叹,想要给他看看自己写的诗的时候,却没能说出口,于是就这么干张着嘴;当他给女孩捡了东西递过去,人家走了,于是就这么干举着手;一路尾随男主一行人,在不恰当的时刻分享起他的诗;清晨大家聚在一起闲谈各自的梦境,他一时想不起来,于是想了大半天,又在不恰当的时刻非要拉着人说他终于想起来的梦。
这里我有点难以形容,这又是胆怯,也接近于唯唯诺诺,有时候还咄咄逼人,总之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如果说其他人是拥有着各自的执念、心病。那么这位老兄则是别人眼里的二傻子。总是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表达错误的内容。
企业家的关键词是【死】。
当一群人跟着小胖不确切的信息闯入他家,他本来正准备自杀,于是被挽回了一丝生存的意念,留一行人住下。在乱糟糟的客厅,壁炉火苗的跳动中,他倾诉了自己妻子离世后的孤独。讨论了孤独究竟为何物(原谅我这一段具体的台词没记得)。与作家谈话间,他不知无意还是有意地拿着笔尖戳进手掌。这位大伯症状上来看是重度抑郁症。一夜过去,当清晨到来,一行人附近散步,他似乎是带着猎枪去乱打去了(此处没有给镜头,主镜头一直跟随者男主和周围人的交谈,只有背景不时传来的枪声)。当男主看到他突然登上摩托车往家里冲回去,就猜测到会出什么事了(追寻戏剧性的作家本能)。抑郁症的企业家尽管被暂时打乱了情绪,发作的时候还是会不受控制。于是当他们赶回去,只见到了悬于房梁上的尸体。
这里被饶了远路的是什么呢?竟然是死。本来应该前一天夜里自杀的,经过了和人彻夜倾诉,家里也入住了男女老少增添许多新鲜气息,还是没能改变任何事情。想必他自己也是在打猎的清晨忽然意识到,这种倾诉和陪伴的劣质和脆弱。
劣质和脆弱,这是我在影片自始至终感受到的东西。这种微弱的联系栓着几个人四处走动。当作家与女演员他们告别,很快又遇到了表演杂技的二人组让他帮忙录像。
再上路,搭伙作伴的可能换了一群人,但依然是似曾相识的症状,似曾相识的一拍即合、无疾而终。
持续绕远路的每个人总是依着惯性顺从惰性,依着惯性驯服偶尔产生的疑问。
一群人作伴踏上旅程,与各自的追求确是越走越远。
让我茅塞顿开的节点不是企业家自缢那里,而是在后半段,男主角在渡船上试图推老伯下河的场景。这里首先在前半段就埋了个伏笔,男主角曾问过老伯会不会游泳,老伯说我不会,男主回答的是“那挺好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回答很奇怪。原来此时男主就已经握住了一把钥匙:能让他的故事更戏剧性的钥匙。
面对男主的杀意,老伯先是以为他开玩笑,一边说不要开玩笑了一边假意挣扎。没想到男主真的铁了心要杀人灭口,老伯此时才声嘶力竭地求救,之后慌张逃跑。从演员自然又细致的表演上不难看出,导演对影片中人物关系的把握非常准确,演员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演什么。这就让一个略显荒诞的一幕幕看起来又那么真实。
上学期在report里我写过探讨艺术电影的价值。假如“娱乐电影”是为了消磨时光,那么艺术电影的存在是为了促使我们去思考。想必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因着只在课上就着日文字幕看了一遍,有疏忽的地方请包涵。不过约莫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不多,如果因为这一篇影评产生了兴趣,不妨一看。
<严禁任何形式的演绎、复制及转载>

原文地址:
威尔海姆,一个人,登上了白雪皑皑的茨库秀比斯山,寒冷,寂静,也是孤独,当登临高处,当俯瞰底下,油然产生的却不是超然感,而是回到原点的寂寞感,“这也就是一个人原来的生活,站在山上等着,并没有暴风雪——当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感到寂寞,这好像只是我一个人没有意义的歧路。”登上高山,威尔海姆是为了寻求暴风雪的刺激,感受大自然的暴力,而从这一种刺激和暴力中,他分明想获得写作的冲动,由此成为一个“作家”——一种身份的界定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窠臼中挣脱出来,但是在没有暴风雪、寂寞的一个人世界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改变。
被命名为“没有意义的歧路”,威尔海姆终于发现自己刻意为之的写作之路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甚至还是回到了一个人的原点,当发现站立于世界的尽头就是原来的生活,这一趟寻找之路对于“作家”来说,就是一次失败,但是这失败的“错误的举动”却并不是没有意义,它以歧路的方式打开了面向自己,面向世界的方式,无意义的意义,就如写作本身一样,并不在于写下和过去有关的记忆,和现在有关的迷惘,和未来有关的失语,而是在写作本身——在于登临这并没有暴风雪的茨库秀比斯山本身,在于从起点出发回到原来生活的经历,在于发现“没有意义的歧路”而有所感悟。
改编自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那题辞便是:“我们如何分离?在茫茫人海中。”而这一句话就出现在威尔海姆做出一个人去登茨库秀比斯山的时候,这趟旅行最后以分散的方式结束,胖诗人贝隆一个人朝火车站奔去,他大约要去寻找新的诗歌;老头布洛海鲁姆几乎是被威尔海姆赶走的,在船上威尔海姆想要把他推下河,挣扎着的布洛海鲁姆听到威尔海姆说:“过去的水也很澄净。”然后开始流鼻血,一年一次的流鼻血是布洛哈鲁姆命名的“液体的本命年”,于是看到他流鼻血的威尔海姆松了手,布洛海鲁姆便趁机离开了;而剩下的女子塔莉莎和女孩米妮先是跟着他,但是当威尔海姆说自己想要去爬茨库秀比斯山的时候,塔莉莎问了一句:“挽留不行吗?”终是不行,于是在大街上她们和威尔海姆分离,这一分开便回答了那句题辞:“我们如何分离?在茫茫人海中。”——分离就是分离,茫茫人海终究会选择一个人前行,一个人登顶,一个人发现“没有意义的歧路”。
选择和茫茫人海逆反的方向行走,就是威尔海姆这一次旅程的终结,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看不到”的状态中,而从起点回到终点,在茫茫人还中和“他们”分道扬镳,是不是新的书写的开始?是不是真正成为了作家?这是威尔海姆在某种意义上的成长,当他在最初的时候陷入孤独的时候,他是想用写作来逃避现实,这是另一种写作,其实是一种没有走进现实的写作,闭门于一种想象和虚构:他看见外面飞过的直升机,听见唱片里的音乐,看见和听见,都像发生在一个人的世界之外,都是一种隔绝的存在,甚至他自己也沉默着,“两天没说什么话了,好像舌头也没有了。”正是这种找不到存在的感觉,让威尔海姆选择了另一种极端,他狠狠地用拳头击碎了玻璃,血便流了出来,他慢慢舔着血,仿佛要从这血腥的味道中寻找灵感,但是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建立在自身受伤的虚无主义之上,就像母亲对他说的那样:“要成为作家,最好不要忧郁和不安。”无疑自残式的写作是失败的,于此,他踏上了远行之路,开始了对现实的真正体验。
这一次出行是富有深意的,一方面威尔海姆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找不到一种存在感,想成为作家当然只是想象,“出发的那天,看到家乡的街道,没有什么感觉。”仿佛麻木了一般;另一方面开始这次出行是母亲的想法,她为威尔海姆准备了两本书,关于感情的书和生活的书,还为威尔海姆买好了车票,临行前拥抱着他,母亲说:“你看过书之后再决定吧。”书是一种知识的存在,是对于现实的指导,车票代表着一种现实生活,母亲为他出行所做的准备更是证明了威尔海姆曾经生活的虚无,而告别虚无开始旅行,他到底去向何方,到底前往何处,大约连母亲也不知道,威尔海姆几乎开始了一种无目的的旅行。但是当他坐上了火车,当他打开了书,认识现实的那条道路便在他面前展开了。
他翻开的书第一章写着和“父亲”有关的生活,那是一个“水车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的世界,那里有小鸟的叫声,有慢慢融化的雪,一切似乎是美好的,但是,“父亲出去了。”出去的父亲,实际上预示着这个打开的世界是要寻找父亲,父亲是什么?是记忆,是历史——这一条旅行之路就是关于威尔海姆进入历史面对现实朝向未来的路,而威尔海姆的出行、寻找甚至发现“没有意义的歧路”代表着德国青年的成长历程——当战后的一代寻找生活的意义开始书写德国的现在和未来,他们其实都面临“父亲出去了”这一境遇,就像维姆·文德斯出生于1945年,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空白,历史之中的父亲当然是缺席的,所以在开启第一章的旅程中,威尔海姆代表着战后一代审视历史的开始。
在这一次旅途中,威尔海姆遇到了像“父亲”一样的老人布洛海鲁姆、在痛苦的孤独中被认错的那家宅子主人,他们都代表着经历了战争的一代人:在火车上,布洛海鲁姆就告诉威尔海姆列车长认识他,他没有车票照样乘坐了火车;之后从那家宅子出来一起散步的时候,布洛海鲁姆更是明确说到列车长是自己的副官,言下之意他就是一名老兵;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会唱歌的犹太人,“他帮了我,我杀了他。”从这里可以看出老人过去可能是一个杀死过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而当战争结束,他的身上无疑带着历史的罪恶,所以在威尔海姆面前,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流浪歌手,和年轻女孩米妮一起,避开人们的目光,也为了避开历史——在最后威尔海姆来到地铁站的时候,就看见布洛海鲁姆戴着一副墨镜,一种遮蔽的存在,就是对于历史罪恶的逃避。
当威尔海姆遇到这样一个“父亲”的时候,他急于想知道如何书写一部历史小说,而这部历史小说无疑就是一部政治小说,“政治我不知道,政治家不满足的东西会在文学中得到表现,人的欲望也一样——把政治和文学结合起来就好了。”威尔海姆是想在政治小说中发现人的欲望,而他认为欲望都是一样的,但是,布洛海鲁姆告诉他的却是一种存在于过去的政治小说,“过去就是过去的时代,寡言和无悲伤共存,这就是政治小说。”把政治变成一种寡言和无悲伤共存的东西,把政治小说安放在无法回去的过去时代,布洛海鲁姆就是要把那段历史锁在“过去的时代”,也以此逃避自己犯下的罪。但是这种逃避、寡言和无悲伤,却以另一种方式连接到了现在,那就是“液体的本命年”的鼻血,每年一次成为一种病态,甚至后来越来越频繁,足以说明历史的罪恶本身是无法遮掩的。
与布洛海鲁姆一样,宅子的主人也是经历了“过去的时代”的人,但是和“过去就是过去的时代”的逃避和遮掩不同,宅子的主人却走不出痛苦,自己的妻子因为患病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而居住在偏僻乡村的他,也被孤独包围着,对于他来说,这种孤独是一种被国家主义异化的孤独,他欢迎这些人入住家里,在壁炉前他和威尔海姆说起了自己的孤独,这是“德国的孤独”,他说,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传统世界,为了超越不安,所有观念都被导入到了日常生活中,勇气、忍耐、勤奋都成为一种美德,这是这个国家的哲学,但是在过去的时代,犯罪却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存在,人们的虚荣带来的羞耻心消失了,“所以在德国很孤独。”说着这段关于孤独的国家哲学的时候,他用笔在自己的手心不停地戳着,而最终手心里流出了血。
犯罪成为一种合法化存在,这便是他所认为的国家哲学存在的悖论,在这个无法摆脱的孤独面前,他有用自残的方式表达着无法走出的痛苦,一样是血,布洛海鲁姆在“液体的本命年”中选择了逃避,而宅子的主人却以极端的方式逃离痛苦——在威尔海姆、布洛海鲁姆以及其他人一起外出散步聊天的时候,枪声响起,在第三次响起才让他们警觉地结束对话返回屋子的时候,宅子的主人已经吊死在楼梯上,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跟随着妻子的脚步而去,是精神疾病无法治愈的结果,但是上吊是不用打响了枪声的,三声容易被忽略的枪声又从何而来?也许这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警示,更多陷在德国式孤独中的“父亲”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过去。
布洛海鲁姆和宅子主人是“过去的时代”的象征,而胖诗人贝隆也代表着过去,他是因为诗歌才和他们在一起的,他也朗诵了自己的诗歌,在他的诗歌里是腐烂的蘑菇,是阴暗的下水道,是“垂死挣扎的我”,这些意象的存在对于一个醒不来的诗人来说,似乎代表着青年一代的迷失,胖诗人和威尔海姆的年纪相仿,他本应代表着现在的青年,但是很明显,他对于现在是“未醒”的状态,在大家醒来各自谈论起昨晚的梦境的时候,贝隆却说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但接着又说想起了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在现实中失语,他却被笼罩在“叔叔”的阴影下,正是他推荐说自己叔叔有一幢别墅,他邀请大家一起去,但是当进入那间房子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拿着猎枪的宅子的主人,贝隆这才告诉大家自己弄错了,那个人不是自己的叔叔。叔叔被弄错了,这种阴差阳错正是贝隆代表的一代在腐烂的蘑菇、阴暗的下水道、“垂死挣扎的我”的意象中活在错误的过去,而他最后选择奔向火车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逃离。
布洛海鲁姆和宅子主人,以及被叔叔影响的贝隆,都是过去时代的存在,他们以逃避、自杀和逃离的方式介入到现实中,而现实这篇文章到底如何书写,对于威尔海姆来说,它提供了一个现在的样本,那就是塔莉莎,这个在威尔海姆一上火车时就注目却乘坐在不同列车上分道扬镳的女人,最后还是和威尔海姆走到了一起。威尔海姆希望成为作家,而她则是一个演员,他们的相遇有着最现实意义的爱情发生可能,塔莉莎对威尔海姆说:“自己就是自己,不要去管陌生人。”她甚至一开始就认为威尔海姆就是一个作家,但是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交错总是发生:火车似乎一开始就开向了不同的轨道,彼此注目却朝向不同方向;之后虽然又遇见了,威尔海姆说:“我想和你一起在街上奔跑”,但是旁边却跟着不同的人,他们两个人并排行走的对话变成四个人甚至五个人在一起的混乱;在宅子的那个夜晚,威尔海姆悄悄走进黑暗的屋子,他以为这是塔莉莎的房间,却不想抚摸着的女人是米妮,他打了他一个耳光,接着又抚摸了他的脸;在最后山脚下的屋子里,他终于为塔莉莎盖上了被子,塔莉莎告诉他:“我很迷惘,但是我爱你。”当爱情终于要发生的时候,塔莉莎却说:“我不喜欢一个永远冷漠的人。”
爱情在交错中终于没有发生,这也是现实的歧路,两个年轻人在现在的世界里,其实生活在不同的状态中,威尔海姆对于现实的书写,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背负着对于政治小说的迷惘,对于国家哲学的迷失,对于身体伤残的体验,但是在塔莉莎看来,“自己就是自己”的人生观趋向于一种自我主义,在宅子里醒来之后每个人都说到了梦,塔莉莎说起的梦是关于自己的,“我梦见自己穿着冰鞋,北海结冰了,我向前滑行,最后掉在了冰里。”一个人的梦,一个人的滑行,一个人的掉入,需要的是一种爱情式的解救,但是这种解救是为了实践“自己就是自己”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为了诱惑威尔海姆,但是以梦的方式表达这一种爱情的渴望,对于塔莉莎来说,就成为了表演,而身为演员的她,所强调的也是“台词生活”——梦和台词装扮着生活,其中当然有虚假,甚至有虚伪,所以当威尔海姆想要获得写作的灵感时,塔莉莎却走向了另一条路,她撕掉了威尔海姆写下文字的纸,她拿起了刀想要“杀人”,她拒绝了和他一起去茨库秀比斯山,就像那个掉入冰里的梦一样,她最后告诉威尔海姆这是一个骗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看不到。”塔莉莎的这种自我主义现实观,完全是一种悬空的存在。
当历史在布洛海鲁姆、宅子主人、被叔叔影响的贝隆身上体现出对现实的逃避、自杀和逃离,当新一代的年轻人又以自我为中心构筑起悬空的存在,未来又会走向何方?无疑米妮便是未来的代表,这个被布鲁还鲁姆称为“艺人”的女孩是纯洁的,是可爱的,是真实的,她会面带微笑用双手倒立、抛球展现技艺,她会毫无掩饰地靠在威尔海姆身上释放喜悦的心情,她被打了一个耳光而不会报以愤怒,但是这个和象征着“过去”的布鲁还鲁姆在一起的女孩,这个最后和“现在”的塔莎莉一起离开威尔海姆的女孩,并非是未来的符号,因为她身上体现着最残酷的一个特点便是失语——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只是在用身体的行动和表情来回应这个世界,当未来成为一种失语的存在,是因为无法从历史造成的阴影中安然走出,是因为无法在现在的迷失中言说,而这也正是渴望成为作家、希望用书写的方式言说命运的威尔海姆陷入的困境。
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时间的一条轴线,它是不可断裂的,“我们如何分离?在茫茫人海中。”如何从过去找到未来的方向,是一个国家的时代命题,有人自杀,有人逃离,有人失语,但是即使这一段旅程最后还是回到了一个人的原点,还是没有能迎来暴风雪摧枯拉朽的改变,还是走了一条“没有意义的歧路”,但是一个人登临,一个人俯瞰,一个人经历了成长,本身就是一次书写,一次对政治之外自然的真正拥抱,就像那本书的第一章,在一个“水车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的世界里,在小鸟的叫声和慢慢融化的雪组成的美好中,父亲并没有出去,父亲又回来了。
第15届##无人知晓单元第7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错误的举动》,下面请看前线出走之人们走向惆怅的评价了!

松野空松:
孤独从城市往乡间蔓延。
果树:
与系列的其他影片相比,诗意全无,黯淡无光。
DudeLebowski:
有些刻意和突兀,但在文德斯强烈风格的加持下观感还是很好。
donnie:
文德斯的群戏公路片。互相不能理解的人们曾经在一些瞬间共享孤独。
节南山:
摄影非常美,隐喻太过晦涩,成功让我在高强度观影中获得美好的补觉时间。
kc512:
哑巴女孩、纳粹老人、写诗小胖,这三个角色几乎就是男主角內心人格的外在化,而男主角又代表了战后一代日耳曼男性,迷恋童真、嫉恶如仇、却又嫌弃自我。
子夜无人:
其实并不那么“公路片”,尤其要比起《直到世界尽头》的话,几乎完全放弃了对于外部风景装点门面式的表现,而是仅仅延伸人的情绪本身。只要有那种无限的孤独和惆怅,我就好像永远踏在旅途上;同是天涯遇到的沦落人,每个人悬在头顶的包袱都在击碎一个文艺青年的终极梦想,写诗的手残废在了挖掘生存空间的土壤、去到远方的路又才刚刚塌方,他们聚在一起说着彼此都听不懂的话,沉闷却装作相谈甚欢。
DAY7的无人知晓场刊将在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对于德勒兹,电影理论就是一种哲学,换句话说,“电影理论并不‘关涉’电影,相反,它与那些电影引发的哲学相关”。因而其电影理论与哲学之间是一种生成的关系,其对电影史的梳理实际上也是一种电影-哲学的间性梳理,既不能将其归为外部化的哲学梳理,也无法归为一种纯粹内部化的电影梳理。
通过以二战为节点,德勒兹将电影史梳理为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两大类型,二战的摧毁性使得人类的思维处于一种惊鄂的动情状态,在世界的废墟之中游荡徘徊,茫然不知所措。巴塔耶在对耗费的推崇中,指出祭祀的行为可以使得人类在缺失的震撼中,获得跳脱理性的拘囿,获得新的精神解放的可能。而在德勒兹这里,战争作为一种巨大的耗费则使新得影像亦即时间一影像成为了可能,人类的精神、电影的神韵,伯格森的时间不再只是通过一种传统线性感知-动情-冲动-运动的方式间接捕捉,而是在影像中直接呈现出来。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无疑成为了德勒兹这一分类的有力佐证,那些影像里的人在被战争摧毁的,废墟一般的世界里游荡,不再是在一种情节、戏剧化的推动下行动,进而获得看似圆满的结果,而是永远处于一种浑噩的情绪里(例如《偷自行车的人》,在结局重新回到一种无法行动的困厄之中)。德勒兹在书中指出这类新影像的五种明显特征:弥散性的情境、有意弱化的(事件或空间)链条、旅行形式、对俗套的意识、对情节的抵制。
在文德斯的“公路三部曲”《或错误的举动》、《公路之王》和《爱丽丝漫游城市记》,甚至那部美丽的《德州巴黎》无疑成为德勒兹的晶体-影像(时间-影像最为重要的形式)。而这部《错误的举动》无疑成为德勒兹阐明自己观点的绝佳文本——那个想成为作家的青年在结尾也说出了电影的真正主题:我只想一个人独自回到自己的浑浑噩噩之中。其一系列举动似乎均是一种丧失了行动意义的错误举动,并非对于情境而动的理性行为,而是一种虚假、错误的选择和游荡。
而作为观影者,也不要以一种传统的,通过纯粹故事化的传统观影方式理解这样一部,即使是今天也属于的“新影像”,进而得出晦涩难懂的结论,我们需要跟随主人公,一起游荡在漠然的城市、有士兵的荒野、有着想自杀的主人的房屋,并带着一种略为忧伤同时又很漠然的感性,共同观察、体验一种纯粹的“视听情境”。
或许这样,这类电影就好理解多了!
参考:德勒兹《运动-影像》、《时间-影像》
《德勒兹与巴迪欧电影理论比较研究——— 以文德斯《虚假的运动》为例》,作者:胡新宇
201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