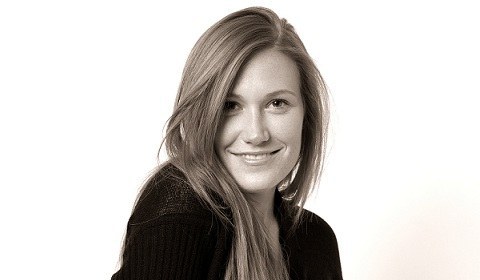悸动的心 Restless(2011)
简介:
- 伊诺(亨瑞·霍珀 Henry Hopper 饰)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生活毫无兴趣,却喜欢在陌生人的葬礼上游荡。在一次葬礼期间,他偶然邂逅了一位独特的女孩安娜贝尔(米娅·华希科沃斯卡 Mia Wasikowska 饰),两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诺向安娜贝尔介绍自己的一个鬼魂朋友浩(加濑亮 饰),安娜贝尔则与伊诺分享她为之痴迷的达尔文学说。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两人关系日渐亲密,生活的乐趣也慢慢复苏之时,安娜贝尔告诉了伊诺一个事实——她是一个将不久于世的癌症病人。面对着一边是难以割舍的韶华时光,一边是无法改写的死之永夜,这段不寻常的爱情将以怎样的方式对抗生命的流逝……
演员:
影评:
- Gus Van Sant的电影一向对死亡都有所触碰,这部电影更是直接探讨死亡。
《Restless》有着各种与死亡相关的内容:葬礼、绝症、车祸、鬼魂、停尸间、万圣节,还有大一点的战争与进化论。但重点还是落在了“生”的上面。男孩对身边亲人死亡的拒绝,直到露出接受爱人去世的微笑。
影片以某种“小清新”的方式,却一改小清新电影的明亮、鲜艳、透彻,营造出一个光线有些不足、色彩有点萧瑟(却不失丰富),整体影像质感跟大多数电影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关于死亡,一向是困绕人类的最终极问题之一。而死亡的问题,更多不是死的那一刻(那一刻也许只有一秒),更多是生者对死的态度。也就是你该如何活着。
对死亡的恐惧,一向是创作的重要来源。但这部电影很少展示恐惧,大多数是茫然、悲伤与不接受。而女孩直接面对死亡,更多展现的是平静与坦然。我想大多数人应该都想以一种平静甚至是温暖的方式来迎接死亡,但事与愿违,因为我们精神上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牵绊,更别提肉体的痛苦。
这部电影的力量,也许是“轻”了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些生的乐趣和死的平静,对现代人有一定治愈效果。虽然从开始就在讲爱情,但这部电影却不止是一封情书,更是面对死亡的写的一首小诗——就像日本飞行员最后的那封信一样。时间流动,生命的温暖与哀伤并存,悲欣交集。
生需要诗,死同样也需要诗。 
作者:Stéphane Delorme 英文译者:David Davidson 翻译:Annihilator 原文地址:
全文约3000字阅读需要10分钟
我们因何而喜爱一位电影创作者?当我们面对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的美丽新作时,我们多半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对于使这位波特兰导演成为同辈中最重要的导演的那三部电影——从《盖瑞》(Gerry)到《最后的日子》(Last Days)——我们并没有感到这般的震惊。但如今,我们发现了其他电影创作者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种自信、有把握且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个人意愿和接受挑战的驱使下创作作品。
几年前,格斯·范·桑特凭《大象》(Elephant)登上了业界的顶峰,但他并没有试图自缚于作者或超级作者的姿态来超越自己。这曾经发生在过去几位戛纳获奖者身上,他们的平步青云使其作品的形式变得僵化(如文德斯、莫莱蒂、阿莫多瓦——我们期待他们的新电影)。格斯·范·桑特似乎不是这种傲慢和忧虑的受害者,公众的认可似乎不会影响他:他无需证明自己,他着陆、并再次惊人地出现,出现在旧金山的嬉皮街头(《米尔克》(Milk)),出现在一家繁忙的星巴克的等待队伍里(一部与汤姆·汉克斯合作的未完成项目),或一部像《爱情故事》(Love Story, 1970)那样的感伤的情节剧中,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将《悸动的心》(Restless)与阿瑟·希勒的电影相比较。
 Restless, 2012
Restless, 2012我们喜爱一位电影创作者,是因为其风格,也同样是因为其选择执导哪些电影的姿态。当科波拉在80年代从事一些项目时——他甚至不担心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只是工作任务——他创作了自己最好的一些电影,同时加强了自己的电影风格;他创作了一部迪士尼电影(《家有杰克》(Jack)),然后停下来,在自己家里重新开始创作电影。或者像林奇,他从《妖夜慌踪》(Lost Highway)转向了《史崔特先生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很多电影创作者一旦到了50岁(格斯·范·桑特已经58岁了),就不再在乎姿态,而是一边前进,一边回头沉思于其既往作品的遗骸之中。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人来说,姿态似乎是被一种难以准确表达的个人挑战所驱动的,以防止作品序列变得故步自封。作品类型的不断更新并不同于古典制片厂时代的导演的情况,后者被项目所束缚,同时保持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霍克斯作为作者的标准模式);它是一种选择,一种必要的能力,去加速减速,沿着自己的航线去航行,去驶过暖流或寒流,永不停歇地穿越河流。
为什么选择拍摄《悸动的心》?但又为什么选择拍摄《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或者《盖瑞》?或者《惊魂记》(Psycho)的诡异翻拍?首先是制作一部聚焦于异性恋情侣的亲密电影——这是导演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类型——并用好莱坞模式讲述这个“爱情故事”的欲望和挑战。可以想象,这会引起《最后的日子》的影迷们的批评,他们会认为这部电影缺乏野心。但是格斯·范·桑特重新发现了行走电影(walk-film)这一形式,这遵循了他的“年轻之死”三部曲(《盖瑞》《大象》《最后的日子》)中的事前验尸(pre-mortem)原则:故事讲述一个受父母去世困扰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只剩几个月可活的年轻女人。导演自此讲述了他们这几个月内的友谊。

然而,把这个主题简化为此前的死亡三部曲中的死亡倒计时是可惜的。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三部曲对于必将来临之事的使用方式的独创性。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悸动的心》的独创性。他试图做的,比拍第四部由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拿着斯坦尼康拍摄不快乐的青少年的作品还要困难。这是因为格斯·范·桑特害怕循规蹈矩。挑战在于从这个沉重的主题中提炼出情节剧,从患癌青少年向感伤喜剧(sentimental comedy)的转变。挑战在于混合不同的基调。必须最大限度达到平衡以维持这种脆弱的均衡,包括了演员身体性的脆弱以及导演的极度精妙的选择。这种轻盈的均衡在琐碎细节、低级趣味和死亡临近所带来的变态迷恋中滋养自身。格斯·范·桑特因此在《悸动的心》中找到了两个美学层面的挑战:纯粹克制的愉悦,他很少停留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以及不同类型的混合(情节剧和感伤喜剧),他之前已经为此种混合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范式——虽然其风格或许没有此般流畅——即他那部梦幻般的《我自己的爱达荷》(My Own Private Idaho, 1992)。
 My Own Private Idaho, 1992
My Own Private Idaho, 1992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格斯·范·桑特的作品序列(越来越多地?)具有道德色彩。他想要变得有益:《米尔克》的拍摄是为了捍卫一桩事业,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各种教诲意味的观点(一个晚上打电话寻求安慰的同性恋残疾青少年)。《悸动的心》提出了一种启迪人心的学徒期:对于来世的学徒期,而这部续集没有他先前的三部曲那么地充满毒污。它几乎是解药。就像对于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一样,这种对青少年的迷恋因其来源于善意和保护的道德立场(好像导演在说:“小心”)而加倍。这部电影想要变得快乐,它在男主角父母的突然去世后为其提供了一次和解。在导致父母去世的事故中,他陷入了昏迷,他承受了双重的罪责,既幸存了下来,又没有出席他们的葬礼。整部电影都基于这一创伤,基于这一疗愈。他曾经没能来得及吗?现在他有的是时间(三个月)来与他及时遇见的这个年轻女孩告别,为她送行、陪伴她。死去的是她,但安息的是他。

为了实现这一点,这位电影创作者选择进入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即使这一领域早已深埋于他的某些电影之下——那就是奇迹的领域。这种奇迹之感在万圣节的森林里的一个伟大场景中达到了顶峰,男孩扮成日本飞行员,女孩扮成艺妓,他们重演了一部日本鬼片中的一个场景。选择米娅·华希科沃斯卡(Mia Wasikowska)出演是明智的,因为她仿佛还穿着蒂姆·波顿(Tim Burton)《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2010)中那个仙女般一样的服装: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女演员,她带来了一种信念,打破了这个主题下潜在的感伤。珍·茜宝(Jean Seberg)一样的发型,麻雀般的头,男孩式的穿着,她有一具雌雄同体的身体,这在爱丽丝与约翰尼·德普的滑稽形象的爱情中已经显而易见。男主角(亨利·霍珀(Henry Hopper))看起来像一个没有王冠的国王,他与姑妈住的大房子看起来和《最后的日子》中的那个一模一样。还有第三个角色,他非常奇怪,强调了一种日本的幻想:浩,一个神风队队员的鬼魂,自父母去世以来一直陪伴着男主角。这位同伴对这位年轻人的现实施加了魔法,但他加重了故事中的死亡的概念。在《大象》的非凡的开场中,一个儿子询问父亲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楚克环礁的经历,而在得到回答之前,这个青少年说:“我去过那里”——但他怎么可能去过?这句神秘的言论激荡起战争无所不在的事实,激荡起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档案影像的毫无缘由的侵入。

《悸动的心》的魅力还在于导演独一无二的场面调度:秋天的颜色穿过树林染上了米娅·华希科沃斯卡的宽大睡袍,构图如同投注于角色的友善的凝视,就像朋友的手放在肩上;随着情节展开,出现了一些处于焦外的形象,比如当这对情侣站在父母的墓前时,墓碑上两只羊并排的幼稚雕塑。传统手法同样存在,尤其是音乐,但是它们被天才的构思所弥补:比如年轻女孩的第一次病发,她话说到一半,甚至没有哭喊,就以一种无限暴力的姿态向后倒下;或者,在她死前的一个场景中——与所有好莱坞电影中都有的那种医院场景完全不同——她只是简单地问他,“可以吗?”,就像是在问“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你会没事吧?”

但在这部光芒四射的影片中,最奇怪的是亨利·霍珀的存在。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随时有可能呈现出他父亲——丹尼斯——的特征。他只需稍稍眯起眼睛,我们就会回到1955年,《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的年代。当影片的片尾字幕结束,出现了对丹尼斯·霍珀的献词时,一种更深的情感吞噬了整部影片,仿佛影片的故事就是这位角色的背景。这对父子之间的相似性增强了它的力量。
往期推荐

- 如果说看电影要有代入感,那你想为自己挑选哪个角色?
在《Restless》里,我想我不会是女主角,皮肤白白手脚长长的,执着地喜欢着水鸟,想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寿命。
我也不能成为男主角,喜欢用粉笔画出自己身体的轮廓,弄出好像事故现场一样的线条;拿锤子打碎父母的墓碑,悲伤而又愤怒地问他们为什么要丢下他。
我想我只能是男主角身边的那个鬼魂。每天和男主角一起拿石头扔火车,一次次地在游戏中取胜于男主角,在偶尔听到“长崎”之后,默默地坐在浴缸里,梳理自己在人世的那些回忆。我身上永远穿着战争时的制服,上面是被浓烟,弹孔,血迹弄出的破旧感。我站在鲜活的世界里,我的人就像我的衣服一样和这世界格格不入。
或者我甚至连他也不是,我只是另外一个不知名的鬼魂。我飘荡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年代久远,我已经逐渐忘记自己尘世的记忆,又或许即使我想起来,我曾经确实拥有的人生也像现在一样是虚无而又不值得回忆的,我活着时无法用力抓紧我生活的土地,就像现在我孤独地飘荡在空气里,也抓不住一个可以和我聊天的少年。我在画面里,但是没有人能看到我;我想开口说话,但是没有人能听到我。
看过太多一见倾心或者是日久生情的爱情故事,少年,中年,老年,他们都会遇到各自命定的爱情。我曾经渴望拥有《The notebook》里诺亚为艾莉修建的白色房子;我曾经想得到《Love me if you dare》里于连和苏菲打赌用的好看的盒子;我曾经幻想自己是《天使爱美丽》里的Amelie,用一些奇怪的花招让尼诺来追寻我的线索;我也希望自己是《重庆森林》里的阿菲,偷偷换掉编号633的警察房间里的生活用品,以这样的方式慢慢进入他的生命......
他们说要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为你准备的,你总会等到心灵契合的另一半。他们说其实爱情寻找的就是自己的影子。那么,如果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么也许我们会开始怀疑自己这个实体的存在,也许我们会慢慢变成影子,变成孤独的鬼魂。
伊诺和安娜贝尔排演浪漫的死亡剧情时,伊诺说:你再等等,我马上就来。说完就作要切腹状。安妮十分不满。我想说,如果我是安妮,我会很感动很感动,虽然我也会劝他:你要好好活下去,活着就一定会遇到好吃的。但是谁知道呢?和心爱的人一起死去,活着孤独地活下去,哪个更好?
PS:自己很喜欢片尾博史写的那封信,但是网上没有搜索到台词的英文版,所以对照电影的中文字幕,自己勉强听了几遍试着写下英文版,希望错误不多。
As I write this letter,
the ocean breeze feels cool on my skin.
The very ocean is soon to be my grave.
They tell me I will die a hero that safety and honor of my country will be rewarded of my sacrifice.
I pray they are right.
My only regret in my life is never telling u how I feel.
I wish i were back home
I wish I were holding your hand.
I wish I were telling you that I have loved you ,
and only you since I was a boy.
But I'm not.
I see now that death is easy.
It is love that very hard.
As my plane dives i will not see the faces of my enemies.
I would instead see your eyes,
like black blocks frozen in rain water.
They tell us that we must scream "ばんざい" as we plunging down to the target.
I would instead whisper your name.
And in death as in life,
I will remain forever yours.
我写这封信时
清凉海风轻抚我的皮肤
这片海洋将会是我的墓地
他们告诉我我会壮烈成仁
我的牺牲会带给祖国安全跟荣耀
我祈祷他们说的对
我人生唯一的遗憾
是从没告诉你我的感受
但愿我能回家乡
但愿我能握着你的手
但愿我能告诉你我爱你
我从小就认定你了
但我食言了
如今我发现死很容易
找到真爱却很难
当我的战机俯冲
我将看不见敌人的脸
我宁愿想象你的双眼
仿佛雨水冻结的黑石
当我冲向目标
他们说要高喊“万岁”
我宁愿低语你的名字
无论生死
我永远都是你的人 - 格斯-范-桑特眼里的青春,总是弥漫着一股青草地上的水汽,介于清澈与暧昧之间。即使是那部残酷冷峻的《大象》。《无法安宁》讲述的是另一种残酷:命运的不可逆转,成长的无可奈何和生命中难以面对的伤痛。所幸,本片里,青春的戾气从这残酷之中突破重围,坚定顽强地守卫着我们心中的柔软。
伊诺克是个跟同龄人不太一样的男孩,他不开车,也没有车,有一个陪他混日子的日本鬼魂哥们高桥宽(加濑亮饰),有去参加陌生人葬礼的癖好,在一个葬礼上认识了患有癌症的安妮贝尔。安妮贝尔开朗独立,行事果敢大胆,用高桥宽的话说,怎么看都是个男孩。两人在平淡清闲的生活里相伴相爱,迎着那个已知的黑洞从容而行。
死亡,我们究竟应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它?有没有指导手册?死去的少年背负卫国的荣誉,死过的少年被阴影缠绕,将死的少女却平静从容。迷茫隐痛的人生,究竟有没有通向豁然开朗的捷径?格斯•范•桑特用最平实手法,用这样三个少年与命运纠缠博弈的故事,给予出一个生命的态度,竟然跟《功夫熊猫》里给出的一致;伤痛是会愈合的。
好像有那么群孩子,在他们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这段青葱岁月,总是特别敏感,视伤痛为特立独行的标志;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人,因为经历复杂离奇或是荒谬,当然,重要是他们在成长的途中痛不欲生。然而,当他们长大成人的那天到来,回首望去,痛苦却是全部灰飞烟灭,只剩下各种逗趣和美好的事情。一如伊诺克在安妮贝尔葬礼上,只有会心一笑。
安妮贝尔跟伊诺克,由于被提前告知了结局,而格外珍惜他们的这段时光。所幸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痛上,而是极尽所能地敞开心灵,享受青春,快乐得像两只草间的昆虫。伴随着美妙得让人身心酥软的一首首歌,或美国乡村,或法国独立;片中没有一首歌让你觉得,死亡跟青春有什么关系。这是事实。死亡伤不了青春一根汗毛。青春那样美,美得像一条甜蜜的河。
相比金棕得奖影片《大象》,或是奥斯卡得奖的《米尔克》,本片的视听和叙事手法,都略显简单,没有令人惊艳的内容或风格。只在开场有那么一个瞬间,仿若回到久远的爱达荷。或许因为,导演觉得这样的表达更贴近成长,贴近死亡。更或许因为,朴实与简单,更贴近青春。因此,此片定不会成为经典小说,只能是篇哀而不伤的清新日记。
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