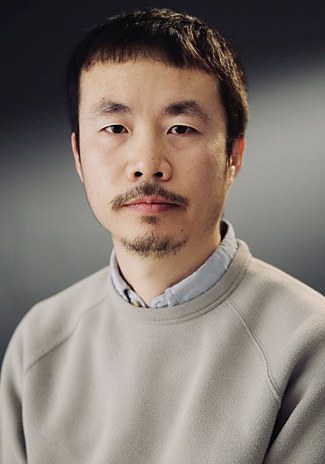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
简介:
- 老马(马新春 饰)是村中有名的木匠兼画匠,到了73岁时他已不再下地干活,平日里除了在村口看看牌局、聊聊天,就是和村里另一名木匠老曹一起做棺材生意。但现在政府大力推行火葬,越来越少有人来寻两个老人制作棺材了。老曹近一年觉得自己身体状态很差,遂找了老马为自己制作了一个画着仙 鹤的棺材。做完这一副棺材,老马就去女儿家过中秋节,回来时老曹已驾鹤归西。老曹的尸体被偷偷埋在槽子湖旁的玉米地里,老马来这里拜祭,回去之后宣称自己在湖边看到了仙鹤。老马偷偷告诉孙子他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将自己埋在槽子湖边,待某日仙鹤将他驮到天上去……
演员:
影评:
- 【剑南春梦游记】之一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观后随感
电影很不错,应该说相当不错。
电影蕴含有一种深沉的诗意,导演是个很聪明的人,或者说很有悟性,有智慧。在此之前我听别人跟我说,是个女导演拍的,我看的时候就想,这不会是个女导演吧,不太可能。我就猜是个男的,口齿比较笨拙或者略显傻气,不太能说会道那种。看到人也觉得差不多,他还是不算太能说,呵呵,他如果太能说会道,非常有条理有语言感染力的话,那就似乎有点太显聪明了,就有点与他的悟性不太符。再或者他是既有慧根又伶俐那种,那就又太晶莹透剔,太厉害了,似乎就不太会拍出这样的片子。
因为他太冷静了,也可以说是隐忍,在他的这个电影里,处处透露着算计,每个细节都非常精心安排,电影看似节奏缓慢,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多余冗余的地方,每一处都有讲究,有往后的铺垫。比如说,他拍前面的孩子们的童趣,天真可爱的嬉戏村景;拍那个女孩子捉蜜蜂被蛰了手,暗示这个女孩非常童真(她甚至不知道蜜蜂会蜇人);拍那个老人家的子女如何处理上一代人关系,如何处理下一代人关系;拍老人家如何与他们无法沟通,以及与同岁数的其他老大爷都无法沟通……包括他说的,堵烟囱,用以表现老人的一个潜意识的心理;包括那个骑棍子的小男孩,智娃(这个名字也起得很好),其实这两个段子多像阳光灿烂的日子,呵呵,骑棍子的傻子,古伦木欧巴。当然,导演不一定是参照或COPY了这些段子,但是无意中体现了类似的隐喻。
可以说,导演是个非常细致的人,每一处的段落都承上启下,往后铺垫,但是很奇怪,你不能说他是细腻,只能用细致,非常精心设计的细致。他这个电影,悟性高,精心,但是却总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不太对,差点什么。如果说的话,也可以说出一二三四五来。
比如,第一个地方,他拍到老人家和小男孩看见仙鹤的时候。我们知道,仙鹤这种东西的意象,那是非常形而上的,在中国文化的意境里,那是有仙寿恒昌的意思(不是福寿永昌,不好意思,记忆力有时会靠不住,连百度有时都会骗人—_—#)。在西方人那边,可能会是上帝的天使,终极价值,这一类东西;在中国人这里,那是生死,那是芳龄永继,那是仙寿恒昌,是非常有神秘色彩的,甚至玄而又玄的东西。所以,这个电影里其实最好是不要出现有仙鹤,它不露面那是最好。比如说白鹿原里面的那只白鹿,那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意象的东西,它神秘、美好、吉祥,令人向往,但是它从头到尾在书中都没有确切地出现过。它代表了某种形而上的终极,在中国人眼中或许就是宿命,是仙境一般的极乐世界。苏童的小说里也没有出现仙鹤,他也没有说那个仙鹤确切的存在。所以,如果非要出现仙鹤不可——毕竟电影与小说不同,可以有一些视听体验——那么,这个场景也一定是虚幻的,感觉虚无缥缈,似幻似真,有点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意思。当然,这个虚化场景的处理,要与具体的叙事时空(乡村)相结合。但是导演处理这个场景的时候,就太写实了,几乎可以认为是他们亲眼见到了仙鹤,尽管这个镜头也拍得比较有美感,但是却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意象给削弱了,甚至破坏掉了。这是一。
第二,他这个电影,虽然富含了诗意,但是却从头到尾感觉不到太多的抒情。当然不是说没有情趣,他是相当诚恳的,有深沉之爱的,但是很奇怪这些情感在电影中并没有赋予太多的表现,表面上看起来是隐忍,但是我们知道,隐忍、克制,不代表没有情感,没有抒情,只是蕴化于其中,不煽情而已。然而,他在电影中的这种情感,最多只能说是情趣,有乡村生活和乡土气息的真挚,但是并无太多让你觉得情感流露的地方,而相反,都是细致的冷静的表现。于是乎,这些因素铺垫下来,到了第三,也就是最末尾,也应该是这个电影的高潮阶段,按照苏童小说再现场景的地方。
应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个蛮沉重的故事,甚至是蛮让人心悸的一个故事。
导演说到,是非常有浪漫色彩的,李玉(还是尹丽川?我记不太清了)等跟他说其实是很有美感的,很浪漫的感觉。这个我是不太同意的。我甚至觉得这种浪漫色彩的思想,其实很危险。
中间漏了两段没说,仙鹤,宗教情怀、天人合一、终极价值、形而上学……,这种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会进入这些里面,往往在一个人遭受到许多生活的打击,包括肉体和精神的磨难,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以前失恋了,于是就开始不知不觉间沉迷于传统文化,着迷中医、佛道……等等这些东西了。或者是在生活的巨浪中被打翻了,不知不觉间开始追问所谓生命的意义,所谓天命,所谓信仰,也可能就是去了西方的基督教。在这个片子中,是一位老人家,他忽然有一天不知不觉间开始专注于仙鹤了,开始想着乘白鹤去了,他的子女们不理解他,固然是无法沟通,而包括他的同岁人之间,其实也没有人能真正明了他的心思,只觉得这老头傻掉了。其实,这时候,在这位老人家体内,已经产生了某种诗性,和神性,岁月的流逝让他逐渐感觉到了一种生命的荒凉感。这种感受具体来说就是荒凉,甚至连苍凉都不是,荒凉,荒唐,荒诞。
我以前去我老丈人家里,和他喝酒,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似乎是我想让他跟我讲许多他年轻时候的事情,我老丈人是练功夫的,很能打,据说年轻时一个人打十几个没有问题。他其实或许不太想讲这些,至少也不想对我讲,但是好像是为了满足我一点点,就跟我扯乎了半天,他们的方言说到快了我也不太听得懂,只能听明白一些大概意思,他如何拿枪守镖,如何跟别人干仗,怎么样把对方打败。总之都是一些很威风的事情,的确也是我想听的,蛮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但是末了,老丈人长叹一声,唉,现在老了,不搞那些了,女儿们也都出去了,你看,有什么意思呢?年轻时威风再多,再厉害,但是老了啊,人这辈子真是没意思啊。(大致意思吧,非原话)
那声叹息的确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沉入我的心底,不过说实话,那时我并不能太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些年也慢慢有了一点点体会,不能说有很多,但确实比以前能略微体尝了,后来想起来,那就是一种人生的荒凉感啊。千言万语,说不出口,就是一句:唉,这人活着这一辈子真是没意思啊;老了,更是没意思啊……
还是说回到电影吧,片中这个老人家就是感受到了这种荒凉,所以他想超越它,想追寻更高更远的价值,同时也有对传统和土地的眷恋。这些眷恋,似乡情,乡愁,也似绑缚,似锁链。这种双重的冰与火的考验在不断地灼烧着他。所以,最后他做了个决定,要乘上白鹤,回到土地里——从形而下的现实境况来看也是非常成立的,城市里的孩子不太明白,乡下人老了,怕出门,怕死在外面,怕不能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怕被一把火烧了。
然后,小孩子把老爷爷给活埋了……
这是个多么沉重,多么让人心悸的故事啊。
之所以说,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浪漫色彩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其实我蛮明白那些有这样想法的人,小文艺青年,或者小文艺导演,大概都会有一些这种浪漫化的诗化的或神化的念想。这种念想,倘若是真到了毛时代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被感染,被同化,甚至从精神深处被征服的,还有什么浪漫/诗化/神化比那种崇高的宏伟的大无畏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更加有魔力呢?
大致上,这个导演有点像他拍的那个小男孩啊,智娃。
继续说他最后这一段电影吧。这段电影,也是再现原小说的场景,其实是蛮需要勇气来拍的。应该是要体现巨大的张力,并且这种张力形成某种压力,沉沉的死死的压在观众的身上,在看这段的时候,我的确也感觉到了隐约的一些压力,沉重,但是或许是我太重口味了吧,基本上我觉得导演还是没真正发到力啊,你看他让老人家轻飘飘的就坐到那个坑里去了。所谓震撼的效果,就应该是这种张力和压力,在观众内心深处形成某种爆破性的力量,一下子感到被扼住喉咙一般说不出话来。如果说哪怕前边有千样万样的不足,只要这一处高潮处理好了,这种震撼性的力量,触及人魂魄的力量,应该会大大的掩盖前边的瑕疵。我看到这一幕戏先是坐进去,然后突然就到土已经填完了的镜头,猜到可能是公映被剪了。不过,我个人感觉,即便是没有被剪,我就看前边这一点点的处理,可能还是不太能达到我说这个效果吧……这一段,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大的力量,很大的悲悯。说实话,我一开始看见小男孩挖坑,就有点感觉不太敢看后边的镜头,结果他处理得有点太轻飘飘了。
应该说,整体来看,这个电影还是相当有功力的,相当不错,导演在前面的各种处理,包括他的态度——你看他其实没有对这个电影中的任何人有明显的批判态度——这种视角暗蕴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怀。儿子媳妇对老人不理解,有时候难免生气,不过脾气归脾气,叫他来吃饭半天不来,还是要叫小孩子夹肉盛碗里去给他端去的。自己就生气,懒得去端,呵呵。
总的来说,导演有情怀,有智慧,悟性,但是他心中的深沉情感,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绑缚住了。这种情感的淡化或者说缺失,其实在原小说中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小说不一样,小说很短,很短,对于这样的短篇小说来说,只有10%是浮在水面上的,更多的是水面下那90%,甚至1%和99%。对小说来说,这样的处理是成立的,不会有太多问题,因为太短了;但是对于电影就不行了,其实这个小说对于电影来说只能说是一个引子,一个启发,电影是个全新的时空结构。
这种情感的缺失,我个人感觉,或许是这位导演,他还没有遭遇到所谓神迹的体验。他还没有被某种冥冥中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击中自己的全部身体和心灵,有如五雷轰顶。你看他最后会在片子末尾问这些问题,齐天大圣归谁管?归玉皇大帝;那玉皇大帝归谁管呢?归如来佛;那如来佛呢??
——插一句话,电影里加的这两个段子我都非常喜欢,齐天大圣大闹天宫闯阴曹地府被压五指山,和哪吒闹海。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叛逆和反骨,对男孩子,那就是齐天大圣,大闹天宫,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对女孩子,那就是哪咤闹海,削骨肉以还父母,自此恩断义绝。
导演很有悟性,这些东西既精心设计,又似信手拈来,说明他对这些问题是思考过很久的。但是他最后仍免不了要去发一个天问,问一问苍天:如来佛,你归谁管呢?这位导演,他也很好强啊……
如前所说,我想,他或许是还没有遭遇过类似于五雷轰顶的所谓神迹,于是,他心中真正的悲悯,还没有被启开。他的情感,他的悲悯,被他的理性,被他的智慧,给锁在了里面。
导演最后说到的那个事情,在他拍摄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包括每次放映的时候,天都下雨。有很多时候,其实我是个蛮迷信的人,呵呵。不知道导演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或许这是上天在给他启示阿。
上天在用眼泪来注入他的电影,因为他那么智娃,那么爱浪漫,呵呵。
最后,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这个电影是相当不错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电影是我看过的苏童小说改编的电影里面,除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之外,拍摄得最好的电影。我看完之后,甚至有一些激动,和兴奋。一点不夸张的说,我觉得比台湾那些小清新的青年导演拍的电影,不知道要好多少。
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和这位导演类似的人呀。我虽然经历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神迹体验,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是一轮一轮的,我现在也依然免不了,想去问一问天。这个画面,如果按我的描述的话,要么它就是外在的,类似于像少年派漂流那样,在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中央,或者是沙漠、草原……总之,是在某种巨大的自然力量的荒无人烟的中央,抬着头对着天空大声喊……
要么它就是内在的,呵呵,就像大话西游里面,紫霞仙子进到至尊宝的身体里面,钻到人的心上,看到一颗硕大的红彤彤的不停跳动的心,那心上布满了经文和咒语,层层密布,然后对着它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一声:喂!!!!!再或者就是白晶晶,挥舞着宝剑走到心的前面,看见那心上宛如长城,被刻满了各种名字、办证、到此一游……还有某个女人的一滴眼泪……于是大怒,高呼一声,我擦!!!!!然后一剑斩去……
然后,我就死了。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 昨天晚上在第三届深圳湾艺穗节上看了开幕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消息:央视新闻频道报道了河南周口平坟事件。一部电影与一个新闻事件的共同关注点在于:土葬。不同的是,电影探讨的是一个老农民的土地情结,而新闻事件反映的更多是利益与权利的冲突。不管是电影,还是新闻事件,其深层次的话题都可以归结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入土为安。
影片中的老人为了“入土为安”,不惜让自己的孙子和外孙女将自己活埋。一个老人为了“抵抗”火葬,以如此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当代的很多在大城市长大的人来说,也许是不能理解的。但以各种方式躲避火葬的情形,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很多搬迁到城市居住多年的老人,也有着很深的眷土情结,他们希望百年之后,能够在家乡土葬。而年轻的一代,一般在理性上是能够接受火葬的,在心理上却未必认同,“入土为安”的观念仍然深深烙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对农村场景的展现,也许与每个观众的经验或印象有区别,但从农村的风貌和农民的面貌来看,影片是准确地抓住了当代农村的特点的。有人诟病影片中演员的表演,认为比较生硬。而导演回应称最满意的恰恰是演员们的表演。以我观看过的多部由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农村电影来看,导演李睿珺敢这么说,绝对是有底气的。所谓生硬,我以为不过是演员的肢体语言不够丰富和他们说对白的时候缺乏抑扬顿挫的表现力。没错,从所谓专业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表演是业余的、生硬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奉献了中国最好的农民表演,因为我从未见过专业的演员演得比他们好。他们的表演缺乏层次感,不够丰富,是事实,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来自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没有技巧,但是,他们也毫不做作。很多人以为本色演出是容易的,指导出演自身身份的演员也是容易的,其实恰恰相反,非职业演员在“做作”方面,往往是超过职业演员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控制。李睿珺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让这些“非职业演员”不演过火,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相对自然的表演,放在就地取材的环境中,构成了一幅中国当代农村风情画。
看完电影后,我特意把苏童的同名小说找出来读了一遍。与小说相比,电影的内容更加具体和丰富。小说集中描写了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活埋。对于农村生活和老人的日常活动,小说只是做了概括性的描写。影片的前三分之二,小说具体涉及的不多,主要是李睿珺(编剧/导演)根据小说的概括性描写和现实生活的情况进行想象、加工的。影片的后三分之一,导演则相对忠于小说的描写,甚至台词都改动不大。而说到小说与电影在精神主旨上是否相通,我认为大体上是相通的,不同的是,小说对主题的表现更具有普适性,而影片则更多体现了主题的当下性。由于苏童的小说相对抽象(背景、描写),从小说到电影,是不容易想象得到的,而李睿珺居然把小说影像化了。因此,我认为电影是一个保留了小说内核的原创性作品,影片的创作是对小说的一次放大性利用。
回到“入土为安”的话题。对于老人的做法,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是捍卫生命的尊严(或死亡的尊严)?是愚昧的坚持?是对土地的眷恋?是保存灵魂的居所?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认为“入土为安”是理想的归宿。我不算纯粹的唯物论者,但我认为人死后,不再有感知的能力,“入土”或“化灰”,并无区别,再者,对于后人来说,“化灰”绝对是减轻他们负担的做法,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认同影片中老人“入土为安”的观念,但我不会去批判他,因为我很清楚他的固执与他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平坟事件,我想,是否可以以一个渐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当平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平坟复耕和移风易俗的问题的时候,这就更加值得我们停一停,想一想了。
导演在表现老人渴望“入土为安”的过程中,用的是一种缓慢的方式。影片的节奏比较慢,镜头也比较长,虽然孩子们的嬉闹给影片增添了生气,但影片大体上来说是安静的。老人在“大限将至”的暮景中,偶尔也会焦虑和恍惚,但他心中还是保持了一份白鹤般的悠闲与淡定。“活埋”一节,固然十分残酷,但导演用一个长达数分钟的镜头来表现,冷峻之余,又有一种惊人的沉静。面对死亡,老人难免悲伤,但他的内心应该是没有恐惧的,因为他的心中有白鹤——他将平静地抵达彼岸。总而言之,影片缓慢的节奏、沉稳的叙事,是符合一个老人的心境的。
相对于李睿珺的前作《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摄影略有变化。两部影片的摄影都是杨谨,构图的变化不大,变化主要是在色调和影调上。《老驴头》中农村,给人一种颓败、萧杀之感,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农村多了一些悠闲和快乐,色调上偏饱和,多了几分温暖,影调上则冷暖交替,不像《老驴头》那般冷感和干燥。
影片的音乐由著名独立音乐人小河操刀。音乐起来的时候,总是貌似有点不太自然,但恰是这种不太和谐的做法,很好地渲染了影片的情绪,为影片增色不少。
不管你怎么看,老人总算以自己的方式“入土为安”了。老人也许不需要我们的惋惜或认同,不如,我们祝愿他的白鹤之旅一路顺风,抵达生命的彼岸。 - (知道拿电影去跟文学原作比较,既合理又不合适,不过因为先看了小说,总不可避免的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画面想象,或多或少影响观影感受)
电影放映完毕后,有观众问导演:“你是双鱼座吗?”
李睿珺纳闷:“你怎么知道的?”
观众回答:“我也是双鱼,只有我们能在小时候看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要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才会哭。”
我们知道双鱼座盛产艺术家,这或许反证了这个星座人的敏感本性。不管星座是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扯淡,总之,从甘肃小村庄走出来的八零后李睿珺又是一个佐证这“趣味迷信学说”的好例子。他把作家苏童又一番关于生与死的灵性思考(短篇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成功改变成独属自己的故事;他让那些在亘古不变实践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亲戚朋友,还原为围绕自己成长经验的可爱精灵;他年纪轻轻就试图将那么一些只可意会的深邃意境,用精雕细琢的影像进行传达和抒情。
而这种试图,从观影感受上是愉悦而接近于成功的。为什么说只是接近呢?因为我个人相信苏童的意象始终是专属文字的。因为是灵巧的短篇,观影前,不少中国观众都简单扫了一眼,大家带着几乎同样的疑问,“就一个老头和两个小孩,这可怎么改成电影啊?”
莫非是像《樱桃的滋味》那般同样指向意味悠长的生死?可李睿珺实在没必要成为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和感悟的阿巴斯。他选择并挖掘出小说打动自己后引发的少时记忆,从故事情节到电影时空都将苏童原作的物理格局扩大数倍。记忆里,浮现出导演最初可感知的伤心,为大闹天宫罪行的孙悟空被判刑而哭。“没事,第二天他又会从电视里跳出来的”,大人开导道。“可是他要被压在山下500年!”孩子继续嚎哭。电影里,小伙伴们会去到河边的建筑沙堆上,比赛谁能将头闷进沙里的时间最长;会看着邻居小孩跟着父母与上来宣传火葬并挖祖坟的村干部拼命;会让大人为自己在河里抓来鸭子,却看着鸭子被煮熟后翻脸不认人。而所有的这些记忆,都是最简单和直接的,绝不会像成年后、文艺后,将记忆彼此相关联,并过度解读为死亡体验的隐喻。
而苏童的原作内容,几乎只留在了电影最后的十多分钟里。一直坚称在水田边看到仙鹤的爷爷,与孙子孙女进行着生命最后时刻的对话,老人不愿进火葬场,而期望在地里画个圈躲起来,等着远方来的仙物,驾鹤西去。
“老人摸了摸孙子的头发,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老人揪着自己的喉部,一边咳嗽着一边说,我让他们……长成……人……他们……要……把我变成……烟。”这是小说中最直接最不含蓄的部分,从阅读感受上颇入心灵,可一旦成为电影对白,就有可能不像说人话。所幸,李睿珺不但放弃了小说中全部可能的“画外音思考”,还聪明的加上自己最熟悉的乡音——并非大众所熟悉的普通话——解决了中国电影中最老大难的对白设计问题。
可是,关于生死的苏童式意象,始终难以真正通过影像来表达。爷爷表达了土葬心愿后,眼瞅着可爱的孙子真就拿来铲子动手,虽说并非恐惧,却也对行将就木的生命有着一番疼痛感悟,“可是你怎么能把爷爷活埋了呢?我是你爷爷,没有我就没有你爹,没有我也就没有你,你怎么能把你亲爷爷活埋了呢?老人捂着胸又咳嗽了一通,他卷起衣角抹了抹眼睛,说,那不行,你爹知道了非揍死你不可。”通过小说看来,这样的思绪和随之而来的挖坑掩埋行为被赋予了禅意,没人会追问其现实可能性。可到了电影中,感觉还是有那么点走样了,“怎么能把你亲爷爷活埋了呢?”苏童角色的这句话,自然而然的过度成了观众对电影角色行为的纳闷和疑问。
因此,李睿珺这部改编电影的突破与不足,反而更加印证着,电影与文学,始终是两门不同的艺术。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脱胎于苏童的同名小说。原著小说很短,影片最后的二十分钟忠实地再现了原著小说的全部内容。但如果把影片就浓缩成二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会略显突兀,而现在给人的是急转直下的惊悚感,恰如小河配乐中那嘶嘶拉拉而又嘎然而止的琴声。
前一个小时的故事无非是让我们走近这一家人的生活,了解子女对于老马身后事的看法,智娃和苗苗的个性,以及老马那关于死亡、白鹤和烟解不开的心结。如果只留下最后一场戏,那影片就很容易变成“固执的老人不可救药”或者“不懂事的孩子最残酷”之类的主题,而当我们有了之前一个小时对老马的情感代入,体会到他对烟的认识(旱烟)和恐惧(炊烟),他对子女不尊重他遗愿的担忧,才能理解他最后的决定实在是在情理之中——每个人都怕死,但和怕死比起来,老马更怕变成烟。
或者说,和怕死比起来,老马更怕死后升不了天。老马的工作是做棺材,影片开始就是老马在棺材上画白鹤的片段。可以想象,老马画了一辈子棺材上的白鹤,一定是饱含着对死者的祝愿,从另一个角度讲,他比谁都希望死后能驾鹤西去。老马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了在家里可以坦然地谈论死亡,因为他见得太多了,女儿在把他接去家里过中秋节的时候就直接说道:“你还能死在我家里?”不过子女应该没有想到,火葬对他们来说是移风易俗,驾鹤西去对于他们可能只是美好的传说,对于一个认真画了一辈子仙鹤的老人,如果告诉他仙鹤永不会来,那就是对他一辈子的否定。
老人和小孩一样,会调皮捣蛋,会逗来逗去,老马的仙鹤就和智娃的孙悟空似的。只不过老人让人更不忍心拒绝,就像画面几次三番提醒我们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尊重老马的遗愿也不能算是溺爱,虽然我是个无神论者,但如果抛开文化语境来看这么一个“老人临死前想象着仙鹤会来接他归天”的故事,不失为一个浪漫的童话,如果他能得偿所愿,会很感人。如此天真的一个老人,却得不到应有的临终关怀,是本片的悲剧性所在。
当然,不是所有想入土为安老人都有老马这样美好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怀,就像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在73岁的时候挑出女儿菜里的头发丝一样。但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人有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置自己的遗体?毫无疑问,如果在塔尔寺的人们有这个权利,那整个国家的人就都应该有这个权利,便于管理不应该是粗暴执法的挡箭牌。
说说表演——有专家诟病本片的表演不精彩,不如专业演员——我觉得这种原生态的表演配合上现实主义的摄影方式对生活的还原度极高,在高原风景下映衬下老马展现出了真实的苍凉感,智娃也相当有灵气,让人认可这就是生活本身,继而认同片尾那一片飘过核桃树的浪漫羽毛也是生活本身,让这个全片唯一具有形式感的镜头也有了实感。白色的羽毛轻轻飘过,土黄的大地却压在了观众的心头,带去沉重的观感。
不禁要吐槽一下,诺大的放映厅只坐了稀稀拉拉十来个人,文艺青年们都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