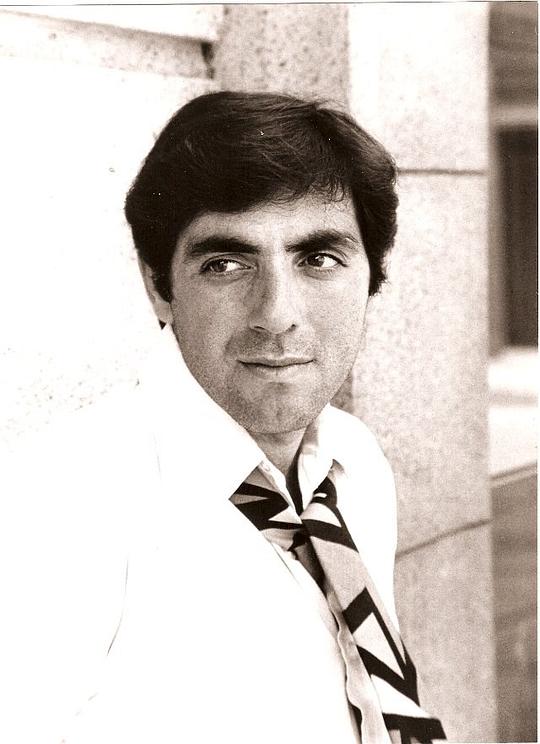穷街陋巷 Mean Streets(1973)

又名: 残酷大街(台) / 罪恶大街
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主演: 罗伯特·德尼罗 哈威·凯特尔 大卫·普罗瓦尔 艾米·罗宾森 理查德·罗农斯 西萨尔·达诺瓦 维克多·阿尔果 乔治·梅莫利 Lenny Scaletta 珍妮·贝尔 Murray Moston 大卫·卡拉丁 罗伯特·卡拉丁 Lois Walden Harry Northup B. Mitchel Reed 文森特·普莱斯 凯瑟琳·斯科塞斯 马丁·斯科塞斯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上映日期: 1973-10-14
片长: 112 分钟 IMDb: tt0070379 豆瓣评分:7.5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按:本篇选自去年夏天的旧作,原文曾首发于“澎湃·思想市场”与微信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题“马丁·斯科塞斯,从戛纳启程的伟大”。之所以挂出来,蹭热度只是原因之一。前几天看到一条豆友广播,提到《电影手册》的一则评论中写构成斯科塞斯人格的是“自杀的暴徒-唯美主义者-牧师”的三位一体。深以为然,但或许也并不新鲜(当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暴徒+牧师”其实也就是存在主义,而其存在主义美学也强烈地显露于《穷街陋巷》中。这部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构成斯科塞斯美学的源头,尤其是其对暴力和精神性(spirituality)的痴迷;在我看来它甚至是更为“斯科塞斯”的,因为他将暴力和精神性的呈现带回了他最熟悉的小意大利,并以一种极为新浪潮的方式解释了为何存在主义是我们的毒药,也是最后的解药。

时间拉回到1970年底,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年轻讲师斯科塞斯决定离开东海岸,前往好莱坞追逐自己渴望的主流成功。他从“B级片之王”罗杰·科曼那里得到了在好莱坞的首次执导机会,为后者拍摄了一部以暴力为卖点的“剥削片”(exploitation film)《冷血霹雳火》。这部影片惹恼了他在纽约的精神导师、美国独立制片先驱约翰·卡萨维茨,后者怒斥其“花了一年拍的东西屁也不是”,并敦促他继续拍摄像《谁在敲我的门?》这样有浓郁个人风格的影片。于是,斯科塞斯开始修改一份多次遭拒、尘封已久的剧本,也就是《穷街陋巷》。这部影片成为了斯科塞斯的破冰之作,也标志着其个人美学的成熟。
影片讲述的是生活于纽约小意大利街区的几个年轻人的故事,主角为“纽约古惑仔”查理(哈威·凯特尔)和他的朋友强尼(罗伯特·德·尼罗),情节线索则是麦克与强尼之间的讨债和逃债。作为生长于纽约的第二代意大利移民,斯科塞斯在影片中放置了许多个人寄托,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甚至结局(查理、强尼驾车遭遇麦克枪击)也取材于导演的亲身经历。片名“穷街陋巷”(mean streets, 或译“残酷大街“)出自硬汉派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简单的谋杀艺术》一书:“一个男人必须踏入这些穷街陋巷,尽管他自身并不残酷”。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影片所具有的黑色电影风格:对都市犯罪和暴力的呈现,道德模糊的人物和晦暗、阴郁的空间景观,以及潜在的社会政治意义。很难说到底是小意大利的生命经验使斯科塞斯终生都痴迷于对暴力的呈现,还是对暴力题材的痴迷使他一再重返“小意大利”。不管怎样,《穷街陋巷》确实开启了包括《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好家伙》、《纽约黑帮》等在内的斯氏银幕暴力序列。
而在《穷街陋巷》中,小意大利也的确构成一个完美的叙事空间,其完美根本来自于其封闭性——比残酷本身更残酷的,是残酷的不可终结。这种封闭性首先体现在查理的女友特丽莎要求查理随她离开小意大利时,她一再要求,查理却一再拒绝;接着,在强尼和查理的屋顶射击场景中,它再次以辩证的姿态现身:夜色中,强尼要射向的帝国大厦终究只在模糊的远景中一闪而过,他们疯狂而绝望的行为只能以回到小意大利街区的地面告终。因此,空间的封闭性也就凝结为一种抽象性,指向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在暴力和罪恶中生存,最终被暴力和罪恶所吞噬。空间封闭性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现身于影片结尾,当主人公们试图逃离小意大利时,命运直接出场,以异常残酷的方式将他们留在了小意大利的残酷大街上。有趣的是,坐在麦克车后座上朝他们开枪的正是斯科塞斯——如果说《出租车司机》里斯科塞斯饰演的乘客是崔维斯的暴力启蒙者的话,那么在《穷街陋巷》中,他就成了终极暴力的实施者。这是否能够看做“作者权威”的寓言呢?

然而在影片中,斯科塞斯并没有将空间/暴力的无可逃离设定为某种难以捉摸、不可言说的宿命。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发现,查理之所以拒绝离开小意大利除了其叔叔承诺给予的餐厅之外,更在于其显露的存在主义气质。众所周知,意大利的特产除了黑手党,还有天主教。影片最知名的镜头就是查理将手伸向火焰,探测自己内在的罪感和痛苦。

但查理显然不是古典的虔敬天主教徒,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科塞斯赋予了他后尼采时代的内涵,这主要通过强尼这一角色得以实现。强尼的出场极具戏剧性,他炸毁了一只邮筒,而影片对此没有交待任何原因。换而言之,强尼意味着一种无因、纯粹的恶(即使不是邪恶,也是顽劣)。正因于此,查理与他的友谊也就像浮士德与梅菲斯特或正邪两赋的卡拉马佐夫家族,而查理流连的纽约酒吧和脱衣舞女郎也就有了《荒原狼》中黑老鹰酒馆的意义。影片甚至在开篇就借着黑幕中的画外音也道出了这种关系(有趣的是,这段画外音同样来自导演本人):“你并非在教堂而是在街上、在家里赎罪,其他的都是狗屎,你深知这一点”(“You don’t make up for your sins in church. You do it in the streets. You do it at home. The rest is bullshit and you know it”。换言之,强尼正是查理的救赎所在,他给予查理的并非希望,而是朝向恶的选择——而选择所依据的自由意志正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内在要义。由此,查理对强尼不问善恶的不离不弃也就有了存在主义式的形而上色彩。《穷街陋巷》中浓郁的宗教罪感和存在主义式的救赎追索也成为斯氏影片的一大母题,蔓延至《出租车司机》、《基督最后的诱惑》、《沉默》等作品中。

如果说暴力及其救赎构成《穷街陋巷》的主题深度的话,那么其形式风格则更是为人所赞叹。斯科塞斯1960年进入纽大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时,法国新浪潮已风行纽约电影圈,他很快就成为特吕弗们的信徒。法国新浪潮奉“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为圭臬,强调以场面调度和景深镜头来达成自然主义的纪实风格。在《穷街陋巷》中,斯科塞斯同样运用手持摄影机、复杂的场面调度等技法来实现对小意大利空间景观及其中人事的“纪录”;尽管由于经费不足,室内戏大都是在洛杉矶完成,但由于精湛的剪辑,影片的真实感并未遭到破坏。真实感还来自情节配置,不同于古典好莱坞强调环环相扣的情节因果性,《穷街陋巷》中充斥着意外:突如其来的酒馆谋杀、莫名其妙的殴斗……同样,影片中置身于暴力丛林中的人物也丝毫没有约翰·福特、佩金帕等昔日美国导演作品中的英雄风采,动作场面既没有作为替身的特技演员,也没有舞蹈式的动作编排,只有现实世界中街头混混们的笨拙。所有这一切都赋予影片以粗粝而凶猛的纪实感。

不过,虽然受惠于法国新浪潮极多,斯科塞斯却更像是转益多师的杂家。作为意大利人,他对战后意大利电影自然也十分熟悉。确实,《穷街陋巷》对人物内心痛苦和压抑的呈现、对当代生活中信仰问题的追问都很容易让人想起费里尼。罗杰·伊伯特看完影片后认为斯科塞斯十年后将成为“美国的费里尼”,而斯科塞斯则回应道:“你真的认为需要十年么?”。
不同于上述欧式艺术电影的元素,《穷街陋巷》对音乐的运用则是纯美国式的。新好莱坞电影定位于反文化运动世代的年轻人,钟爱在影片中配送同期的流行音乐,比如《逍遥骑士》之于House of Rising Sun、《陆军野战医院》之于Suicide Is Painless、《毕业生》之于The Sound of Silence,《穷街陋巷》的片头曲则是六十年代的名曲 (很1960s很好听)。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或许可以启发我们打开另一重文本空间:斯科塞斯竟然为这部表现男性情谊的影片配上了一首如此热烈、纯粹的情歌,这的确无法不让人想起影片中查理和强尼之间甜蜜的“打头杀”和街头打闹,更不必说两人还实实在在地有一段“床戏”呢。而不管查理对强尼的“执迷不悔”是形而上的宗教救赎,还是另有深意,他们的同性情谊确实是残酷大街的黯淡夜色中唯一的光亮。

尽管发行很不顺利,但《穷街陋巷》很快就轰动了北美评论界。影片甫一上映,一贯犀利的宝琳·凯尔就撰文惊呼“它对小意大利中成长经验的呈现有着一种不拘、偶发的节奏和令人晕眩的敏感。斯科塞斯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美国电影里前所未有的粘稠腐败,以及对罪恶更加成熟的感觉”。很有可能,远在戛纳的“导演双周”单元正是通过评论界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和很快就将成为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翘楚的斯科塞斯——它对新好莱坞运动的呼应证明了当时大西洋两岸电影界的沟通效率:1969年,《陆军野战医院》夺得金棕榈;1974年,斯科塞斯来到“导演双周”的同年,他的同胞科波拉也凭借《窃听大阴谋》捧回自己的第一座金棕榈。
 《穷街陋巷》上映25周年纪念海报
《穷街陋巷》上映25周年纪念海报时间为《穷街陋巷》带来了更多赞誉和推崇。2013年,美国《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甚至将其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电影的第七位。罗杰·伊伯特在影片上映三十年后写下的这段话大概更加公允:“如果说科波拉的《教父》将黑手党呈现为一个影子政府,斯科塞斯的《穷街陋巷》则开启了现代黑帮片讲述日常生活现实的另一条主线。前者关乎事业,而后者关乎工作……伟大的影片不仅对观众也对后世的作品留下印记,《穷街陋巷》在无数方面都是现代电影的源头之一”。
- 《穷街陋巷》影片的开头有一段男主角查理意味深长的独白,他显然是面对上帝说成这番话:“你不是在教堂里赎你的罪,你是在街头,在家里,赎你的罪。”这段用我自己的赎罪方式不禁让观众思考这个从睡梦中惊醒的男人到底背负多深的罪孽呢,随着剧情的展开,查理在他黑手党叔叔凶狠的放债集团里不过是一个收债的小角色。他一方面渴望成为圣徒,另一方面又期望在黑手党内部能够青云直上。
查理的信念“要赎罪,就得在街头有所行动,而不是仅仅去教堂里作祈祷”,这让他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即如何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斯科塞斯将这个世界的堕落,将它那种暧昧不明、善恶不分的本质,用《穷街陋巷》中阴郁夜景表达了出来:忽亮忽灭的红色霓虹灯标志、俗丽的夜总会内部装饰、烟雾缭绕的房间和树影重重的街头,这就是斯科塞斯心目中的当代时髦监狱,一个噩梦般的世界。为了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获得一席之地,查理必须讨好他的黑手党老大叔叔,而另一方面,害怕受到神的惩罚的查理时不时将自己的手指伸到火焰上,象征性的体验被诅咒被炼狱之火焚烧的痛苦。
查理摇摆不定的立场,影响到了影片中由德尼罗扮演的乔尼。乔尼一出场就炸坏了一只邮箱,他这样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找乐,体现出这个人物性格上的没心没肺。正是这种没心没肺把乔尼引向了酒馆的争斗,并把他引向了更危险的赖账不还。满不在乎的借钱不还,这只是乔尼的古怪脾气的一个侧面。他的古怪还体现在那无节制的暴力行动上,而这恰恰触犯了乔万尼(查理的黑手党叔叔)的信条。乔尼肆无忌惮的暴力还将自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这种自我暴露正是那群小心翼翼的团伙一直力图避免的。炸邮箱,朝着帝国大厦开枪,这都集中体现了乔尼的无所顾忌。而真正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确是他那张嘴,在胖乔伊的桌球室里,一场无聊的争端刚刚平息却因乔尼再次的出言不逊而致使暴力再次升级。而在面对放债人迈克的时候,乔尼则表现的更加无所忌惮。他从查理那里拿到还债的30元中拿出20美元请迈克喝酒,他还债的钱就只剩下10美元,而且还挑衅道:迈克是世界上最蠢的放债者,居然还不断借钱给他。“你是他妈的笨蛋。”当迈克冲过来抓他的时候,乔尼掏出一支枪并且在此嘲弄迈克。尽管枪里没有子弹,但乔尼的行为已经足够触动迈克的杀机。
电影结尾处的高潮虽然有模棱两可之嫌,但从情节的发展来看,这种暴力收尾是逻辑的必然。上帝的审判透过呼啸的弹雨体现出来,但真正执导这场雇凶杀人戏的,其实是斯科塞斯。当时迈克已经从车里跳出,要去捉拿乔尼,但杀手却继续朝查理车内其余的人开枪,似乎是以此为乐。查理的伤只不过是皮外伤,他渴望惩罚而害怕毁灭,斯科塞斯满足了他对惩罚的渴望,但却让他避开了毁灭的命运。《穷街陋巷》里最有分量的是过程,而不是结局所付出的代价。但查理摇摇晃晃离开车祸现场时,他依然在挣扎之中。他既没有下地狱也没有上天堂,但他得到了缓刑。
斯科塞斯把《穷街陋巷》称作是“关于信仰的宣言”。在他看来,《穷街陋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还能在当今的社会环境里成为一个圣徒?”这部电影将天主教对于罪恶、惩罚及赎罪的看法,用电影手段形象地表达了出来。“想做圣徒,此路不通”,这就是《穷街陋巷》的结论。 - 说实话电影看了大半才开始进入情境。黑暗混乱的街道,灯光迷离的酒吧。小混混们无休无止乱七八糟絮絮叨叨的对话让我很烦躁。直到进入剧情,理顺了人物关系之后才慢慢开始看进去。
这是马丁早期的片子,很多导演都喜欢以家乡或者自己熟悉的人事作为自己的处女作,马丁也不例外,《穷街陋巷》带有半自传的性质,把导演所了解到的那个五光十色的美国中的“小意大利”展现给了大家。
马丁喜欢集中表现深刻社会问题。也得了电影社会学家的美称。而美籍意大利人是马丁最为熟悉的一个族群。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社会形态是极其复杂的。在的美国多数人都有着自己的亚文化。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亚文化可能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如美国黑人亚文化。亚文化还可能基于原来的国籍,如美籍墨西哥人,还有这部片子里所反映的美籍意大利人亚文化。
这种亚文化与美国的主文化相碰撞,还有不同的亚文化之间相互摩擦。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影片《穷街陋巷》中至少反映了黑人和犹太人与美籍意大利人之间的碰撞。
碰巧的是,这部片子中的黑人和犹太人角色设置的都是女人,而且都是底层的女人,主角查理甚至不敢在大街上与自己喜欢的黑人女人相见原因是太过丢脸。
全球至少有八大黑社会犯罪集团而为首的就是美籍意大利人集团。在多部片子里,如《教父》《美国往事》中都成功的塑造了美籍意大利人中的黑手党形象,通过电影,我们看到了血雨腥风的黑帮团体。当然也有侧重底层美籍意大利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状态的电影,例如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
《穷街陋巷》是一个看似戏谑却很悲伤的故事。
剧中的人物没有任何正事可干,总是无缘无故的争吵和斗殴,还有养豹子之类很荒谬的事情。场景总是固定在黑暗的街道或者昏暗的酒吧,让人感到压抑和沉闷。他们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集体,女人,例如片中的特丽莎,总是处于弱势,没有什么话语权。
其实故事主线很简单,不过是查理总是帮助强尼,而强尼一而再再而三的混账。最后在高利贷者的追逐中强尼被打到鲜血淋漓,查理,强尼,特丽莎在黑暗的街道恐惧地大声呼叫,血液流淌在美国的暗夜里。
导演并不是想侧重这样一个血腥的故事本身,他只是通过这个展现一个混乱的美籍意大利人群体。最后的结尾是砸向观众重重的一击。在欢快的音乐中,在灯火迷离的美国街道,留给美籍意大利人一些刺痛的感觉。
有人说马丁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发现了罗伯特德尼罗,原以为《出租车司机》是罗伯特德尼罗与马丁的第一次合作。今天才看见了更为年轻气盛和青涩的罗伯特德尼罗。 我不止一次提过老马的电影对于我自己的重要性,正是他的《出租车司机》将我领入了第七艺术的大门。如今虽然对他产生了审美的疲劳,但是依旧不可改变自己心中他的地位。而他所关注的大量元素乃至话题,乃至他所学习的那些风格,从《穷街陋巷》这部他早期的电影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个人超爱这幅海报。
个人超爱这幅海报。
老马是电影社会学家,这一点,恐怕是大家所公认的一点。然而他究竟是如何将社会和人物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我看来,塑造出令人信服的电影环境的同时,突出在剧情外的氛围和现实,这样两两结合,才使得他的电影独具魅力。
在本片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痕迹很重。不说别的,那在街道上拍摄出来的晃晃悠悠的素材,个人体验的突出描写,乃至剧作本身上在中间部分所塑造出来的散漫都让人想起德西卡,罗西里尼他们。再比如最好的例子,大概在15分钟开始时的对话,本来黑暗小屋所营造出的空间不同有种经典好莱坞的感觉,可是不一会儿又换到了外反打。这样我们所关注的点便从“二者的交接”变成了“他们说了些啥”,虽然隔开了人物,但也让我们适应那种生活。而后面,长辈谈话时的夸张运镜,则为环境和情节赋予了过多的激动,向观众说明这个地区的一种要素。
本片最具有借鉴意义的,从28分钟开始的“无聊”的戏份,被调度成为了“对生存环境的观察”,如同罗西里尼的旅游片一样,不同的是这样的生活所带来的绝望给人的震撼力更大。释放暴力时的长镜头充斥着野性以及对荷尔蒙飙升的真实记录,笼中狮子的意像象征与自己的“野性”的妥协,更不用说侍应生被干掉那段戏的调度,主角与配角的位置一瞬间调换,如同希区柯克一样的悬疑在一个配角身上释放后,又被前进的剧情抛弃,暗示后来强尼小子被干掉的同时,也通过平行剪辑告诉观众,死与不死,激烈与不激烈,这社会还是一样的糟糕。
当然,除此以外,老马还有的创新,就是无时不刻的压力。酒吧和台球室那有意为之的超现实打光,在餐厅和家中不平衡的手持镜头(这里很卡萨维茨),有关宗教的如同梦呓一样的主人公话语(这个,由于自己不是很了解基督教,所以先忽略不讲了),乃至无处不在的,无压力场景里的快速剪辑。27分钟和56分钟左右的这俩段对话的剪辑,极其精巧,那无处不在,但不释放给任何人的环境压力让大家适应着压迫感。也在习惯压迫感后,对后来的血腥结局可以木然的接受,因为这环境本就如此。
在剧情的塑造里,强尼小子这个人物,我是相当喜欢的(当然也多亏了德尼罗的演绎),绝对的无赖泼皮以及似乎看破世事后的为所欲为,乃至对兄弟的简单情感,都可以说是相当的反常规了,让人想起《水浒传》里的李逵,《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老爹,或者近一点,《穷山恶水》里的吉特,极其纯净,不带任何缘由的恶的元素在他们身上存在着,象征着社会不可缓和的顽疾和罪孽。
 德尼罗年轻时演个混蛋都演的这么好。
德尼罗年轻时演个混蛋都演的这么好。当然,虽然说我喜欢老马,但如今重看,对这狂躁郁闷的电影还是难坚持看完了,只能说它的艺术表达太好了吧,哈哈。心情不好的时候,请慎重观看本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