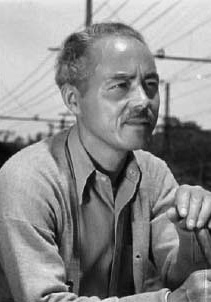恶魔之街 悪魔の街(1956)
演员:
影评:
作为铃木清顺的第三部作品,第二部长篇,虽然三部作品都在拍摄于同一年,但这一部成熟的不像是一个新人拍的,从首作就体现出的精巧构图自不必多说,这一部更为颠覆的是摄影机的叙事效率,这个颠覆不只是对于铃木清顺个人的,放在那时期的日本电影里也极为少见。用下面两处来举例。


这一段是在展现男主的老大杀完人后尸体掉入泳池的过程,不过这场谋杀的全过程都发生在荧幕之外,摄影机仅仅拍了男主在水中的倒影和尸体掉入水中后产生的涟漪。



男主来医院看望受伤的朋友,这一段以室外保安的抽烟戏开始,靠灭烟子结束,中间的男主戏份虽然保安不在画面中,但烟雾一直缭绕在画面内,与男主的身影重叠,两层影像汇集在这一画面里。
静止的摄影机,这种由小津发扬光大的镜头语言在黑泽明之前一直是日本电影的标志,其本质是当时移动摄影机很费人力,因此通过人物的站位,构图来减少摄影机的运动,即便后来黑泽明在罗生门里打破这一刻板印象,但固定的拍摄技巧他在后面的作品中依旧存在。镜头下导演完美的人物调度似乎一直伴随着日本电影,也成了大部分导演所最求的。而铃木清顺的这一段虽然表面和上述所提到的类似,但本质却是一种对于老式日影中所见即所得的抵抗,荧幕外的世界随着镜头一起被演员的调度给固定了,形成了一种舞台剧半的所见即所得的空间关系。而铃木清顺在他的第三部作品中,通过放大所见之物的动态以此延伸出了所不见之物的世界,探讨了荧幕外的世界与荧幕内观众所见影像的关系。
这种视觉上的放大在影片中还以另中形态呈现出来。

男主与反派打架,不过镜头并没有对准两人打架的姿态,而且停留在两人站着的体重器上,体态上的冲击被转换为更为明显的仪表盘。
铃木还不满足于这种视觉形式的探讨,他把所见即所得转换为了听觉。虽然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对于自身作者性的刻意强调。



男主和情人在室外谈话,室外充斥着噪杂的收音机的播报,下一个镜头,摄影机突然来到了室内,影片迎来了几秒的沉默,观众完全不知道男主说了什么,这个镜头的移动在剧情上也没有任何意义。铃木清顺就这样肆意的摆放镜头,这可是在当时娱乐化气息最为浓烈的日活,他还仅仅是一个拍了三部电影的新人,这种为了展现作者性而体现出的叛逆属实佩服。
不过对于作者性的炫耀还没有结束。
 这场戏的目的是打劫运钞车,镜头从车载音响开始
这场戏的目的是打劫运钞车,镜头从车载音响开始 镜头上拉,车载音响的音乐成了背景音
镜头上拉,车载音响的音乐成了背景音


 男主特写
男主特写
 运钞车出发,音乐突然停止
运钞车出发,音乐突然停止 音乐继续
音乐继续






 运钞车的画面,满面笑容呈现的很诡异
运钞车的画面,满面笑容呈现的很诡异





 驾驶员死后压在了喇叭上,喇叭变成背景音
驾驶员死后压在了喇叭上,喇叭变成背景音 之后的打劫画面全为固定帧,喇叭的背景音持续
之后的打劫画面全为固定帧,喇叭的背景音持续





 发现是男主的幻想
发现是男主的幻想 喇叭的背景音其实是男主自己压着喇叭导致的
喇叭的背景音其实是男主自己压着喇叭导致的这段打劫戏的分镜只能用帅来形容了,快节奏的剪切和远近关系的夸张转换,这种我一直认为是他在日活后期才形成的视觉快感竟然在这一部就完美的拍出来了。更让我惊讶的就是静止帧了,仅仅靠着与聒噪背景音融合诠释了铃木清顺自己的暴力美学。而且这一段不只有视觉效果,男主的脸部特写车载音乐的突然停止,运钞车上诡异的笑脸,这些镜头的穿插早已透露出这一切都是男主幻想。铃木清顺似乎在用这作者性和叙事性高度结合的段落表面自己不只是一个只会肆意移动镜头的以此来宣泄作者性的导演。
看了这部后我查了查与之同年的日本电影,以及差不多时期的日活娱乐映画,因为在日本新浪潮崛起的60年代之前,我已经想不到比这一部还要先锋而且注重叙事的商业电影了,我找不到一个衡量标准,不知道铃木清顺放在当时到底有多强。在找了一圈又看了一部载入日活史册的同时期黑色电影后,我确性了,铃木清顺是真的前卫。如果他不是在日活,恐怕新浪潮的旗手不是大岛渚而是他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