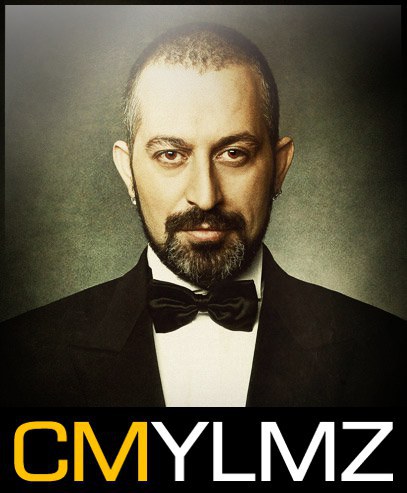占水师 The Water Diviner(2014)
简介:
- 一名在澳洲以农为业的的占水师康纳(罗素·克劳 Russell Crowe 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里波利战役后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试图寻找他三个参战阵亡儿子的遗骸。即使一开始遭到军方的百般阻挠,他也不屈不挠,更遇到于伊斯坦堡入住旅馆女主人爱莎(欧嘉·柯瑞兰寇 Olga Kurylenko 饰)及一名曾与他儿子对战的土耳其军官出手协助。康纳抓住一丝希望,为查出真相,穿越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九死一生,只为寻回儿子阵亡的真相,了结自己及妻子的心愿……
演员:
影评:
- 一战期间,英国军队于1915年4月25日在加里波利半岛实施登陆,遭到了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最终惨遭失败,同时参战的澳新军团也损失惨重。此战史称加利波利战役。
“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这就是片头,土耳其人攻入阵地,发现敌人都已经跑掉了的背景,而胖大叔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就在之前双方胶着对攻的那大半年时间里就战死了。
这场战争的一方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
由于准备不足与指挥官汉密尔顿对战场情况一无所知,在接到指派的时候,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 - 占水师是一种土澳式的浪漫——直接,真实,动人心魄。三条主线,并不是每一条都处理的很好,但是却让你无从挑剔,是的,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第一条是战争剧情,围绕土耳其内战和澳新军团登陆战展开。宽恕,最后帮助找到自己孩子的,竟然是当年杀死自己孩子的机枪手。而在生死关头,父亲居然救了昔日的杀子仇人。战争不是人与人的仇恨,而是一种准则的体现——是的,我们来了,我们死了很多人,我们走了,什么都没有带走。但是我们为之骄傲,这是我们的准则。这是一种普遍的澳洲文化认同吧,导演骄傲的讲了出来。
孤独。这个电影我是一个人去看的,而且全电影院只有特么三个人。。剩下还有是一对情侣坐在最后一排。那种包场式的气氛和音效(……)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那种内心的震撼感。片子开头的回忆以及父亲在妻子死后决定去寻子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了飞屋环游记——(当然我觉得飞屋环游记梦幻开场100分后面只有不到七十分)。战争场面的真实,遍地的白骨堆积,没有任何花俏,没有所谓的大场面,大制作,魔幻主义手法,小资主义情调,文艺逼范儿,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动人心魄,却在一幕一幕之中让你捂着胸口觉得如此压抑。
老板娘和父亲的感情线就不应该这么简单粗暴了,这也是一种遗憾。导演在战争,父子情,宽恕,这类历史性的主题上处理的非常好,但是在感情上就不尽如人意了。不过妻子和女主角实在太漂亮,女主的熊孩子也长得太可爱了= =。大叔式的父亲着实有魅力。
Brother against brother. Nation against nation. Man against the creation. We murdered each other. We broke the world, we did this. Man did this.
战争过于残酷,但是人性,却是人世间沟通的桥梁,宽恕,是和平决定性的方式,爱, 能够化解不理解和不认同。当他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已经在寻找和平和希望,虽然就像纪录片一样的记录了铁汉一般父亲在异国他乡的故事和日常,但是足以打动人心——因为这种主题,不需要你了解土耳其内战和澳新军团,就可以理解,让你为之震撼,因为全世界的人,人性是共通的。
对于爱情的描述,三分半,对于亲情的感触,四分,对于战争的解读,四分半,对于人性的拷问,满分。但是我还是给了五分——因为你值得去看这样一部电影,因为电影已经超越了自身本身。
P.S. 父亲和女主用餐那段凝视那段真的美爆了!半夜惊醒又让他拉回残酷中配上当时的配乐真的胸口感觉沉沉的。另外哥哥开枪打死弟弟的时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p.s.2 = =这电影好像之后澳洲美国和土耳其放映吧,看不到的人,真是太可惜了。。。 
4月25日,是澳洲公共假日Anzac Day(澳新军团日),这一天,澳洲全国各地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纪念百余年前他们在万里之遥的欧洲参加的一场战役,加里波利战役。
1915年的今天,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英国及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计划取得海峡控制权并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但却遭到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胶着八个月,最后惨败,同时参战的澳新军团也损失惨重。澳洲当年视英国为母国,所以也派出了军队远赴欧洲,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了一战。虽然一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但作为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加里波利战役给了对方以沉重打击。随着1918年11月一战的结束,这个统治近五百年的大帝国分崩离析,面临被英法等国瓜分的命运。

本偏安一隅的澳洲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五百万,但却有41万多人入伍奔赴战场,光加里波利这场战役,澳洲士兵就死亡八九千人,这也是澳洲整个一战中单场战役中阵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个特别的日子,我在电脑上重温了罗素·克劳导演和主演的电影《占水师》,15年初在它上映没多久后去电影院看过,当时还在豆瓣上做了标记,“《星际穿越》之后在悉尼看的第二棒电影”。
 ▲此片当年应该没有在中国上映,豆瓣标记人数不多,评分也不是很高,但不妨碍我觉得它是部好电影。
▲此片当年应该没有在中国上映,豆瓣标记人数不多,评分也不是很高,但不妨碍我觉得它是部好电影。影片中,罗素·克劳的主演的康纳和一家人生活在澳洲内陆地区的一个大农场,康纳是占水师,在三四年可能都不下雨的干旱地区,这也是不可或缺的技能和行当。家里有三个儿子,后一起入伍,远赴欧洲,加里波利战役战败的消息传来,他已默认三个儿子都已阵亡,但妻子一直幻想着他们还活着,以至于都有点神经质,这样过了四年,还是走不出这份丧子的悲痛,最后投湖自尽。临死前一晚,她还怪丈夫找得到水却找不到儿子。悲怆无比的康纳给死去的妻子许下了承诺,一定要找回儿子的尸骸,带回澳洲和她陪伴。
就这样他踏上了去奥斯曼帝国的漫漫长途。行船三个月,到达君士坦丁堡,去相关部门申请去加里波利的通行证,但被告知平民禁止去那里。可能是因为看了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这本传记,我不是很想用现在的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来分别指代奥斯曼帝国和君士坦丁堡,毕竟,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前序,伊斯坦布尔作为城市名也是在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广为采用。
初来乍到君士坦丁堡的康纳体验差到极点,在求官员网开一面的时候被也叫奥尔罕的一个拉客小男孩拿走了行李包,以为被偷了东西的他追着小奥尔罕满大街跑,最后被引向了小奥尔罕叔伯家的家庭旅馆。天真无邪的小奥尔罕靠着这特别的方式成功揽客,开心无比,康纳因为也需要住宿,于是就住了下来。
官方合法途径去加里波利无望,只能走小道。他听了小奥尔罕母亲爱莎的建议,去轮渡到某个地方,然后出高价找那里的渔夫搭船前往。此时帝国战争善后部队正在加里波利区域开展善后工作,对于“一叶轻舟”冒然过来的康纳几乎是立马下了逐客令。但听了康纳的故事,奥斯曼前军官、现协助英国开展善后工作的哈山少校(伊尔玛兹·艾多甘饰演,看过锡兰执导的电影《小亚细亚往事》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位土耳其知名男演员)动了恻隐之心,力排众议决定提供必要的帮助,理由就是康纳是唯一一个只身远道而来寻亲(尸骸)的父亲。

凭着当地军官的回忆和叙述,以及作为占水师的特殊感应,康纳终于找到了两个儿子的尸骸。之后哈山少校更是给康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另外一个儿子,从电报得来的名单列表看姓氏,如果没错的话,当时并没有死,而是被俘虏并送至别处。因为此时离那场战役已经有四年,随着一战后来的进展和最终结束,战俘也已被释放,但这个儿子并没有任何消息,所以很有可能也已经死了,只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死在加里波利。
于是又返回君士坦丁堡。当年战俘被送往的战俘营位于现土耳其的内陆小亚细亚地区,时值希土战争开打,希腊人派兵那边,局势非常混乱。出于安全考虑,哈山少校无力进一步帮助康纳去十面埋伏的内陆寻子,康纳被安排翌日清晨乘船离开,将经印度加尔各答然后回澳洲。但寻子心切的康纳没有接受安排,翌日清晨在爱莎的协助和指点之下,逃脱了本要接他上船的工作人员。后康纳又被押至哈山少校处,父爱如山真心可见,于是哈山少校和一众下属带着康纳踏上了去内陆的火车。
火车后来被埋伏的希腊武装军袭击,车上的人除了康纳因为协约国的澳洲身份,被网开一面,哈山少校等人都面临被当场处死的危险。关键时刻,在火车车厢上还教了奥斯曼军官们如何玩澳洲板球的康纳拿着球棒偷袭了正准备枪毙哈山少校等人的希腊武装军,成功救出哈山少校,并迅速骑马逃脱。路上看到了有风车,康纳想到了前一晚的梦境,想到了家乡的风车、水井和儿子们的童年往事,预感儿子可能就在这里。于是上前打听,果然不出所料。大儿子因觉得自己没能保护到两个弟弟,辜负了父亲的嘱托,无颜以对,而是在这边离群索居,造风车、挖井,倒是很好地传承了父亲的手艺。在希腊追兵赶来之后,他带着父亲来到了一口深井旁,跳下去可以通向别处从而成功脱险。起初他不想走,但面对父亲感人至深的话和浓浓的亲情,他答应和父亲同进退。
再次回到君士坦丁堡,回到小奥尔罕的家庭旅馆。小奥尔罕早就特别依恋康纳,感觉有如父子,而女主爱莎的甜咖啡,一表钟情。当两个人起身,四眼相对,我都想象到了康纳带着他幸存的大儿子还有小奥尔罕和女主回澳洲的情景。
当然,这份在异乡生发的情愫在整部影片里并非主线。我更关注,也更多思考的是,关于一战,关于澳洲,关于土耳其。宏大叙事,但也可以细致入微,从《占水师》看澳新军团日,突然有了一种和往年不一样的视角。火车上,哈山少校旁边的军官对康纳说,“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国家在什么地方,那就不要侵略它”,澳洲当年,确实是仿佛打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仗,付出了单场战役中伤亡最多的代价,但这场战役对澳洲的国家身份认同、对澳洲看待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土耳其来说,前朝奥斯曼帝国因一战而瓦解,近五百年的超级大帝国,曾经征服了在更之前的千年拜占庭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分崩离析,想来令人叹息。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再也没有了拜占庭和奥斯曼的荣耀,“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如此写道。
而影片中十岁的小奥尔罕,不仅让我思念起和他同龄的小外甥,也让我想起了帕慕克写的这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通篇我都在用小奥尔罕,满满的亲切和喜欢。看到在土耳其取景的镜头,我脑袋里都会冒出帕慕克笔下的点点滴滴,很多次,我甚至就觉得小奥尔罕就是帕慕克这个大奥尔罕儿时的分身,穿梭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经过蓝色清真寺、博斯普鲁斯海峡、托普卡帕皇宫,串起了我很多身未至但心向往之的地方。

澳新军团日,重温《占水师》。愿世界无战,愿和平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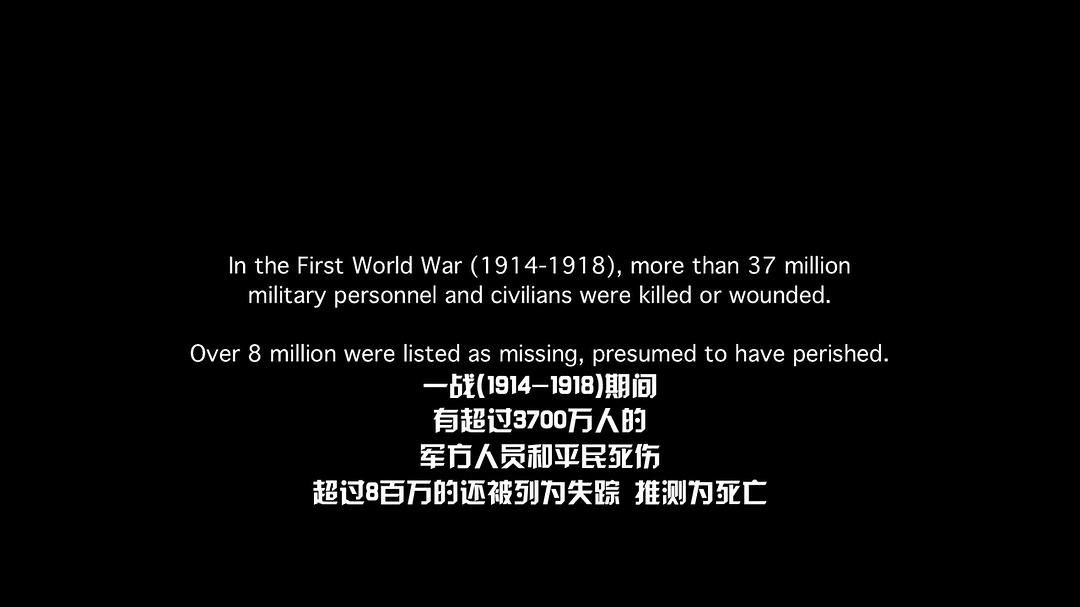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囧在澳洲 (?Jiong_2046)
 欢迎微信搜索?Jiong_2046
欢迎微信搜索?Jiong_2046- 这部片似乎很普通,但是要细细感受。男主角挖出水时你感觉到了即将丰收的感觉了吗?媳妇淹死在自己的蓄水池里时,你感受到了那种撕心裂肺吗?当寻找儿子们遭受种种阻挠时,你感受到了那种坚决吗?当被土耳其人敌视时,你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宽容了吗?当面对那个孩子时,你感受到了那就像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了吗?如果没有自己对孩子的了解,你能找到他们的骸骨吗?如果没有对孩子的了解,你能发现那扇风车吗?当儿子说:”你走吧,我要留下。”你会坚持吗?当故事中的一切悲惨都发生时,你还会继续爱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