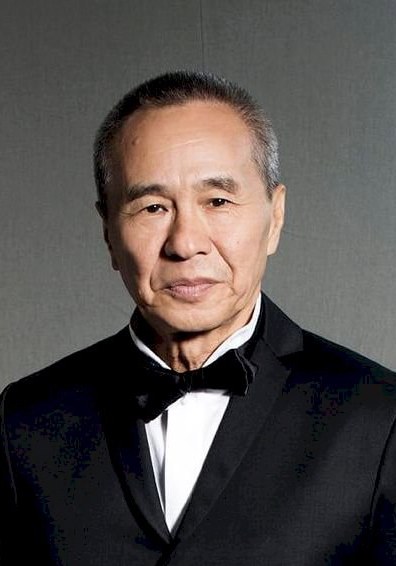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 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2014)
简介:
- 臺灣新電影三十週年之際,導演谢慶鈴從台北飛往清邁、巴黎、東京、香港、北京、鹿特丹甚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背景完全不同的導演、影評、藝術家们,娓娓道來臺灣新電影與他們的關係,那麼远、那麼近。
演员:
影评:
- 《台灣新電影》儘管是一部平鋪直敘、沈悶嚴肅討論電影的紀錄片,但對熟悉台灣新電影的觀眾來說,提供了很不錯的思想整理,與自我觀影經驗的再反省,看到那些熟悉的鏡頭,會讓你回想起當初那些影像衝擊帶來的悸動與會心一笑;對尚未接觸台灣新電影的人,也是很好的入門指南。
在威權壓抑下迸發出青春焦躁不安能量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們等當兵前無所事事《風櫃來的人》;荒謬戲謔卻又沉重點出省籍糾葛的 《香蕉天堂》;現代化下傳統仕紳沒落與女性獨立化的《海灘的一天》;赤裸直指國家暴力造成最沈痛悲劇的《超級大民》.....
台灣新電影以貼近土地的態度,在時代氛圍下凸顯立體的個人,它們撞擊出一股橫空出世的力道,繼而分毫不差地抓住時代面貌與精神,又以保持某種客觀距離感的方式,在另一個形而上的層面超越了時代,最終精準地呈現最純粹的電影美學。
三十年過去了,現代的台灣電影走出了悲情與抑鬱,但卻失去時代的張力與精神。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台灣新電影的形式與內涵,在其他國家的新生代電影工作者身上,得到某種程度的傳承,正如同當年台灣新電影從歐陸新浪潮身上獲取養分。儘管新電影以另一種百花齊放的方式得到了新生,但令人婉惜地卻在自己發源土地上失去蹤影。
侯導在最後說,重要的不是形式與手法,而是時代的內容。賈樟柯則說沒有什麼好留戀的,只是可惜失去了一種電影的生活方式。賈樟柯嘴巴說不留戀,但在他自己的電影形式中,某部分也是對新電影的留戀與致敬,那些電影內涵也正如侯導所說的一樣,緊緊扣著中國的當代氛圍。
那台灣自己的新導演呢,除了教科書式的研究、模仿與崇拜之外,在未來又能以什麼樣的形式去傳承、轉化繼而超越台灣新電影呢?
三十年後的人,又該如何紀錄與述說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影?又或者,我們根本沒辦法再以有系統與思想脈絡的方式,重新檢討我們當代的電影,因為後人仔細深究後,才發現後現代之後的我們,擁有的只剩下一片庸俗與蒼白? - (2015/10/26)
昨日在新竹影像博物館看了這部關於台灣新電影的紀錄片,之前早已耳聞此片風格不甚傳統,所以也有了心理準備。沒看過之前相關主題的其他紀錄片,這部去年紀錄台灣新電影三十週年的作品,找了旅法藝術工作者謝慶鈴搭配法藉攝影師Olivier Marceny,行遍巴黎、泰國、日本、香港、中國等地,訪談深受台灣新電影影響的電影工作者、影評人、策展人,談他們對台灣電影的記憶與想法。
全片幾乎是外部的觀點,志不在呈現完整的潮流歷史脈絡,而是發散式地從電影美學和台灣歷史記憶切入,從西方觀點一路走到日本、中國,我們看到馬可穆勒談他接觸並引介台灣新電影到歐洲,看到阿薩雅斯和Jean-Michel Frodon爭論著台灣新電影的現代性與中國性,是枝裕和又談了一次他父親的灣生記憶(笑),佐藤忠男從台灣電影中反思日本殖民的痕跡,王兵談第五代導演的集體電影中所缺乏的個體歷史記憶,鮑鯨鯨談她當兵時在野外看《童年往事》的記憶...。
與其是要述說怎樣的觀點與歷史,電影反而更多放在影像與人物、地點的狀態,種種偽生活的設計下鏡頭的流動,似是向侯孝賢和李屏賓的鏡頭美學致意,於是整片訪談的流動也像是斷簡殘篇記憶的拼湊,一種非常寂寞地,在新電影三十週年浪潮已然結束許久的當下,鏡頭看著電影激起的浪潮在這些人身上留下了怎樣的痕跡,這是非常迷影式(cinephile)的切入觀點,鏡中人談他們對電影的熱愛,而影像也服務著同樣的觀點,企圖留下訪問當下那些生活與地景的光影,同時穿插著經典作品的片段,以電影的形式再次向觀眾提示台灣新電影的魔力何在。
影片最後訪談終於回到了台北,我們卻看到蔡明亮說著其實他並不一定屬於台灣新電影,以及侯孝賢說著當代台灣電影新的浪潮還沒發生,重點並不是有沒有新的形式,而是有沒有屬於時代的內容。寥寥數語之下結束了這一場追憶電影的夢境,台灣新電影如此的盛放卻又如此的脆弱,充滿了歷史的光輝卻又無關痛癢地被許多人誤解及遺落。
就像賈樟柯追憶台灣新電影是一種電影人的生活方式,這部紀綠片則是記錄了觀看電影的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談論著電影與記憶,他們感知著影像與故事,這是以台灣新電影為名的電影探尋之旅,看似沒說多少,但其實也說了很多。我只是在想,是否有一天這一切包括電影與觀看的方式終將被人遺忘? 台湾新电影和第五代几乎是同时由始的,难怪乎要进行对比。这是不解风情的政治爱好者,拿来比照两岸文化的优越性的思维模式。
真不知当年谢晋推选《悲情城市》,会给意淫者多少政治解读。大陆的语境依然带着隔阂感,是站在西方对面的…这种历史影响至今泾渭分明。对台湾电影的讨论,其目标与其说是寻求异域的认同和价值体现,不如说是要问问对岸是怎么看的…纪录片本身也绕不开这种政治思辨,这是该片之不幸。
意识形态的对冲是故事的缘起,新电影似乎想用电影的方式去改变,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新电影真正为人喜欢的,是电影同质性魅力的散发…不解意图的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困惑于现实与创作关系的人看到了各种智慧和工作成果的示范…如此种种,已经超越了历史语境。
事实上改变这种局势(不同意识形态产生的压力)的却并非是电影,电影反而成为过去思辨留下的印记……脱离需求之后,看这些电影,想的就是电影发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