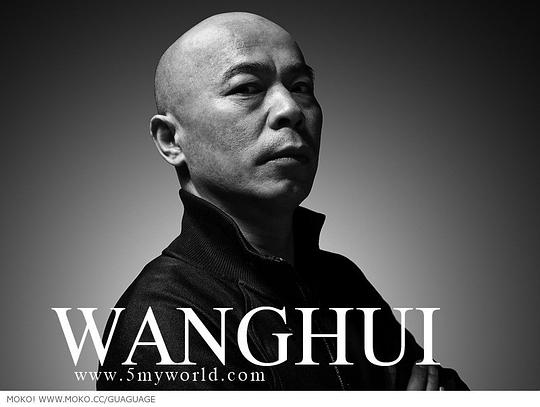新龙门客栈 新龍門客棧(1992)
简介:
- 宦官专权的明朝中叶,东厂曹少钦(甄子丹)假造圣旨杀害了忠良杨宇轩,并想斩草除根杀死其后代。侠女邱莫言(林青霞)、江湖义士贺虎等人冒死救出忠良后代后,逃至边关沙漠里的龙门客栈,与杨宇轩部下周淮安(梁家辉)会合。龙门客栈实则黑店,老板娘金镶玉(张曼玉)利用乱世,以美貌和风骚 作诱饵杀人越货聚敛钱财,但她却为英俊潇洒的周淮安动了真心。为了摸清潜藏于龙门客栈中的出关暗道,周淮安将计就计,答应与金镶玉成亲。
演员:
影评:
金镶玉出场时,100分钟的电影已近1/4了。
一出场,便是个性感的俯卧姿势,以及一句简单的笛声:先下行,再上撩,这是她的主题曲。电影前1/4,金戈铁马,关山万里,兵甲铿锵;唯独她出场,是清越的管乐。
以及,张曼玉发丝纠缠、脖颈间香汗淋漓的背影;一个故作矜持的回首;以及,被按倒后,本电影最性感的一幕:汗水淋漓。
张曼玉的娃娃脸面相,演金镶玉恰好:带点娇憨,带点天真,所以之后杀人不眨眼,才显出对比来。
刚还软玉温香,忽然相思柳叶镖杀人翻脸无情,这就是金镶玉的出场。惊艳而急促,捉摸不透。



然而也没那么难以捉摸。之后,金镶玉便显出她的一点执念:
林青霞的邱莫言来了,金镶玉一句“不正眼看我的,都不是男人”;这是她的自信,也是对男人的鄙夷;之后她去窥看邱莫言洗澡,二人打将起来,也是她的心思:
金镶玉讨厌伪装,非得揭穿了才好。所以她得意对邱莫言说:“可是我看你比你看我看得通透啊!”
之后又自鸣得意:“是不是连蜡烛都没点过啊?”
上了房顶,听见周淮安的笑声,金镶玉大怒,就光着身子站起来指:“哪里来的蜡烛啊!?”
金镶玉对男性的态度,从她骂人就听得出来,“去你爹的!”
她性子刚硬,而且总要坐得比男性高,没事就桌子上叠起椅子来,俯视男人们。
金镶玉讨厌伪装,讨厌男性权威。于是用妖娆多变或粗直凶恶对待男性权威——她不是不知道男人不会把她的话当真,她无所谓,她的许多妖娆,只是不屑罢了。所以在她不动情时,曲子是“喝碗酒嘞撒泡尿嘞,大漠里的汉子爱美酒!”就这么粗直,就这么不屑。
周淮安来找她谈事,讨好她说是上房,金镶玉很直白地:“什么上房?土房子罢了。”
周淮安再讨好她,问她“这是什么花?很精致。”
金镶玉恶声恶气道:“萝卜花啊!还能是雪莲花?”
她是不相信世上有纯洁无瑕之事的,样样摆起的架势都要揭穿。
但她到底对周淮安心动了,于是故作柔弱地划伤了手,眼珠一转,哎呀一声。
就在她故意划伤手的一瞬间(张曼玉眼神与手势的配合精妙绝伦),那缕清越的笛音又响了。

东厂三大档头到来后,金镶玉方显出其为本片第一重要角色的价值。
如果没有她的摇摆、莫测与斡旋,东厂与周淮安一伙早已开打;就是忌惮着她这点摇摆,双方还得场面上你来我往;金镶玉也就虚与委蛇,未语先笑;说些桃花运、割羊肉之类不相干的话。
终于周淮安发现了她的地下屠宰坊,图穷匕见,黑店本质揭露了。金镶玉望着周淮安。这是她本片第一次没有表情的瞬间。
大概因为这一刻,彼此坦诚相见,没有秘密了,不用假装了吧?
我觉得那一刻,张曼玉美极了,丰富极了。这个没有表情的瞬间,凝聚了一切。
信任,不信任;爱,恨;贪欢,利益,她自己过往的经历,自怜。她看着周淮安,不需要任何矫饰了。
可以谈条件了——真的要谈条件吗?

之后是著名的婚宴对打。金镶玉在听见黑子说东厂动手杀人后,瞳孔连续缩放两次,愤怒出手,杀了陆小川,又合力杀了贾廷。
已经撕破脸皮,不用假装柔情蜜意了。周淮安旁若无人地跟邱莫言谈情说爱。金镶玉继续冷笑:看惯人情,她是不相信这些所谓真情的。

只到听见周淮安说笛子身外之物时,她才恼了,说了句戳心的话:
“你们这些过客,达到目的就走,我们都一样,无情无义!”
这句话说来狠辣,又何尝不是她的自我保护?她长久以来对虚伪的不齿,也就出于此。
但嘴硬心软,生死之际,乱箭如雨而来,她还是要将周淮安的笛子还给邱莫言,而且倔强地:“你的笛子,别人施舍的东西,我不要!”

最后大战曹少钦,尘埃落定。曹少钦一死,金镶玉第一句话是:“周淮安?”
而周淮安在昏迷中,咳了一声,道:“莫言!”
金镶玉放下了心,倒了地;与此同时,怅然若失地,咬了一下牙。她是爱周淮安的,也再次确认,周淮安并不怎么爱她。

电影最后,周淮安走了。还说了,“下一批过客来时,你自会忘记我的。”
本来到此结束,也就可以了。的确,金镶玉可以继续做她的老板娘,继续戴着巧笑嫣然的面具,杀人越货,勾引自己喜欢的人,继续下去。
然而金镶玉回去,将客栈烧了,去找周淮安了。
她何尝不知道周淮安爱的依然是邱莫言,她最后怅然地一咬牙时已经知道了;她何尝不知道这么去追着周淮安未必有好结果,她是最懂得用面具来自我保护,同时揭穿他人虚伪的女人啊。
但她去了。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在无情无义的沙漠里玩弄人情左右逢源揭穿虚伪,是因为她不相信世上还有真东西;但一旦发现还有点真的,她就义无反顾地去了。就像那一缕清越的笛声,其实无遮无拦,纯粹之极。
张曼玉的金镶玉演得,真是好。她的娃娃脸带点娇憨与天真,让她笑得甜又迷人;她是全电影唯一一个摇摆不定,但又有所成长的人物——曹少钦要杀人,三大档头要捉人,周淮安和邱莫言一出场就生死相许了真爱,只有她在变化,在摇摆,在成长,在怒骂,在欢笑,在揭穿了一切虚伪后,做了自己愿意做的选择。
在其他人布衣缓带城府深藏的轻柔姿态下,张曼玉那些夸张又迷人的肢体语言,是这部电影里最动人的时刻。她制造一切悬念,制造一切戏剧性,而且本人的情绪,从开头的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到中间的动荡,到末尾重新平和。本片其实也就是由她情绪主导的。她的变幻又纯粹,是本片真正的灵魂:一个最纯粹的女人,仿佛她自己就是变幻不定的沙漠本身。
作者:川江耗子
作者博客:
英文名:New Dragon Gate Inn
拍摄时间:1991年
导演:李惠民
监制:徐克
武指:程小东
演员:
林青霞(饰邱莫言)、张曼玉(饰金镶玉)、梁家辉(饰周淮安)、
甄子丹(饰曹少钦)、刘 洵(饰贾 廷)、吴启华(饰陆小川)、
熊欣欣(饰曹 添)、徐景江(饰边关千户大人)
江湖醉渡十五春,风流最是《新龙门》。
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侠客。江湖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尘世的打打杀杀如此,荧屏内的刀光剑影亦是如此。在风起云涌、亦真亦幻 的武侠电影世界,徐克是一面不倒的旗帜。1979年,鬼才“徐老怪”以《蝶变》开创了香港新武侠的典范,并发动新浪潮运动支撑住香港电影的半壁江山,后来的《黄飞鸿》、《笑傲江湖》系列更是打开了香港电影进军世界影坛的辉煌之门。他或执导,或监制,或武指,云集了香港前后20年最当红的男女演员,天马行空地运用好莱坞电脑特技,制造了“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武侠太虚幻境,让数亿影迷拥有了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1991年,徐克会同程小东、李惠民,重新诠释胡金铨1967年拍摄的经典同名剑侠电影,共同创作了武侠电影巨制《新龙门客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现在《新龙门客栈》已被公认为武侠电影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徐克武侠电影的扛鼎之作,恩怨情仇、剑光游走之中洋溢着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神韵,浪漫主义的侠义精神,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自由主义情怀。
一晃十五年了!十五年,过尽千帆,《新龙门客栈》依然风采依然,如丰碑一样屹立于江湖世界,无人可敌无人能撼。十五年了,金镶玉依然风韵不减当年,邱莫言仍旧是我们的最纯情的初恋,历久弥新,经久愈坚,日日跟随我们陪伴我们的青春逐渐老去。
新龙门客栈的旗帜,永远飘扬在贺兰山下龙门关前,大漠朔风之中。
庄子云: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事实是,江湖中风云动荡,奸臣当道,宦官专权,赤子之心岂可苟且偷生于乱世无常?因为天生俱来的侠骨柔情,因为不离不弃的儿女私情,为了营救忠良之后,周淮安、邱莫言、金镶玉注定要在大漠之中、在龙门客栈相濡以沫。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龙门客栈香烟袅袅,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他们的主子却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这里的人远离繁华与尘世,他们不相信正义、道德、是非、法纪,他们坚守的是生存之道,他们不走官道,也不想涉足江湖,但他们却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江湖与官道之间,卖人肉包子,提供客房,赚钱,发财。这里的人粗犷豪爽,野马无缰,爱恨分明,完全地恋爱自由和性开放,因为他们有一个风骚入骨的女老板。在她的打情骂俏之中,坐镇的是欲仙欲醉的男欢女爱。
但是,因为正邪势不两立,周淮安身在龙门关,万马千军随之奔腾而来,龙门客栈遂成江湖。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金枪刀匕最无情,剑已出鞘势难平。正所谓龙门山的风雨,说来就来,金镶玉一个小女子,恁她百般能耐也无法阻止大明东厂抢夺江山的铁蹄和高强武功。
首先到来的是邱莫言。林青霞这个琼瑶剧中的纯情女子,被徐克雕琢成精致绝伦的“东方不败”之后,再一次以女扮男装形象出现在沙漠之中。这个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女侠,恪守着传统东方女性的内敛、矜持与儒雅,怀着对周淮安的爱慕之情,她选择来到这个沙漠,选择了风刀霜剑相伴的生活。为谁情多丝宛转,未免心苦巧玲珑。笛声悠扬,吹奏的是“革命爱情”的悲壮旋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什么时候才能和心爱的人同上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
周淮安终于来了。这个让邱莫言、也让金镶玉望穿秋水的男人极品骑着骆驼穿越风沙而来。风流倜傥、儒雅多情,还是大明帝国80万京城卫戍部队总司令,试问哪个女人不希望点亮这支蜡烛?驻足客栈之时,金镶玉正赤身裸体在楼顶欢唱:“八月十五庙门儿开,各种蜡烛摆上来。红蜡烛红,白蜡烛白,小妹我一把攥不过来…”心声坦诚得彻里彻外,周淮安一声仰天长笑,金镶玉怦然心动,脸上现出脉脉柔情一抹朝霞。心慌意乱从楼顶跃下并将客栈旗子裹在身上,虽然狼狈仍不失风情。我身上就是龙门客栈。小女子虽点遍天下男人的蜡烛,但是为了你我金镶玉须作一生拼,尽君今夜欢。
但周淮安此时心中只有邱莫言。两人早已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龙门客栈楼上,周淮安与邱莫言久别重逢,二人百感交集,莫言伸出左脚,手倒背,周淮安伸出右脚,手亦倒背,姿势优雅特别,心有灵犀一点通,此时无声胜有声。没有激情拥抱,没有惊呼大叫,莫言在周淮安抚摸她脸庞时柔情似水娇艳欲滴。浓得化不开的情啊,却要面对腥风血雨的考验。
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笛声传达的是邱莫言对世事的感伤,对梦想爱情生活的期待。离乱情怀最伤人,因此她对贾公公说,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周淮安说:多少风雨,我们俩都能死里逃生;世事无常,人势所逼,谁能料到你我能否顶过这最后一关。鬼门关前爱情甚至性命都得先让道,为了过这一关,周淮安迫不得已以色相为诱饵,以娶金镶玉为名逼其提供秘道。一边是忠心侠义,一边是儿女情长,周淮安把赌注押在了金镶玉手上。但一开始赌局陷入颓势,他进了洞房不仅难脱身,还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而且曹少钦已经兵临城下。危急关头,邱莫言等人杀出重围,帮手全部遇难,莫言中箭而返。
三人的爱情纠葛戏在敌军压境之前达到高潮。新婚之时,邱莫言看到自己送给周淮安的笛子在金镶玉手中,悲伤欲绝,借机与东厂之徒斗酒,将一坛酒倒入口中,酒入愁肠,化作伤心泪。莫言的心在流血。其实,一开始金镶玉就处于下风。笛子于周邱而言只不过是定情信物,而她却以为拥有它就占有了周淮安(笛子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男人性器)。周淮安对莫言说:那笛子,我无心送给金镶玉,真没想到会令你异常不安,还好能向你解释。人说乱世莫诉儿女情,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莫言说:笛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周淮安说:身外之物,莫过于此刻之情。这对莫言来说是莫大安慰,对金镶玉来说却是莫大的伤害。最具象征意义的情节就是,当时莫言受了箭伤,周淮安在金镶玉的房间里给她疗伤,是金镶玉提供的金疮药——金镶玉的无意伤害还是要她来偿还。
其实,周淮安并非对金镶玉没有动情,只是金镶玉不计后果的纠缠让周淮安非常恼火。初次见面,二人已经互生情愫。金镶玉说,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雨。周淮安回答:龙门山有雨,雪原虎下山。二人的问答里已经“巫山云雨”了一番。而且他们之后的每一次对话都心领神会。的确,丰姿绰约、泼辣风流、至情至性、我行我素的老板娘,简直是个(男)人见人爱的尤物,她不羡慕做什么天山上的雪莲,即便是朵萝卜花也要活出自己的娇艳,周淮安也曾亲口直言:“那么美的东西,哪个男人不想要呢?”
她义无返顾地爱上了周淮安,但多情总被无情恼。她不相信周淮安承诺的事后报恩,她要的是今宵共度的欢娱,她看惯了无情无义的男人。男人们都是一上来就要要完就走,周淮安不也是想利用她?所以当周淮安骂她就像沙漠一样无情无义时,金镶玉回应道:你们也是这沙漠的一部分,只顾着自己,有没有想过别人呢?你们这些过客,达到目的就走,我们都一样,无情无义! 救忠良之后是周淮安的情义,希望与邱莫言一起安全离开也是周淮安的情义,但是,周淮安显然忽略了对金镶玉的情义。蕙性柔情忒可怜,镶玉真乃女中仙。我们这时都站在了这个开黑店的老板娘身边,尽管她是一个野蛮女友。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乱箭之下,金镶玉冒着生命危险把莫言的笛子捡了起来,莫言也投桃报李把她救了出来。金镶玉还给莫言笛子时说:你的笛子,别人施舍的东西我不要。依然至情至性,让人顿生怜惜和敬佩。决斗之中,受伤的莫言被流沙慢慢淹没,绝望的周淮安爱莫能助痛不欲生。还是金镶玉胸怀大局:周淮安,你要挺着,你是男人来的,你还要带孩子出关呢。一剑穿喉,周淮安和金镶玉幸运地斗垮了曹少钦。大漠之上,天地变色,风沙呼啸。朔风之中,孤独的竹笛成全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的执著追求。金镶玉一把火烧了自己经营多年的龙门客栈,追随周淮安而去,天涯海角任平生。
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娇。作为男人,十五年时光让我从少年步入青年,但是金镶玉、邱莫言这两个女人的笑颜一直驻留我脑海挥之不去。金镶玉,或许是“玉在匣中叹,金钗土里埋”,也许是“金壁生辉玉玲珑”;邱莫言,也许是她希望和周淮安“记取年时,头白成双唱旧词。莫言秋晚,五日小春黄菊绽。”但是不是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周淮安说,龙门客栈,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这里的落日。可是,我却不断地回首,回望龙门客栈的残阳,迎接金镶玉邱莫言刺向我的温柔一刀。
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十五年前,茫茫大漠里,一间孤独的客栈,上演了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惊世骇俗的爱情悲喜剧。林青霞、张曼玉,这两个中国男人最爱的女人,在镜头面前展现出风格迥异的娇媚,已经彻底在烙在了我们的青春记忆里,永远不老。
(天涯精华贴,欢迎批评指正)- 今天去看了修复版《新龙门客栈》。总的感觉不错,毕竟是百看不厌的经典,我心目中永远的武侠电影南坡万。让人欣慰的是,影院里的气氛很好,当年让我们乐不可支的地方,一样有人哄堂大笑,而且上座率也不错。
修复版有些改动,仗着对这片子倒背如流的底子,我也不翻碟了,来数数数码修复版跟当年的影院版和DVD版有些什么差别吧。
1,片名。修复版在片名旁边加了“经典版”三字,其实没必要。片子本身是经典,那是那么多年口碑叫出来的。修复的这一版跟原版比,不如人意的地方不少,自称经典,是蜜上加糖,白白折了滋味。
2,片头字幕。编剧一栏原先是“张炭、司徒慧焯”,现在成了“徐克、张炭、何冀平”。把何冀平写进去了,很好。苏叔阳没写进去,不太好吧?
3,配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貌似全部重配的。张曼玉的配音据说找的还是原来那位,配得最好,一开口就压得住场面。甄子丹的配音可能是我的习惯问题,语气语调还是原来那样,可是低沉了很多,开场那场戏不像当年那么慵懒奸邪,感觉不太适应。最失败的该属给刘洵配音的那位,这片子看的就是贾公公啊!那把浑厚平稳的男中音,怎么也找不到太监的感觉,原版的哑笑也改了,失色不少。总的来说,修复版的配音“戏味”没有原版那么足了,让人有些遗憾。
4,配乐。新版的配乐把高亢的唢呐改成了轻柔的类似笛子的乐器,相当不给力。多年来,我印象里马队在雪山下行进的和曹少钦仗剑追杀三人的精彩场面就是伴着嘈错的弦子和高亢的唢呐,那种凄厉的感觉配合画面,无可替代。
5,某些血腥画面没了。一是路小川被挤进磨盘里,贾公公大叫一声“小川”,张曼玉用瓢接血这几个镜头没了,直接一瓢血泼上去。二是林青霞客栈里缒着红绸砍人头的画面没了。三是曹少钦长剑刺中鞑子,鲜血涌出沙漠的镜头也没了(谢谢陆同学补充)。90年代能放的所谓血腥镜头,现在反而不敢放了。真TM无聊。
6,某些台词改了。张曼玉的口头禅“操你爹”改成了“我去你的”……你能接受老板娘发现相濡以沫的伙计死了后,居然只骂了句“我去你的”而没有热情问候人家令尊吗?我反正是不能接受。
7,那首酸曲。我记得原先的歌词只有“喝碗酒来撒泡尿,沙漠里的汉子爱妹娇,我的小呀哥哥呀爱妹娇”,这版里听到了另外的歌词“吃饱了饭来上了炕,沙漠里的妹子爱哥壮,我的小呀妹妹呀爱哥壮”,很好。
说完改了的,再说说没改的。悬崖混战,贾公公先后两次加入战团的剪辑错误没改。原先港版有而大陆公映版没有的两个镜头加进去了,一个是邱莫言拜神,一个是鞑子带孩子上房赏月。
新版的字幕错处不少。现在记不住了,只记得一个“坝上大肥羊”写成了“八成大肥羊”,什么跟什么呀!
我承认,可能是因为原作太经典,我们这些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的影迷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无法接受哪怕一点点的改动。不过良知未泯的理性告诉我,从第三到第六条,配音、配乐、画面和台词的改动都毫无必要,只会削弱原先的情节和气氛。
最后,寄语85后和90后,这个帖子不是写给你们看的。所有这些改和不改,只有我们这些专门去影院看刘洵的老戏友才会在意。上述细节会造成的种种细微差别,对你们完全没有意义,赶紧去影院支持史上最强武侠经典才是正事。看过这片子,你才可以不心虚地说一句,“咱也算是上影院看过真正的武侠片的人了”!
链一个以前写的兵器谱在这儿。
ps 继续寄语85后和90后,你们怎么听不出好话坏话来呢?我哪儿是在骂你们?这是同情你们好不好!除了广东的朋友,你们其他人在影院里看过《白发魔女传》、《狮王争霸》、《刀》这些真金白银的新武侠经典吗?没有吧?你们都是看着《英雄》、《夜宴》、《黄金甲》这些塑料“大片”成长起来的吧?哪怕喜欢新武侠,看的也是DVD吧?我手把手告诉你们这修复版哪儿不够好,催你们去电影院看,总不至于是在坑你们吧诸位?你们说呢? 我是个做生意的,却做了人生最折本的一笔买卖。 “金壁生辉玉玲珑,好名字。”谁敢说你不谙风情,就算是投石问路,你一副妙口舌也叫我受用无比。到后来,我都不知道,那情分是不是从这最初的开始就有了。 漫漫飞沙看不清你脸孔,但是一把倜傥的笑一样捏住人的心,最早,识得的是你的声。就算我裹的是一身破幌子旗,我也知道,你在心里看了我不止一遍。 店不留人雨留人,多想这雨一直绵绵落到无绝期。 我竟失了由来的信心,怕留不住你。你断然不会是来日的十香肉馅,所以,你成了牵我性命的人。世道就是如此,我挟持不住你就是你挟持我,永远没有势均力敌的平衡。 看见你抚她的脸,如果你的眼神看我的时候是戏谑,那么对她,就是似水情意。 我一早知道她是个女人,但是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如果知道,我还会不会留下她?你猜。 我当然要留下她,没有她,你也不会来。 从来没有人在意过我雕的那些萝卜花儿,只有你说它精致,是顺口的话罢,抑或逢场的戏话。但是我愿意当真。这年头能当真的东西真不多,买卖谈好了都要先收银两。 但我愿意让你欠着。 于是,我刺破自己的指头用自己的血染了萝卜花的色,它们本来就不是天山雪莲,要当也只能当曼珠沙华。因为刺疼了才会记得,但是我是舍不得刺你的,你只要把带着我的血的萝卜花带走就可以了。我知道你不是知恩不报的人,但是我不止要你报我一夜。 你竟然开口说到嫁娶,就算我梦寐以求也会猝不及防,这下轮到你得意,“怎么,也吓到你了?”我当然不是惊吓,只是心底被击了一记寒战,就算点过再多蜡烛也会在心思最隐秘处膜拜一对红鸾烛火。如今等到今生梦中良人,却在如此较量中被轻率点破心中隐秘,我当下便知,你当我,一如当这片沙漠,是必经之途,也是路中过客。 其实是连失望的资格都没有的。 一早就看见了结局的,于是抽你那支笛,知其是你心尖所爱,拿来为自己在你心里辟一角位置,憎也好,怨也罢,只要不如同那漫天飞沙,一阵风过,便也不知何处来何处去,散到了无踪迹的天涯。 没有想到,真在这大漠里与你张灯结彩结了连理。 就算我知道,这边是欢欣喜庆的场面,那边是你今生不再见的决心,就算我知道,这或许只得一夜的夫妻情分。在镜前,我依旧欣然梳妆着衫,做你最娇媚动人的新娘,因为这一夜过去,我就是你的妻,亘古不变。 却连这一夜也过不掉。 我最终还是要让你走的,让你们走的,你一早就知道,对不对?你终究是个过客,是这个沙漠的,也是我的。 她身体里的那支箭被你逼出来,直中我们白纸红字的双喜,尽管它本身其实是个幌子。你终于被刺疼了,因为她的伤口。 “身外之物,莫过于此刻之情。”你含情脉脉地望她,终归连被我抢走的那支笛你都看作了身外物。 我在这个客栈里生活了这么久,到了,我带走的唯一一样东西却是她送给你的笛子,为了还给她。我不要你的身外之物。如果我想要的你给不了,那我什么也不要。 你一直是嫌弃这个沙漠的,你说它无情无义。最后它埋葬了她,会不会因此你对它生出留恋来?于是我问你,你会再来龙门客栈吗?你说,你没有勇气面对这个沙漠。 我终于可以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