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的蓝线 The Thin Blue Line(1988)

又名: 一线之差(港) / 正义难伸(台) / 细蓝线
导演: 埃罗尔·莫里斯
编剧: 埃罗尔·莫里斯
主演: Randall Adams 戴维·雷·哈里斯 Gus Rose Jackie Johnson Marshall Touchton Dale Holt Sam Kittrell Hootie Nelson Dennis Johnson Floyd Jackson Edith James Dennis White Don Metcalfe Emily Miller R.L. Miller Elba Carr Michael Randell Melvyn Carson Bruder Ron Adams John Dillinger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上映日期: 1988-08-25
片长: 101分钟 IMDb: tt0096257 豆瓣评分:8.1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影片《细细的蓝线》取材于发生在197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伍德警官遇害案件,该片和导演埃罗尔·莫里斯的调查最终证明当年被判死刑的凶手兰道·亚当斯(Randall Adams)实际上被错判,而真正的凶手是指证亚当斯的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其因为另一项谋杀案被判死刑而最终承认了自己才是凶手。影片上映后引起热议,“替罪羊”亚当斯也在被监禁长达11余载后无罪释放。作为20世纪7、80年代西方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之一,《细细的蓝线》显示出高度风格化的叙事策略和对纪录片真实的本质探究,达成了对于直接电影的反叛和批判,也改变了纪录片在处理与现实之间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彰显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新纪录电影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 拼贴结构和复调叙事
实际上,由于纪录性质,影片内部的叙事先于影片之前就已经形成,其叙事仅存在于影片的外部,即它是如何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或说其内部叙事其实是依靠外部结构来结构的。就像莫里斯自己所言,“影片并非讲述谋杀案的故事,不是关于一项调查。其本身就是调查”()。在这里,故事即是形式。具体来说,这部影片以对案件当事人的采访串联全篇,包括亚当斯、哈里斯,达拉斯和维多两地的刑侦人员、警探,哈里斯的好友,以及律师、法官、证人,一共18个人的采访以碎片式的方式分散于影片中。采访素材中穿插大量风格各异的影像材料,如搬演的案发相关场景、新闻报道的文字和照片、历史/纪录照片、档案文字和照片,以及法庭复原画、早期好莱坞侦探片等,同时有多段主题配乐贯穿其中,营造出梦魇般的故事片气质。整体呈现出一种拼贴画的结构风格,形成了多文本多视点的复调叙事结构。
在碎片化的素材拼贴下,其叙事线索在剪辑的作用下还是比较清晰的。从亚当斯和哈里斯讲述案件发生的大致经过,到审判亚当斯、调查案件的细节描述,再到哈里斯犯罪前科和作案动机的发现,以及法庭证词细节、司法程序细节的披露,一步步明确了亚当斯被错判的事实,并以结尾处哈里斯招供的录音结束。如果说采访素材构成一种罗生门式的多视点叙述(telling),那视觉素材则更多是一种演示(showing),作为采访内容的视觉化呈现及视觉物证,与叙述出现的词语保持同步,并建构了一个有关过去的视觉化的叙事空间,与采访的当下叙事空间不断交互,共同指向那个十一年前真实存在的历史/记忆空间。其中的搬演镜头映衬着采访和画外音叙述,既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又以虚构的指示强调间离和审视,如风格华丽而充满悬念感的特写以及慢镜头,混合了当下与过去两种时间感的达拉斯的街道和城市夜景,以及虚构模拟的汽车电影院场景等等。过去的文字、照片等庞大的证据资料则以静照的形式渗入人物和历史的空间,与采访的当下空间形成深入而有趣的并置。而人物画像及侦探片影像则透过人物叙述的内容对其过去和当下的心理进行了审视和呈现。
这种拼贴形成的复调叙事不仅表现为多文本结构对叙事空间的延展,更体现于文本内部所呈现出来的对话碰撞和重复叙事,比如18个被采访者的叙述文本和多角度重复搬演场景各自产生的复调对话形式。在采访镜头中,导演只保留了被访者的回答而取消自己的声音(除了最后一个镜头的采访录音),没有画外音解说,让影片中的谈话保持一种自行诉说的状态,当事人在镜头前讲述各自记忆中的案发情况,形成多角度的叙述碰撞。而反复出现的搬演案发场景,其风格化的影像并非旨在还原现实,而是作为模拟当事人口述的假定性情境搬演,从而取消了单一指涉的确定性陈述。
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复调艺术有两个根本特点,即对话的创作原则和对话的创作手法。这两方面分别体现在创作者对待作品的观念和创作作品的手段上。“新纪录电影主张纪录片要反映后现代社会的‘多声部’和人撕裂的灵魂。”它们主张让各声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在导演的意志支配下展开事件。正如莫里斯的那句“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拍摄对象身上,也就是他们怎样看待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怎样看待他们”。()
二. 互文性和反身性
多文本的拼贴和杂交给影片带来了丰富的互文话语空间,这种互文性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影片多重文本及其产生的叙事空间之间的互文,二是文本与外部世界产生的互文。
第一层次的互文性主要表现在多重叙事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如前文所述,采访、照片、文字及搬演影像等文本共存于影片的叙事结构中,它们并非无序地各自分散,而是经由剪辑的作用呈现出多点映照的对话关系,不断相互生成新的指涉。
文字特写如报纸上新闻报道中抽取的相应词语、亚当斯观看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及其犯罪测试的文字结果、哈里斯犯罪纪录、律师穆德的胜诉记录等等,图片、照片的影像资料如罪犯和证人的新闻图片特写、手枪和车的资料图片、达拉斯和维多市的地图、相关人物资料照片、哈里斯犯罪现场照片等,此外则是搬演案发场景、好莱坞侦探片及法庭审判的复原画像。它们作为采访内容的视觉呈现和补充,将口头诉说转化为视觉文本的信息。同时,这些素材的插入还与叙述文本共生了一种情感联结。如亚当斯谈起地方法院只在乎如何对他行刑而不管他无辜与否时,穿插电椅的资料图片及特写,传达了亚当斯口中“噩梦”般的绝望感;如文字特写“Adams gets death”、“Adams guilty”分别配合律师和法官完全不同立场的叙述,也承载了悲观无奈和辛辣讽刺的意味;数次的搬演场景配合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词,在“确凿无疑”的叙述之外却暗示并展现着一种质疑和戏谑。它们在叙述文本的外部建构了一种与其相应的杂然交错的视觉文本。另外,视觉文本之间也产生着相互勾连。如哈里斯犯罪纪录和他当时的入狱档案照片、被毁的蓝色汽车和作案手枪的照片、其新闻报道中年轻的笑脸,以及童年的家庭生活照,勾勒出他部分的生命痕迹。而具有黑色电影元素的搬演场景和早期好莱坞侦探片的影像素材也形成某种互文关系。
第二层次的互文性则表现为影片文本和外部世界的相互指涉。首先如采访这种形式,是莫里斯纪录片叙事的一个关键因素,他的“谈话疗法”本质上是展开一种调查,“尽量打开一些不可预料的将要发生之事的可能性”。为此他甚至发明了实现第一人称视角访谈的“恐怖采访机”(Interrotron),并在1997年的作品《又快又贱又失控》(Fast, Cheap & Out of Control, 1997)中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方式采访。()而本片中人物正面面对镜头讲述的采访方式便已显示出第一人称视角访谈的意识。另外,采访在新纪录电影中是作为一种核心元素呈现的,同时也是对真实电影采访方式的吸纳和超越。其次,华丽的搬演场景具有黑色电影的风格元素,夜晚暗黑的城市街景、非均衡构图、低调照明及大面积阴影的呈现,再加上车灯对画面的勾勒、枪杀犯罪案件及深沉的配乐,使得搬演镜头展现出极强的故事片特质。同时,这种搬演风格还影响了后来的纪录电视、“真人秀”电视系列片的影像风格,如《NYPD Blue》、《警察》等()。再如,当法官讲述父亲在FBI的经历和米勒夫人讲述自己的“侦探情结”时,插入引用的好莱坞侦探片素材在他们各自叙述的映衬下形成一种戏仿的手段,充满讽刺味道。影片流露出的拼贴画式的实验风格和对影像素材的开放态度也暗含了美国60年代实验先锋电影的影响。
通过这种空前杂交的手法和技巧来突显纪录片对真实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反身性的策略。根据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纪录片中的反身模式主要探讨的是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过程()。而《细细的蓝线》所体现出来的反身性主要在于假定性搬演的场景和结构全片的采访场景中。
首先,不同于传统纪录片中搬演是为了真实再现,如格里尔逊评价《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1922)所言以实现纪录片“记录的价值”(),这部影片是将搬演作为一种风格化的叙事策略,直接提醒观众看到的不一定就代表真实,从而解构了通过虚构搬演以达到真实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一种自我指涉和对真实的超越。真实是必然存在却难以达到的,而我们只能以虚构的方式不断靠近真实。其次,如前所述,采访片段体现了导演一种不干涉的参与互动,即意图呈现话语和话语之间自然和多元的碰撞,这种手法在充满不言自明的矛盾和谎言的采访进程中产生了一种反身性。即通过这种采访的结构解构了话语和真实的传统关联,以及许多纪录片秘而不宣地通过“假面采访”(masked interview)()来“建构”的真实感。从这一角度似乎也可以理解影片结尾哈里斯招供的片段只呈现为一段录音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了(尽管还有采访当天导演只找到录音机的偶然性)。
三. 反讽意味和解构真实
在分析了复调叙事的拼贴手法及其带来的互文本性和反身性之后,《细细的蓝线》中后现代主义的反讽意味和解构思想也就不言自明了。
具体看来,影片在视觉素材的呈现、反身性的自我指涉以及片名与影片的互文中都表现出了反讽特质。在视觉素材的互文话语中,最明显的如好莱坞侦探片搭配法官和米勒夫人的画外音叙述造成的戏仿式嘲讽,法庭复原画像及风格华丽的搬演场景在矛盾和疑点逐渐明晰的过程中也充满戏谑意味,同时,亚当斯讲述格里格森医生对他进行犯罪人格测试时插入的图形图案,三个证人言之凿凿地描述司机形象时插入他们眼睛和耳朵的大特写镜头,以及报道上哈里斯微笑的头像映衬司法机构为保护年轻人而无视他的犯罪纪录等等,显示一种克制微妙的讽刺效果。在反身性策略中,透过积极干预并突显真实的建构过程,诸如对采访的建构、对搬演的建构,进而嘲讽了我们所看到的影像就代表真实这种认知方式()。另外,片名与影片文本中的互文更进一步表达了一种悲观而深刻的反讽。在影片61分钟处,法官讲述了他在亚当斯的审判中曾因辩护律师关于“细细的蓝线”的最后发言而深受震撼和感动,它象征着司法的保护力量,使群众远离乱世,然而讽刺的是,法庭现场本身就是一场虚假的集会,它将无辜的人错判,而法官和胜诉律师却将此案作为自己伟大的胜利之一,“细细的蓝线”最终也只是沦为了宣扬司法正义和自我感动的工具。
这种重重对立而杂交共生的文本话语同时也是间离的,让观众面对采访镜头时采取一种审视和观察的距离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画面背后隐含的社会现象。反讽意味和间离效果显示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质疑精神,既然真相如此容易被遮蔽,“现实”的影像又能保证什么呢?在面对如此难以渗入的有关过去的创伤性事件时,影片没有追求直接地再现过去,而是用虚构搬演的手段在有关过去的碎片化叙述中积极干预真实的建构,看似玩世不恭的手法反而揭示出一种解释的复杂困难性,即过去真相的不可接近,只能在重复和“事件之间的回响”中逐步挖掘。“并不是简单地揭露谎言以暴露真实,也不是拿一种制造嘲弄另一种制造,而是展示谎言如何作为局部真实对历史创伤的动因和证据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细细的蓝线》作为一部新纪录电影,不仅仅通过多样化的文本和语义及反身性策略干预真实的建构,以此反对直接电影将静观立场作为真实的基准,同时解构了传统观念中纪录片影像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将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思考引向了对真实更本质的追问和理解。既然影像就是影像,其与现实未必有直接关系,更无法保证真实,唯一能指向的是建构真实的过程,那就以开放态度对待文本,以多元视点呈现对抗,而真实的获得只能是相对的、偶然的或附带的。像影片结尾哈里斯的录音可以说接近甚至达到了影片追求的真实/真相,甚至他对于指证亚当斯的解释(因其没有收留一个帮助了他的人)与他在采访时谈到的童年阴影和对父亲的报复心理相映照,呈现出掩藏于深处的更为确凿的犯罪动机,即亚当斯在他的心理历程中扮演的角色重复了父亲曾对他造成的创伤()。然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不可忽略,哈里斯因为另一桩谋杀案被判死刑,所以才最终说出亚当斯是无辜的,并成为影片最有力量的一个段落。这一真相的获得可以说是导演在追寻真实道路上的一次特殊的成功,却也充满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哀愁。
就像林达·威廉姆斯所写到的,“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该混同于故事片。但是,纪录片能够而且应该采用一切虚构手段和策略以达到真实”()。尽管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真实被解构为碎片化的、相对的和不可揭示的,尽管连新纪录电影本身都在阐释与被阐释之间面对自我生存的困境,追寻真实本质的过程却具有揭示一切可怕的虚构和谎言的力量。
注释:
⑴ 梅根·坎宁汉,何一枝,宁茜.纪录片的艺术:15位导演、摄影师、剪辑师和制片人的创作之道[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第59页.
⑵ 孙红云.真实的游戏:西方新纪录电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第58页.
⑶ 同⑵,第102-103页.
⑷ K. Macdonald, M. Cousins.Imagining Reality:The Faber Book of Documentary[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6,p366.转引自孙红云.真实的游戏:西方新纪录电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第113页.
⑸ 比尔·尼克尔斯,陈犀禾,刘宇清.纪录片导论(第2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第194页.
⑹ 同⑸,第13页.
⑺ 同⑸,第177页.
⑻ 同⑵,第52页.
⑼ 林达·威廉姆斯,李万山.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续)[J].电影艺术,2000(03):120-124.
⑽ 同⑼.
⑾ 同⑼.
注:本文完整版已发表于电影文学杂志
- 毋庸置疑,莫里斯这个纪录片很成功,不管是从影片拍摄还是从社会影响方面。但是这种由参与者口述历史加部分再现的方式是否适合所有主题呢?
首先这是个谋杀案,所以在整个影片都有个悬念让观众继续看,如果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历史故事,这种口述的方式还会同样成功吗?现在确实有口述历史的纪录片,但是社会影响力却不大,更多的人是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坚持着做口述历史。从这个方面,莫里斯很成功,他虽然也是口述形式的纪录片却选择了非常好的主题。
除此以外,这个纪录片和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第二个区别就是,口述历史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参与者在说,而这个案件纪录片却能够将各个不同方面的代表的说法都呈现出来,律师、证人、被告、警察、朋友。。。能够将参与者都带到镜头前面来进行深入的访谈也是很有说服力事情了。
第三,在影片最结尾的地方,能够取得最关键的暗示性的证人伪证证词,这就达到了反转的效果。小男孩在最后自己说:他是有罪的,因为他在深夜让一个无家可归的我留宿街头而不让我借宿。实际上这句话反面就说明28岁的被告并没有杀人。他只是在得罪了反社会型人格的小男孩罢了。
第四,叙事方式。整个故事结构是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展开的。可是说是不停的重复整个故事。但每一次故事的重复都加入了新的信息。先由正反两面来称述自己那天晚上干了什么。然后由警察说明他们和案件的联系。然后再由两个人称述自己对案件的说法。然后警察称述观点,然后引进来律师,其他目击者,其他人对这些后来出现的目击者的怀疑和评价等更多细节的信息。就像一个树形的叙事结构,从顶点到最后的一个扇形的信息和,观众不断的被新呈现的信息吸引,然后和导演一起猜测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第五,摄影。近景的人脸没问题,但是头顶总是被切掉了一部分,一般来说,采访的时候,人的头顶离边界会保持一点距离。这个片子这种构图不仅切掉了头顶,同时也没有遵循三分之一的摄影构图法。这个影片采访的时候,人全都放在了画面的正中间,没有往右偏一点。也许这就是导演可以营造的,起强调作用。
第六,音乐和灯光很加分。 嫌疑人在2004年被执行注射死刑

报道来自NBC-美联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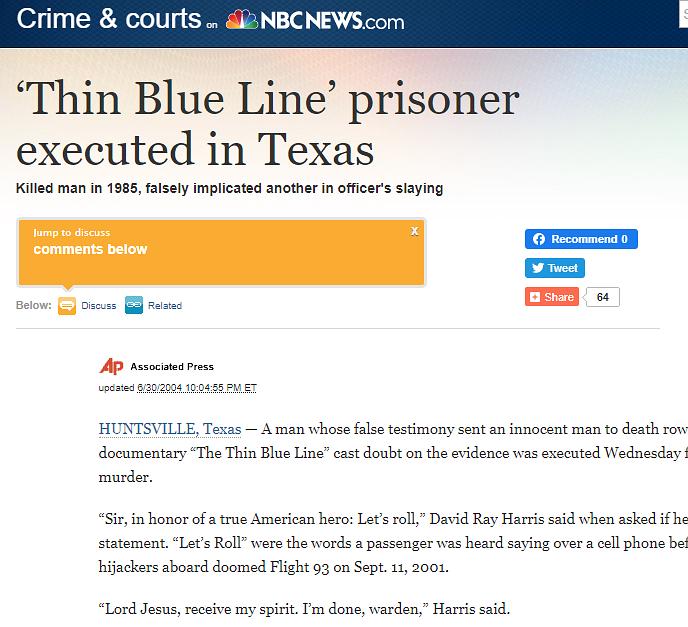
本案被释放的亚当斯在释放后因为讲了自己的故事而起诉了导演,后庭外和解。
他于2010年脑瘤过世,终年61岁。
Randall Dale Adams, a former death row inmate who gained freedom after flaws in his conviction for the murder of a Dallas policeman were exposed in a critically acclaimed documentary, has died. He was 61.
He had never received any restitution for his many years behind bars, said Schaffer, and he later sued Morris to regain the right to tell his own story.
他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他的律师在他死后一年才广泛报告给媒体,美国的一些重量级媒体都做过报道。

本片《正义难伸》获得1989年金马奖非正式竞赛单元-最佳外语片

- 二十几年后看这部纪录片本身,感觉不到特别的震撼,可能是此类题材已经被好莱坞和美剧用滥了。
赋予这部影片真正的是背离纪录片本身的电影化拍摄手法;创作者先知般的敏锐捕捉力;后续发展为影片带来的传奇色彩;以及真正属于纪录片何为真实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