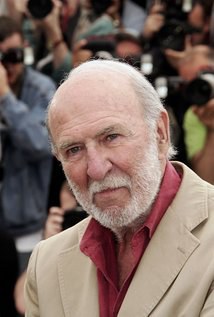明天我们搬家 Demain on déménage(2004)

又名: 同阿妈搬大屋 / Tomorrow We Move
导演: 香特尔·阿克曼
主演: 西尔维·泰斯蒂 奥萝尔·克莱芒 让-皮埃尔·马里埃尔 娜塔莎·雷尼埃 卢卡斯·贝尔沃克斯 多米尼克·雷蒙 艾尔莎·泽贝斯坦 Gilles Privat 安妮·考森斯 克利斯汀·哈克 Lætitia Reva Olivier Ythier 乔治斯·西蒂斯 Valérie Bauchau 卡特琳·埃梅里 Nicolas Majois 娜德·蒂约 科伦丁·洛贝特 艾力克·高敦
类型: 喜剧
上映日期: 2004-03-03
片长: 110分钟 IMDb: tt0328990 豆瓣评分:7.5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讲述一名母亲在丈夫死后带着钢琴、行李和家具搬来与女儿同住。正埋首写色情小说的女儿因宁静生活不再而没有了创作灵感。居住环境变得挤逼,决定卖房子搬大屋。因而出现一连串来看房子的人,他们都是梦想搬家的人,亦各有自己的趣事。轻松有趣的情节由始展开。
演员:
影评:
在《》之后,香特尔·阿克曼一直有意回避再拍一部《让娜·迪尔曼》。不过,香特尔剧情长片中的母亲形象,贯穿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以依靠的轨迹。
确切地说,是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母亲形象。从2004年的喜剧《明天我们搬家》往1975年开创性的《让娜·迪尔曼》回溯,母亲是大屠杀幸存者的这重身份总是迂回但明确的。
《明天我们搬家》开场不久,西尔维·泰斯蒂饰演的主人公夏洛特随房产经理波普尼克去看某个待租房间,他们一走进去便发现,这房间刚刚被熏蒸消毒过,残留着消毒药剂的气味。当他们打开窗,看完房,坐在窗口呼吸的档口,发生了古怪的一幕。老波普尼克忽然说:这气味让他想起了波兰。对此,夏洛特并不惊奇,只是应和:是的,我知道。

这对刚刚相遇的路人立刻认出了彼此,老波普尼克说,“我在波兰失去了全家,”并意识到:夏洛特也是波兰人(幸存者)的第三代。 集中营、焚尸炉或“齐克隆B”的名称并未在影片中提及,但无疑暗示了奥萝尔·克莱芒饰演的主人公母亲有着和波普尼克相同的经历,同样暗示了母亲的父母亲很可能也在集中营丧命。




回到《》(1986)中那条人人为情所扰的地下拱廊街。主人公罗伯特的母亲,由德菲因·塞里格饰演,并且也叫“让娜”。这位让娜有夫有子,在商业街经营时装店。她的生活看似无忧无虑,打点生意利索,在商业街人缘也不错,直到遇见她曾经的美国情人伊莱。伊莱对当年让娜的不辞而别耿耿于怀,同时他道出让娜与他的相遇缘起:集中营解放之后,他曾收留和照顾让娜。

1982年拍摄的《》,真实母亲娜塔莉亚·阿克曼的出境唯有出神、沉默和空白。

再往前是《》(1978年),这时奥萝尔仍是“女儿”,她饰演的安娜在科隆火车站与从比利时移居德国的旧识伊达相遇。随着两人谈话的深入,表面上看起来伊达对安娜多次违反与自己儿子的婚约心有怨气,但当伊达越说越多,说得忘记了身边有人存在(请注意,此时安娜挪动了位置紧挨了过去),她想起的是家庭与战争的记忆。正如伊达和安娜一见面就提到的,暗示了伊达在集中营失去了亲人,同时伊达又说她待安娜的母亲如姐妹,也就是说,伊达与安娜的妈妈极可能是在集中营里同时幸存下来的。

最后,我们回到这个母亲形象的起点:《让娜·迪尔曼》。绝大多数对让娜的描述会是一名寡妇、主妇、妓女,或一个女人。这固然不错,但当我们细看第一晚临睡前,儿子西尔万问让娜是怎么和父亲相识的时候,母亲的回答暗示了此处的让娜和《黄金八十年代》中的让娜重名并非巧合,她们可能同样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往往被忽视了。

这一晦暗的事实有助于愈加照亮影片结尾(即让娜完成杀人后,长达5分多钟的呆坐与出神)的结构性意味。如果把结尾比作最终的且暴力的休止符,那么在影片所描述的3天时间内,类似的休止符早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但是,正如一段乐章不可被归结为一个点,让娜频频的出神也无法由单一的原因解释。确实,第二天下午那锅煮坏的土豆打乱了让娜的阵脚,但扰动让娜的仅仅是嫖客的插入?还是午后咖啡馆里的那杯咖啡?抑或上午邻居的那一番话?提前开火炖煮,难道不是如所有主妇般周周如此?这一扰动可不停地往前回溯,甚至溯回电影开始之前,如让娜的出神一样,它们都只在画外。或许追溯到前一晚姐妹的那封信,或许追溯到读信后、临睡前西尔万对母亲的发问:你是怎么认识父亲的?要是他很丑,你会想和他做爱吗?你还想和爱的人再婚吗?让娜忆起了一些事,可能是某件具体的事,可能是涌出的记忆碎片,实际上,让娜的世界至少早在第一天夜晚就崩塌了。
在几十年后香特尔的追忆中,她称《让娜·迪尔曼》也是一部关于“遗失的犹太仪式”的电影。对应让娜的出神,犹太安息日(Sabbath)本可以在世俗及神圣间分出一条界限,让人在“止息”的同时与更高的存在一同呼吸并继续存活。然而,让娜或母亲有家但没有神、有重复但没有仪式,这种现代生活是非常世俗和序列性(seriality)的,且与集中营的设计高度同构。两者的区别在于:集中营生活在极权主义压迫下剥夺人的人性,使其如动物般要么生要么死;战后的现代生活则至少看起来是自由的,但人们往往在不断自欺的间歇中感到存在的焦虑。“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这也正是莱维归纳“为何集中营内少有自杀,但回归日常的幸存者却自杀频频”的原因之一。

擦鞋、购物、邮寄、做菜、接客、编织……为了回避可怕的闲暇,让娜将一件又一件事填满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拒绝去思考它们,正如第二天临睡前西尔万再一次打开话匣子,这一次让娜却假装没听见,关灯,睡觉。可是,也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已形成肌肉记忆的姿势,使让娜·迪尔曼在她的动作中有了腾出时空的可能,在瞬间出离到她自身之外,重回她经历过的一个个暗夜。
在香特尔后续的创作中,我们会不断看到这种“出神”(ecstasy),也即存在者跳出浑浑噩噩的自在存在之外,意识到他者、外部世界和自身同时的存在,也意识到大他者对自身之凝视的可怖。香特尔镜头中不同的角色将怀着不同的记忆和思绪,但共性和关键在于:他们是作者对具体的、出神的母亲形象进行的普遍化或变形。如香特尔所说:“大屠杀是一个无论如何不能直接处理的主题。虚构和游戏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在重写(rewriting)这个故事,但每次都不同。”

显然,《明天我们搬家》是同一主题的再一次重写,结构上类似于《长夜绵绵》将布鲁塞尔的爱情纠葛超现实地置于同一夜晚,这里的每组登场人物都同时地想要搬家看房,最诡异的是,他们带着明确的目的看房或带人看房,但都不知不觉地开始走神,每一位都如让娜·迪尔曼或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一般,等一盘菜做好或做坏了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期间是一次次“灾后”小小的内爆。
夏洛特母女从《安娜的旅程》片场走出来,经过《提行李箱的人》,现在,母亲成了钢琴教师但刚刚失去丈夫,搬去和女儿住在一起,她没有丈夫的遗物在身边就睡不着觉。影片一开始,妈妈吃着烤鸡莫名地流泪了:“这些鸡太小了,死得太早,哪怕多活一天都更好”。夏洛特则是一名正受委约写色情作品的文艺工作者,她也不知道是父亲的死、母亲的到来、还是这该死的工作本身让她不在状态,于是她唯一的注意点莫名地变成“窗帘真脏”,为此她想把现在的家卖掉后换个地方住。


德拉克尔夫妇是从《黄金八十年代》片场走出来施瓦兹夫妇,明明是来看房,德拉克尔先生总一个劲儿地问自己的老婆在哪儿,德拉克尔太太则永远在自己的世界里,听到匈牙利舞曲也不顾众人就兀自跳起舞来。这证明了“空巢综合征”是语用的懒惰,人的肉身和精神并不一定总住在同一个巢里,她看起来总是“掉线”,然而德拉克尔太太在夏洛特的房间里能立刻感受到另一个看不见的巢,并精确地掳走夏洛特外婆的日记。


孕妇则是从《》片场走出来的朱丽叶,她乐观开朗,下周就要生产,笑着朝向未来,世界或夏洛特的房间在她面前就是惊奇,但她却突然说:我不想要孩子!在香特尔那里,出神的分量往往是最重的,但在《明天我们搬家》中,这些沉重的东西在不同角色的“出神”和“回过神来”之间来回接抛、摆荡。当一个烤着鸡的烤箱放出一屋子的烟——烟的味道,爱吃鸡的人,鸡的配菜,鱼和大海——在思绪飘到焚尸炉的烟雾之前,大家回过神来,是百里香的味道——百里香,自然的味道,花朵,往事,老祖母,家族和血脉……嘴上说着同一句“比例匀称、价格公道、抢手货”,在不同的人心里飘向了不同的所指,这个说的是房子,那个说的男人或女人,这种“文不对题,货不对板”产生了喜剧效果,然而所有人的交流和关系,不正在建立在我们彼此走神的绝对差异性之上吗?确实早有评论者点出,这是一部“犹太电影”,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搬家(dé-ménager),是指离开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这种出离不仅仅时刻会发生,同时对存在者而言也是必要的,在这里,阿克曼无疑追随着列维纳斯。


这部片中,犹太女孩香特尔并不避讳自传性:母亲的经历、父亲的过世和一个接受委约的文艺工作者——“泰斯蒂有点像是我的安托万”,她说。曾在多次访谈中提及,外婆的日记是真实存在的:“我无法说全我的感受,只因我是一个女人,唯有对着纸页书写。”一旦提及外婆的话,或这条母系家史,奥斯维辛就是绕不过去的,但在一个唯有幸存者的世界,《明天我们搬家》里没有任何一处直接指涉大屠杀的地方。


实际上,围绕《》(1985)和《》(1993),欧洲电影世界开展了围绕“大屠杀图像是绝对不在场的还是可被再现的”争论,朗兹曼、戈达尔、朗西埃、迪迪-于贝尔曼等人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应。毋宁说,《明天我们搬家》就是阿克曼的回答,在这里她追随了列维纳斯/朗兹曼,或恪守了“不可造(图)像”的诫命。《明天我们搬家》与直接以奥斯维辛为题材的喜剧《》完全不同,这“拒绝再现”的效果是什么?或许没有比“出神”更好地形容观看香特尔电影时的状态了。当看到夏洛特和妈妈去郊外看房后走在田地里,你是会出神的:在一组推轨镜头中,有牛、有羊、有带栅栏的一片绿色,正如从《》到《浩劫》中那片恐怖的翠绿一样,“绿色,但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绿色”。






大多数人不会否认,90年代开始的“流亡地图学”纪录片四部曲(《》,《》,《》,《》)是晚期阿克曼的丰碑。与此相对,同时期的剧情长片(《朝朝暮暮》,《》,《》,《明天我们搬家》)往往被指为“并不成功地”走向主流与商业。这一时期啊香特尔确实花了很多力气在纪录片和艺术装置上,但和更主流的剧情片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几部剧情片中的运动确实更轻盈,不过香特尔对存在状况的关切并未有过任何改变,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就是在《》之后刻意回避同性恋形象这么多年(她更多地追随普鲁斯特,往往以旁枝逸出或者以异性恋关系取而代之),破天荒地在《明天我们搬家》的结尾展现了多元成家的图景,孕妇诞下了孩子,搬来和夏洛特一起生活,这个婴儿“有时叫西蒙,有时叫西蒙娜”,“孩子慢慢长大,有两个妈妈”。和那许多个令人绝望的结尾相比,这该是为数不多的明亮的阿克曼结局之一了,这一次毕竟是喜剧。

参考资料
Nicole Brenez, “Chantal Akerman: The Pajama Interview”.
Mateus Araujo and Mark Cohen, “Chantal Akerman, between the Mother and the World”, Film Quarterly, Vol. 70, No. 1 (Fall 2016), pp. 32-38.
Marion Schmid , Chantal Akerma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cques Mandelbaum, “Demain on déménage”, « Autoportrait de Chantal Akerman en Cineaste », Cahiers Du Cinema, 2004, p. 214.
宋立宏,孟振华,《犹太教基本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信出版社,2017。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走出黑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
纯粹的阿克曼,始终流动的幽默感来自隔一层人际交往中的纯粹。而人物的神经质有了音乐的打底,更渗透进有趣的真实。音乐是真正的麻醉剂,跳动的旋律,不止的心率,让一切看起来变得不可思议。
“我没痛苦,只有眼镜,真麻烦”。
搬家是整理房子的动力,错落在各角落的花束散发出亲昵的香气,爱情与色情并不是日常,但却可以是首拼贴诗,而我的任务就是拼贴起掉落在生活中的碎片,这便是生活的真谛。
-如果我没死,他会从头来过。 -孩子会改变男人的。 -对于夫妻,人们说搬家就是终点。 -什么的终点?夫妻的! -你这么看?那我等不及要搬了!
因为不舒服感觉到很冷;因为百里香太多,陷入的回忆就越多;因为决定有所准备却还是说走就走。生活难以捕捉(正常人缺乏品味),但却可以实践(让别人来告知你)。
当你了解生活,色情的也可以是现实的,就像每扇门的后面都有男男女女吆喝着再来一遍。特定的现实在自身中寻找,不是鄙视,是怜悯。
略带阿克曼以往装置艺术的影子,亮点在于房间内的场面调度,很生动活泼,但可能也因此缺乏一定的深度,尤其使用了大量对白后。
对于女性所处不同境遇的探讨,几乎全部集中于一所公寓内,将如此多的内容进行组织,可见阿克曼功力,但整部还是属于轻喜剧的风格,使用了大量的对白和人物的调度,让人觉得有点话痨片的感觉,与以往导演作品风格差异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