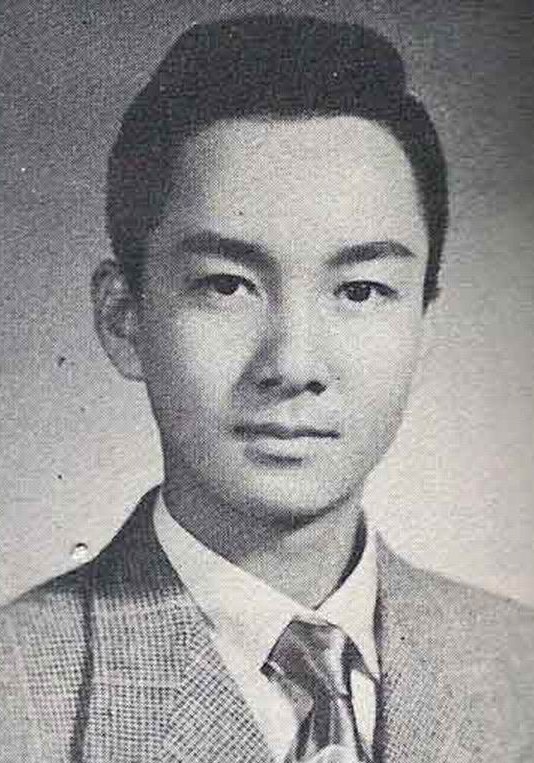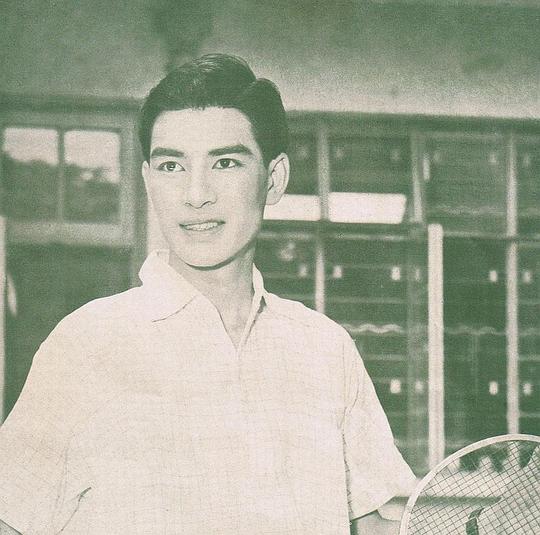南北和(1961)
简介:
- 广东人张三波(梁醒波 饰)和南方人李四宝(刘恩甲 饰)租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两人又同样经营着洋服店,互为竞争对手关系的他们之间常常因为生意问题而产生矛盾,生活中也经常因为南北习惯的差异而爆发争吵。
演员:
影评:
- 前幾天在Youtube看了王天林導演,宋淇編劇的《南北和》,講當時香港本土人(南)和因避戰禍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北)的矛盾與和解,是主題健康的戲劇,健康喜劇的健康,就是健康麻將,健康相聲的健康。
劇情和當下比較,頗多感慨。
和當時的邵氏相比,電懋公司出品的電影主題健康的多,最終都是以大團圓南北和收場,主題健康的戲劇頗不易寫。但這部寫的很好,大的方向,南北和。小的細節和對白上,對南人北人的刻畫非常鮮活有趣,當然是對白寫的好才有這效果。
其實那個時代香港的南北矛盾和現在差不多,本土香港人不及內地新移民(主要來自上海)有錢,但看不起新移民不懂講廣東話,不夠醒目。港人精於算計,但目光短淺。而北佬則喜歡吹水,窮要面子,不切實際。但比較熱情豁達。
最終彼此都願意向對方學習,也願意自我檢討,承認錯誤。
兩個主角都是胖子,演的非常好。
可是現在來自國內的新移民土豪,沒有那時新移民的修養,本土香港人也鬧起民粹一味排外,根本沒有溝通對話可能,南北和是絕無可能了,沒有動手打起來已經算是好。
當時編劇是基於社會現實寫對白,我們可以知道一層唐樓一個月的租金才300塊,而7000塊就能買層唐樓了,一台雪櫃的價格是4000塊(支持分期付款)。那時的導遊已經會帶遊客(主要還是水兵)到固定店鋪然後抽佣。那時的香港南腔北調,但還沒有那麼多人,出來做嘢,大把機會給年輕人出頭,對未來充滿信心,南北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事。
同時,那時的香港還是個中國味道比較重的社會,家庭倫理仍是第一權力,父親不同意,女兒便不敢出門。雖然自己出來做嘢搵食,經濟獨立,但仍然未夠膽挑戰父權。反觀當下,還有幾個子女對父母唯唯諾諾,尊重父權?
舊時電影,也許節奏不夠現在電影緊湊,黑白影片,表達景物更是有限,但那時人人愛看電影。放在如今,這樣劇情輕鬆有趣對白鮮活生動的電影,也屬佳片. 这是我所看到过的国产喜剧片中比较起来使人满意的一部,既不架空又不俗滥。大结构是“喜剧”骨架,细部则用“闹剧”处理,笑料够多而根源于现实生活;除了一两个人物的性格,尚有可议之处,大体上已算得一部像样的喜剧片——如所周知,国产片中是少有像样的喜剧的。
戏剧大师们写喜剧,如莫里哀、莎士比亚以及萧伯纳,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大结构是“喜剧底”,细节则是“闹剧底”;也就是说题材与人物,根源于真实生活,但在小事件上加以闹剧式的夸张。像莫里哀的《悭吝人》(The Mister),题材与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所有,最近本港报上还登载过一位千万富翁,家里只用一个佣人,还亲自上街买菜的事;自然这位千万富翁却不会如莫里哀所写那样,让这个仅有的佣人,做厨子时穿厨子衣服,做车夫时穿车夫衣服,当场忽穿忽脱的——但这一种闹剧式的夸张,不仅使戏剧的演出增加笑料,也更突出地表现了讽刺意味。
我们国产片喜剧的写法,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题材和人物是架空的,写不存在的人做不可能发生的事,根本使观众无法相信,更不用说有亲切之感而“会心一笑”了;但细节上偏又去“写实”,弄得一点不可笑,即有“笑料”也是陈套滥调,这样的“喜剧”,看了只使人啼笑皆非。
本片却是一张可与许多西片上乘喜剧比美的片子,以新春上映的西片来说,不逊于《鸳鸯福禄》(Cinderfella。1960),好过《宝城福星》(The Wizard of Baghdad,1960),《袋袋平安》(Not Wanted on Voyage,1957)更望尘莫及。外省人大量到香港已逾十年。但“南”人与“北”人之间仍有许多不“和”之处;我以为这里面语言隔阂还在其次,主要是“南”人与北人对人对事的态度方法不同之故。而这态度与方法自是源于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教养所形成的性格一部分;本片的喜剧由此产生。故此喜剧的条件——“源于性格”,而且现实。
但细节则是夸张了的,如梁醒波、刘恩甲双方竞贴减价告白(这里还用了慢摄,使动作看上去特别快速),两人同时唱京戏与粤剧;如冰箱及西瓜的“重复”使用(重复也是喜剧中极有效果的手法),丁皓、张清与白露明、雷震两对的“重复”交换座位,诸如此类的地方,笑料都新鲜有趣,而且有突出的喜剧效果。
本片可喜之处,首先便是给国片建立了一个喜剧的楷模,正如我一向赞扬李翰祥为国片建立了古装片的楷模一样;还有可喜的一点,便是打破了国语片之“国语”这一枷锁。国语片自然应以国语为基础,但过分拘拘于所谓“国语”二字的结果(尽管许多“国语”片演员,其实说不好国语),却使对白成为一种架空于现实的死语言,因为在今日的现实生活里,不是各种不同籍贯、不同教养、不同身份的人,都说纯正国语的;我记得在《杀机重重》的影话里,我曾为这一点发过牢骚,其实在英语片中(别的语我完全不懂,但想来也应相同),为了表现地方色彩,人物的出身、教养、身份,也不一定说“纯正”英语的。苏格兰“高地”话、爱尔兰方言、下层社会的俚语、美国西南部土腔,都照样使用,观众自然未必全懂,但并不妨碍他们对剧情的了解,为什么我们非要“纯正”国语不可?本片兼用国粤语,不仅观众决未因此难于了解,许多喜剧效果也由此而产生,更形成一种亲切真实的感觉;片中还让国语演员说半咸半淡的粤语,粤语演员说半咸半淡的国语,同样无伤大雅,反突出地表现了由“南北不和”到“南北和”的主题。
唯一可议之处,是在一、两个人物上,其中有属于表演的问题,但也有性格基本上处理的问题。本片表现了“南”,“北”做生意的方式不同,由梁醒波代表了广东人的保守,由刘恩甲代表外省人的“海派”,在人物描写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梁醒波表现出这人物的性格、气质,而刘恩甲身上却无“海派”气;这自然属于表演的问题,以喜剧的感应和“点送”来说,也是梁优于刘。
根本有问题的是雷震这个人物,他与丁皓代表年轻一代的“北”,和白露明、张清代表年轻一代的“南”对峙;其中丁皓、白露明、张清三个人物演对了,只有他不对。他既然是很年轻就做到一家大公司经理,则其对人对事对生意对恋爱,都应该很“司麦”,才合于他的身份,不应该是如此老实傻气的青年;而且他一定要“司麦”,才能与张清成为“南”、“北”对照,就如刘恩甲之与梁醒波成为对照一样,现在他看上去与张青没有什么分别,就显不出从“南北不和”到“南北和”的意味。影响到整个成为“偏枯”局面,只能在生意上看出“南”、“北”之异,而在谈恋爱上看不出不同之处。这责任自然不一定在演员身上,可能是剧本如此写,也可能是导演对剧中人物的性格,做了错误的“解释”。
1961年2月23日
- 电懋创作的一个很轻松的喜剧小品。梁醒波和刘恩甲都是很好的喜剧演员,就这部片子来看,梁更突出一些,他的表情动作都很丰富,明显有舞台演出的经验。在《鸾凤和鸣》里,二人再次同台任主角,刘恩甲就更好。
这个片子现成搬到话剧舞台演出都不用改动的。戏里出现的冰箱、日本料理、咖啡馆约会、空姐的职业等,都表现出香港当年资本主义的繁荣程度,也有社会学研究价值。
剧中的南北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经商的观念、饮食的习惯、说话的口音、生活方式的不同上。我是北方人,但是在南方念的大学,当时至少一年时间都在经历饮食上的激烈变化,努力适应南方饮食习惯。到现在,南北方饮食我都很欣赏。吾国国土辽阔,习俗差别之大,不是亲历,未必有这部戏里表现出的这么鲜明有趣的体会。
粤语演员说粤语,国语片演员说国语,两种话杂糅在一起,听起来也蛮和谐。不同而和,有了不同,才有“和”的必要,也才有“和”的价值。
片中两位女主角丁皓和白露明争论,白说:都说南国佳人,什么时候听说过有北方佳人啊?
丁说:孟子说了,南蛮南蛮,南方人不野蛮吗?
这些都是谐趣而不粗俗的对话。可为之一笑,则这部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