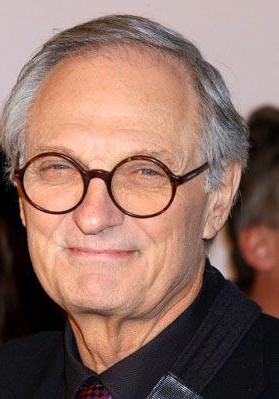世纪的哭泣 And the Band Played On(1993)
简介:
- 一部追击全球各地真实个案,揭示“爱滋”真面目的电影。影帝李察基尔领衔主演,好莱坞十大红星全情参与,唤起举世瞩目。本片由真人真事改编。
演员:
影评:
前几天大半夜在客厅工作,电视机开着刚好转到HBO,正播着And the Band Played On,瞥了几眼,竟然不知不觉把手头的工作给放下了,等片尾字幕出来,才发现,一不小心就给看完了。 当时电影已经播了大半,正播到疾控中心(CDC)的某场会议,会议上,有学者正式提出以AIDS来命名这个新型传染疾病,取代“gay cancer”这些坊间称呼;更主要的是,CDC专家提出艾滋病毒可能透过血液传播的假设,并建议政府对输血进行限制规范,血库的血样进行测试排查。唇枪舌战的不止两方,同志团体首先对输血限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于同志赤裸裸的歧视;而血库官员们则认为CDC只拿得出一个案例证明艾滋病毒的传染和血液传播存在联系的假设,薄弱的证据使得政府认为不值得为此立刻耗费难以想象的人力财力去采取行动;而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家属激动地反驳,一个病人为了治病却导致被一种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病毒致死,难道不应该采取保护措施么?这根本无关歧视。夹在中间的CDC专家,电影主角Don Francis最后拍案而起,如果公共健康和疾病控制还要用效益来衡量的话,如果一个、几个病人的感染与死亡不能够引起重视的话,请问要死数千数万人,直等到诉讼费用比开发预防措施费用更高的时候,政府才会采取行动吗?事后,Don因为这番话被他的同僚和上司指责,这样情绪化的宣泄,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CDC在对艾滋病的研究上更举步维艰。 关于80年代艾滋病爆发的故事,不难让人联想到上一年另一套同是HBO推出的电视电影《平常的心》(The Normal Heart),不过这两个故事在人物和情节上却并没有什么重叠。相对于取材于自身经历,视角集中在同志圈的悲欢离合的The Normal Heart,改编自同名纪实小说的And the Band Played On涉猎点更广,从CDC专家孜孜寻求新型传染病的病毒、传染途径和预防治疗方法出发,回溯了80年代艾滋病爆发对科学界、同志圈和整个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也正是因为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接触面信息量太大,都是干货,才让这部两个半小时长,采用同样平铺直叙、纪实风格的电影并不显得冗长无聊。 影片的主线从CDC的研究员Don Francis举步维艰的研究入手,在迷茫和疑问中,企图抓住狡猾而致命的恶魔的尾巴,眼看着感染与死亡的人数几何倍数般疯狂增长,而那微乎其微的成果与发现,却因为不够坚实而难以将理论化为行动,调查与研究的困难艰巨到难以想象,而他和他的同事们想做的,不过是尽快以科学的方法了解这种疾病,治疗感染者,并使已接近失控的传染速度得以减缓。 而他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这种难以捉摸的全新的疾病与病毒本身,这段历程更折射了同志圈、美国政府甚至科学圈的群像。 艾滋病这个无形而冷酷的杀手,对于80年代同运高涨,欢呼着our time has come的同志圈来说,就是死神的真实化身,悄无声息地随时随地他就举起镰刀,亲临家门。有些如那个在LA的病人一样,死亡临近的步伐让他发狂崩溃,开始怀疑这是否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而如Richard Gere扮演的编舞家,疾病的征兆让他万念俱灰……正如在The Normal Heart中所反映的,这个原本应当是CDC研究成果受益最直接的群体,却在关于疾病的科学研究面前严重分化,有些积极合作,并为自己的群体寻找出路;而有些则讳莫如深,在关于是否应当关闭旧金山同志公共澡堂的听证会上,他们慷慨激昂,声称公共澡堂是他们平权和自由的象征。但是,如果我们都死了,那还有什么捍卫权力和自由的必要呢?欢呼的海洋中,夹杂着这么一个微小的声音。同运活动家Selma在Don耳边说,他们这样,只是因为他们惧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类的本能反应是否认和抗拒;而尚未享受多久自由的空气和骄傲,内心深处那曾歧视被拒绝的恐惧依旧存在,而他们担心,随着艾滋病与同志群体挂上钩,将会让那些噩梦再次重现,这双重的恐惧,让艾滋病成为他们最真实的噩梦,也是最隐秘的禁忌。 而另一方面,同样抗拒着艾滋的,还有一众公共机构,事实上包括CDC本身。他们惧怕在尚未足够了解这种疾病之前,过早地下结论采取行动,除了虚耗财力人力,更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恐慌。假设与结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特例与个案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究竟该等足够多的信息来保证政策的无误,还是应与病情蔓延的速度赛跑……人们谴责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官僚和冷漠,而在这种保守与隐瞒背后,更反映的是他们的怯懦,他们怯懦,他们冷漠,他们官僚,他们保守,是因为他们同样恐惧,生怕有所作为造成更难以控制的后果,生怕被公众指责没有尽责,倒不如无所作为,坏结果总比更坏的结果好。 然而,无所作为并不能保持现状,隐瞒事实并不能阻止流言四起。到了1983年,艾滋病已经不仅仅在同志圈内引起恐慌。大众以仇恨与宣泄来排解恐慌,艾滋病患被当做生化危机对待,甚至有护士不愿意治疗艾滋病人;艾滋病人在生活中遭到歧视恶待,反对仇恨同志的标语示威四起;保守分子在电视上鼓吹这种疾病是上帝对性滥交和同性恋者的审判……当群体中出现难以控制的威胁时,只有把这种威胁驱逐出群体,与之划分界限,才能保证群体的安全感。 这些恐慌、仇恨与排斥,是让科学家在追寻真相的路上举步维艰的障碍,却也正是促使他们必须加快脚步的动力。造成恐惧有种种原因,但最直接根本的,却是无知和异质化。在艾滋病的爆发和研究预防的历程上,更能看到疾病并不仅仅与病患和医生相关,更能影响社会,塑形社会心态的形成,而要打破病态的社会区隔与心态,唯有始于科学工作对疾病的解魅。无论是同志圈中的惊慌或抗拒、公共机构的隐瞒与漠视还是大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化,都是在发出恐惧的讯号,而唯独只有科学家必须力排众议,去聆听他们的声音,用科研来找到消除无知,化解恐惧的方法。 而这个故事除了透过科学家的脚步将这些不同群体串联在一起,还有另一个画面不停闪现,从里根当选总统开始,宣布将国防作为财政预算的重点对象,里根获得连任,里根讲话……国力强盛,民众欢腾,一派歌舞升平,在电视画面里只有掌声与欢呼,却没有这个本世纪以来最令人恐惧的疾病的声音,与压抑在病患与大众内心的哀号尖叫。片尾的后续介绍中写道,当里根总统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及艾滋危机的时候,已有两万五千名美国人死于艾滋。公众的声音不仅需要科研人员们去聆听,去表达,也需要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领袖去聆听。虽然公共媒体大肆报道艾滋肆虐,但官方声音始终保持缄默,研究艾滋经费的不翼而飞,里根政府的沉默,是笼罩在美国上空比之艾滋更巨大的阴影。 而让Don失望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战友之间的分歧。Dr. Gallo和法国科研所就发现艾滋病毒专利上的争吵与官司长达数年。最初发现新型疾病的兴奋,破解密码的激情,最终都被追名逐利所取代,甚至因此可能会耽误对疾病的防治进一步研究,都在所不惜。 影片结尾再一次回到了旧金山,1985年11月的同志烛光大游行,气氛竟是肃穆沉重,没有了四年前万圣节游行的一派狂欢。一直与CDC合作的同运人士Bill Kraus感染艾滋入院,Don赶去看望,在病榻前,Bill问已经离开了研究艾滋岗位的Don,我们究竟能不能战胜艾滋。Don看着Bill,说,不知道。 与艾滋战斗的序幕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而这悲哀有时甚至并不和疾病本身有关。喜欢这部影片可能是在于它并没有着重于歌颂人性的伟大,映衬着这个伤感的结尾,And the band played on,也不像是献给孜孜不倦与疾病作斗争的斗士们,在这时说起,似乎更带着无奈,疾病不会停止,所以,总得有人继续跟它战斗下去。 P.S. 影片的片尾曲的Elton John的The Last Song,写的是一位父亲和他同志儿子之间的感情,歌曲中那句I never thought I'd lose, I only thought I'd win尤为伤感。 P.P.S. 片尾导演剪辑的视频是死于艾滋或者曾积极参与抗艾活动的名人的影像,比如戴安娜王妃,Freddie Mercury,而最让我惊喜的面孔是福柯,还有Larry Kramer,也就是The Normal Heart的原作者,终于在这里找到两者间的交集了! P.P.P.S. 这片绝对是众星云集,最赞的还是Ian爷爷的精湛演技。 P.P.P.P.S. 影片的一开头是70年代,Don来到非洲调查一种严重的传染疾病,导致整个村庄甚至医生全体死亡,幸存者的质问和濒死者的哀求成了萦绕Don一生的梦魇。字幕介绍,这种在非洲流传的传染病在尚未扩散到全球范围前就被控制住了,但是却成了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前兆……这个恐怖的致死疾病正是埃博拉病毒。当防艾工作普及,有研究表明艾滋病毒已经开始衰退,埃博拉病毒却再次卷土重来,在此时看到这部影片,似乎再讽刺不过。或许比起某一种病毒更长久更可怕的,是疾病本身,也是人类恐惧本身。And the band played on,在2015年,又有了新的含义。
- 「I may be down, but I'm not out.」
「I would rather dies as a human being than continue living as a freak.」
「How many people have to die to make it cost efficient for you peopl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Give us a number so we won't annoy you again until the amount of money you begin spending on lawsuits make it more profitable for you to save people than to kill them.」
「Let me ask you this: When doctors start acting like businessmen who can the people turn to for doctors?」 - 这是部根据真实生活拍摄的戏剧电影,该片详细介绍了艾滋病在美国的出现,以及为了治愈它而对官僚主义和社会进行的抗击。12年9月13日想看,迟迟拖到今天才看,敬佩那些为了与艾滋病进行抗击的勇士,医生、患者、媒体,鄙视那些为了名利而追逐的人。细想那些在疾病面前还想着争名夺利的人,有一点能理解,生活在人类社会中,要名垂千史,要在慢慢场合中留下一点闪光之处,让后人记住自己,证明自己存在过,但是过分的自私自利,也是让人唾弃。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为人类的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大多数是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工作、赚钱,恰逢中国在告诉发展的时期,对于功利的追逐尤其明显。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在想,像这样的自私自利的存活有什么意义,当自己去世之时,自己存在过吗?同时又在想经济学讲过----自私即公益!我们每一个人在为自利角逐整个社会就会良好的运转、社会效率是最大的,假如每个人都为了他人着想,整个社会是无法运转的就会乱套,我自私也是在客观上为整个社会的最大福利化做贡献。
但是当有机会出于公益而做一些事情、并真正为他人做出实际的效果,那是令人敬佩的!所以敬佩那些品格高尚的人!记得影片中有一位官员说:我不想我的墓志铭上写着--一位官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