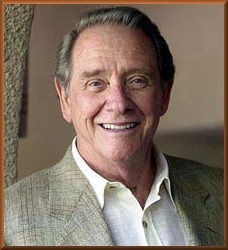大黎明 Un flic(1972)
简介:
- 以下转摘自:
演员:
影评:
- 先声明:梅尔维尔的电影我全都闭着眼睛打五星,阿兰·德龙的电影我全都闭着眼睛打五星。再加上抢店教学片类的,只恨不能再加几颗星。
晚上抽风看完了Borsalino,却忍不住跑来写很久以前看过的大黎明的影评,因为看见阿兰·德龙就会想起梅尔维尔,想起梅尔维尔,不可能不想起大黎明。
不想透太多情节,主要讲讲感受,再说透梅尔维尔的情节也实在太累。看梅尔维尔的电影第一遍总觉得有点吃力,有时候是因为Alain Delon的美貌牵扯太多精力,没有Delon的时候一般就是因为思维太缜密,细节很少直接交代,往往要第二遍仔细琢磨才能初探门道。梅尔维尔很厉害的一点(有时候也是最让人恼火的一点)就在于不交代清楚。这么说也不太精确,因为他确实把所有细节都摆在你面前了,但是你有没有把先后情节串起来,观察够不够仔细,看没看懂这些高智商手法,就另说了。导演非常不担心也不纠结于观众一定思路清晰。比如女主角突然出现在杀人灭口的队伍中用一支空针管解决了目标,比如男主虚虚实实诈出对手的一通电话确定了对方的地理位置。我本来就急性子容易漏细节,还非爱看这类题材,第一次看的时候都实力蒙圈,理清思路之后又深深沉醉于这一魅力不能自拔。
但是这部片子最触动我的是一些感性的因素。更确切地说,是通篇扩散的那种透明的浅蓝色。
首先在《独行杀手》遇见梅尔维尔的冰蓝色,当时被冻得不轻。当时看《大黎明》的时候就是冲着大师遗作的名头去的。电影刚刚开始,为了暴烈的海风中扑面而来的透明蓝,居然给人一种温润之感,我就只能感叹一句:梅尔维尔!从色调上明显有别于《独行杀手》极具入侵效果的浓重的蓝色,《大黎明》的色彩效果只能说是沁人心脾。同样是老练,阿兰·德龙的警官和当年的独行杀手在气质上也有着微妙的区别,一个稳重老辣,一个凛冽逼人。大黎明的情节和节奏整个也温柔得多,但是暗潮汹涌。个人在其中相当欣赏的一段是劫犯在家中的戏份,失业之后铤而走险抢劫银行,却从不敢告诉老妻真相,只推说自己有找新工作的希望,最后事情败露绝望之余吞枪自杀。男主推门看见对方手中拿枪时的那个镜头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梅尔维尔平平淡淡不渲染不煽情却让人拍案叫好的手法。还有熟悉的梅尔维尔式忧伤,男主和最终的对手(也是好友)对峙时平淡的一句警告,对方做了一个掏枪的动作并被击毙其实却并没有武器。男主看清女主的真相之后,最后和搭档在车里长长的沉默。阿兰·德龙常有的面无表情,恍若梦中,而搭档的复杂心情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仿佛替他做了表情。角色从来不表现悲伤,因为悲伤全给了观众了。
有我个人感情因素问题,但是《大黎明》真的是一部让我何时想起都倍感触动的电影,因为温柔而又冷漠的叙事,因为温暖又残忍的透明蓝。褪去了锐气和锋芒的梅尔维尔元素,原来可以这么动人,可以让人在最后一行字幕消失之后,比电影里的Alain Delon沉默更久。有时候我会拿这部片子开玩笑,梅尔维尔在最后一刻,终于给了阿兰·德龙一条生路。走向红圈的独行杀手,在最后一刻迎来大黎明。 【剧透注意】
这部电影有一个奇怪的中译名:首先,它的法语原名Un Flic意为“一名警察”,英文一般也翻译为A Cop或者Dirty Money,实在是看不出来和黎明有什么关系;其次,这部电影本身在梅尔维尔的电影生涯中所处的位置,无论是从他本人的创作历程(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电影)的角度,还是从由阿兰.德龙主演的有着三部曲式的微妙关联的三部犯罪片(这也是其中的最后一部)的角度来看,影片本身都承载着与“黎明”完全相反的意味。只有一个对这一译名的合理解释,就是它指向的是构成电影的质料结构本身:因为在情节上,这一个事件序列中每一事件的开端和发展都在黄昏和夜晚进行,而结局如何就只能等到次日白天才能揭晓,无论是两场关键性的抢劫还是人物之间的见面和联络,都基本上遵循这一规律,而影片情节上真正的结束,即警察开枪杀死劫匪,也正发生于黎明,因此“黎明”在这部电影中有着“结局”的意义外延;而在形式上,这部电影的摄影由参与拍摄《影子部队》的沃尔特.沃蒂兹掌镜,画面依然沿袭了《影子部队》中的冷灰色调,在幽闭性的室内场景采用具有压迫感的低调照明和高对比硬光,然而跟《影子部队》相比,这部电影很明显在各个层次上都极端了许多,其中最明显也是最一以贯之的极端便是笼罩着整部电影的雾蒙蒙的灰蓝色。由于无论清晨、正午还是夜晚,它们的色调都是统一的,因此除了能够根据天有没有黑看出是白天还是黑夜之外我们无法根据这种色彩判断影片中的具体时间,只能从情节中人物对话或一些时间的提示判断出这是什么时候,再加上电影的情节主体大多是在夜晚进行:开头的抢劫开始于银行即将下班的黄昏,然后随着逃亡的进行,时间进入黑夜;随后,无论是克里纳饰演的劫匪西蒙杀死受伤的同伙,火车偷窃的那著名的二十分钟,还是科尔曼那一连串对真实警察日常活动的仿真的走访调查,与线人在街头碰面,以及最后对参与抢劫的失业银行职员的追捕,都是在夜晚进行。因此,白天在这里既是黄昏,也是黎明,你无法辨别二者的区别,而每一次日出过后,时间又会随着情节发展向夜晚疾驰而去。因此,综合来看,称这部电影为《大黎明》,实际上是用一种隐喻和自我映射的方式告诉观众,这部电影具备一种对衔尾蛇一般的虚无主题的追求,“黎明”则是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头,最终也会被自己吞食。
毫无疑问,这不是梅尔维尔的影片之中最出色的一部,当年的票房和评价口碑都相当惨淡。从商业上讲,它很难满足那些冲着诸如三位主演这样的大明星来观看影片的观众,毕竟就连德龙本人也只是在第一个关键情节基本上已经结束的时候才真正出现在故事里(排除电影第三分钟时镜头掠过坐在汽车里的他的特写,但这里似乎只是提醒一下大家刚刚的旁白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而这短短的几秒钟和剩下的与其构成平行剪辑的银行抢劫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而凯瑟琳.德纳芙这样的大咖在影片中也仅仅是一个符号般的配角,作为两个男人之间微妙关系的催化剂存在——这也是梅尔维尔经常被诟病的一点:他并不擅长塑造处在一般异性恋男女关系场域中的女性角色,而且似乎也没打算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拍摄过女性为主角的影片,例如《莱昂莫汉神父》,也塑造过强硬且独立的女性角色,例如《影子部队》中的马蒂尔达,然而《莱昂莫汉神父》中男女双方的情感发展是基于女主角与她的欲望对象神父之间思想上的交锋发展的,而《影子部队》中的马蒂尔达又处在战时那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下。在他的其他影片,尤其是犯罪片中,女性角色的活动大部分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并且扮演着被动和符号化的角色,有时候甚至完全缺席,例如《红圈》,这无疑会激怒相当一部分女性观众。不过梅尔维尔在采访中倒是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这个缺陷,他说他并不讨厌女人,他只是对她们无从下手。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影片的叙事有一些无法忽视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情节中没有得到站得住脚的表现,比如三位主角相互之间应该是相当亲密的三角关系但影片中他们最多的也不过是无言的交换眼神,根据台词两位男主角之间的关系应该远比他们各自与女主角的关系要亲密得多(面对凯西对于西蒙对她与科尔曼之间的秘密恋情产生怀疑的担忧,科尔曼回答:“他没有怀疑,他一直都知道”),但两人之间甚至几乎没有无第三者参与的对手戏或者更进一步的语言交流和肢体接触,这对于从不吝惜笔墨表现故事中存在的男性情谊的梅尔维尔影片来说是非常奇怪的;另外,它在一些看似没必要的地方也故意用一些重复的镜头把节奏拖得很慢,比如一些跟主剧情没什么联系的警察局审问,镜头在一言不发的所有人的脸上跳来跳去,或者戏剧性的推镜头,从人物胸像或者半身像推近至面部五官的大特写,拉长了特定情节的时间或者仅仅是在感觉上产生了时间变缓或停滞的效果,甚至还自带一种奇怪的滑稽色彩。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难说究竟是谁发明了这样的手法,但我们可以在很多上个世纪末的香港动作电影中看到这样的手法,它一般被用在有强烈情感表达或气氛紧张的时刻,例如即将开始打群架之前,影片会用这种方式展示一下准备动手的人们脸上的表情和瞬时的动态,可能还会配上有些夸张的戏剧性音乐,然后大家就知道这是要打起来了。同样让人觉得有些滑稽的还有很多细节,例如那二十分钟火车盗窃里很明显是玩具模型的火车和直升飞机,从直升飞机降落到火车上后的西蒙在去偷手提箱之前一丝不苟得甚至有些不合理的乔装打扮(他甚至还给自己梳了一个整整齐齐的背头),科尔曼与凯西见面时戴着一副夸张的墨镜,在有着壁画的美术馆外的街景甚至也很明显是画上去的,等等。这对于一部基调相当严肃的电影来说,似乎是挺破坏气氛的。看起来,一切都成了符号与情节的杂耍,以至于达到了一种精神错乱的地步。
然而,当我们回顾这位导演的一生,就会发现《大黎明》依然是一部相当重要的影片。梅尔维尔是个相当叛逆的导演,对主流商业犯罪类型片来说他是叛逆的艺术家,对左派居多的战后法国导演圈子来说他是叛逆的“戴高乐主义者”,甚至连对于已经很叛逆的法国新浪潮本身,梅尔维尔也选择了与它叛逆地分道扬镳。现在,他叛逆的对象又变成了他自己。这部电影有着典型的梅尔维尔配置:警察与罪犯的题材更是梅尔维尔一生所关注的,德龙和保罗.克罗谢这样多次合作的熟悉面孔已经是大家公认的“梅尔维尔式演员”,摄影师也参与过他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影片中表现的犯罪细节依然相当一丝不苟,甚至连德龙开的车都还是和《红圈》里长得差不多的美国车。但随着深入剖析的展开,我们会发现这些典型配置又像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戏仿或反身性的嘲弄:德龙从一个好罪犯变成了一个坏警察;开头的引语字幕依然存在,但引用的内容从《独行杀手》和《红圈》的带着东方色彩的寓言变成了一行明确点题的关于警察的文字;在《红圈》里占据重要地位的男性之间的情谊在这里依旧存在,但被弱化到比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还要难以识别的程度;《红圈》里近似《男人的斗争》和《夜阑人未静》的八分钟实时盗窃戏在火车段落被扩张到了相当过分的二十分钟,而其他情节则被压缩了,例如对迈克尔.康拉德的角色的审问就只用警察局外天色从亮变暗来暗示审问已经完成;梅尔维尔的影片一直以平衡写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矛盾而见长,这部影片中写实本身反而成了一种形式主义;过去一直主张的“拍摄有颜色的黑白片”在这部影片中抵达了一种病态的极致,在灰蓝色的笼罩下电影看起来就像被叠上了蓝色滤镜的黑白片,其他的色彩都被洗刷殆尽。再加上前面提及的滑稽感,我们很难不猜测梅尔维尔制作这样一部电影会不会真的出于一种自嘲的目的。可惜,随着他的去世,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被他带进了坟墓。但观察他以往的电影,很明显,几乎从《第二口气》或《眼线》开始,这种因为过于沉重不得不用黑色幽默加以调剂的虚无主义气质就已经在他的电影里生根发芽,而对他曾经已有的成功影片的自我嘲弄则意味着这种虚无主义已经完全成熟,以至于需要用甚至已经有些滑稽的夸张戏仿来让它看起来没那么具有毁灭性。
或许年过五十的他在愤世嫉俗方面也上了一个大台阶。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和法国解放时期的地下运动之后,相信梅尔维尔已经看透了他所处的这个社群:充满男性的自大、冷漠与无情,还有藏在枪支、黑话与金钱交易背后被虚荣的义气伪装的性关系,女性话语在其中的缺席和不受欢迎。法国的地下犯罪世界对他来说无疑是相当熟悉的,年轻时他甚至还曾亲自结交过许多黑帮成员,也许在这么多年后,他已经看清了,无论是罪犯还是警察,间谍还是军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正如他所说:“警匪片是现代悲剧的唯一形式。”因此,他一直擅长在影片中制造令人同情的强盗和强硬狡猾不招喜欢的警察。在《大黎明》中这种思路得到了一种更新:警察和罪犯被置于近乎平等的位置上,我们在二者的世界来回周转,罪犯的工作不会比警察更没有秩序,而警察的调查工作也不会比犯罪行为更不暴力。最终西蒙被科尔曼杀死并不意味着正义战胜邪恶,它仅仅意味着一群人在这场战斗中赢过了另一群人,究竟是谁站在法律的一边并不重要,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法律属于随着现代性陷入危机也一同行将就木的价值观的一部分(正如影片中那栋扭曲的警察局大楼),而无论警察和罪犯他们都仅仅是在做自己的工作罢了,没有人真的遵从某一个有效力的信条。梅尔维尔的叛逆也正在于此,他不相信这个“有效力的信条”存在,他只相信自己,因此也就能伪装自己游走于各个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是谓“打入敌人内部”。而他的不相信又让他仅仅是对这些有毒的男子气概的存在进行看似宣扬实则暗讽的大肆嘲弄(就像在《大黎明》中,最坦诚最清白的角色反而是那个变装女线人加比,而作为警察的科尔曼却仅在需要她的时候温柔相待给予认可,在不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施以暴力,还轻易夺走了或许在外受尽嘲笑和不理解的加比在他这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自尊,还让她穿得像个男人一点),却从不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在《大黎明》中这种虚无与悲观的态度则完全一展无遗,甚至连《独行杀手》和《红圈》里仅存的作为缓冲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德龙曾经在采访中描述这部电影为一场世界末日之后“死人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好像这些黎明之下空荡荡的昏暗街道才是真正的灵薄狱。这是一个由黑色电影(或许还有西部片)的城市中心主义构建起的古老比喻,我们甚至可以在诸如《守望者》这样的文学作品里看到它。实际上这种比喻在如今不但没有过时,随着我们在这个例外状态中越陷越深它的艺术价值反而变得更加值得发掘。不仅仅是西方,日韩、大陆和港台也出现过许多延续这个传统的影片,例如近几年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和《智齿》,但其中很难出现能够达到哪怕是《大黎明》这样的公认为梅尔维尔最糟糕的作品之一的影片表现出的彻底与纯粹。当然电影作为一种商业需要顾忌的东西太多,从市场到审查都是限制所在,独属于梅尔维尔以及受他影响的一批犯罪类型片作者导演例如斯科塞斯、迈克尔.曼和杜琪峰等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希望终有一天我们还能与这种电影再次相遇——哪怕会是在从它的幻想中变为现实的世界末日的街道上的某个黑暗角落。
- 大概每个喜欢吴宇森和杜琪峰的人都知道他们受梅尔维尔影响之深 传说中纵横四海是为了向这部大黎明致敬 但除了两男一女一正一邪的人物关系 其他真的是一点边都不靠 但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梅尔维尔的手法 台词总是很少 少到打个电话也可以玩沉默 他喜欢用任务和镜头来展现剧情 这样的剧情更紧张也更具有表现力 因为不是向观众灌输而是让观众去观察 影片的小高潮开头部分的银行抢劫和中间的火车偷毒品无一例外的没有台词处理 但也看的人惊心动魄 是其后很多年到现在也很难营造出的紧张气氛 作为教科书也不为过 一贯的雄性情结表现 无论是通知同伙坏消息还是自杀 还有最后两人终于针锋相对 梅尔维尔的黑帮片或者警匪片从来不在乎好人还是坏人 只要你是个爷们 就值得尊敬 他对男性友谊的偏爱导致他的片子对女性和爱情的描写从来都是清淡的 甚至是忽略的 这对无论杜琪峰还是吴宇森的影响都很大 你可以从杜琪峰的太多片子中看出他对老梅的这种思想的致敬 从枪火到放逐 从暗战到暗花 没有正义和邪恶 只有敬意和崇拜 可能这部大黎明的表现还不是最强烈 个人认为老梅最好的是红圈 虽然结局很凄凉 但能触动每个男人的胸怀
梅尔维尔比较喜欢的几个场景在这部片子中也都出现了 火车和高级俱乐部 大概名导演总有那么些癖好给自己的电影加入一些个人印记 就像希区柯克总该露一脸 姜文一定有个姓马的男主角 所以记住 想出名 要有一成不变的怪标记 梅尔维尔从不掩饰对于人工造物的偏好,对此甚至不惜以暴露摄影机的行迹为代价换取让我们看到我们“应”看的一切的机会。无疑,梅尔维尔应被归属到“控制”这一端极,其很清楚自己正在以及即将做些什么,他说:“人们在警察心中激发的情感只有含糊与嘲弄”;这又何尝不是梅尔维尔在观众的眼帘之前试图勾引其出洞的情愫呢?但与此同时,那些人工片场的狂风骤雨,美术馆中用以抹杀景深的人工绘制的背景板,以及近乎称得上是不合时宜的反现实布光法,凡此种种带给作为观者的我们的既清晰又模糊的直接感受即是它们在电影与现实的纽带,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间撕开了一个小口子——只是一个小口子,并没有达到高達直接斩断或者说“摧毁”的地步;就像希区柯克在《群鸟》所做的那样,令人震惊的特效非但没有询唤出一个迷失在影片主角(梅兰妮)中的伪主体,其效果更多是轻而易举地证实了电影所反映的现实的虚假与人工的特性。至少在此,特吕弗对于古典电影的批评“在过去的电影里,当人们在处理开车的桥段时,往往会拿着事先拍好的画面在棚内使用背投的技术.......传统的电影甚至连表面的真实感都做不到......”(《艺术》,1959.4)并不成立,当然也可以说,《大黎明》与《群鸟》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传统,甚至比有些“新浪潮”的现代性更为明显。
先别着急下论断说“导演永远拍的是同一部电影。”;即使与时间间隔仅两年的《红圈》相较,《大黎明》内里的组织结构——它的原子的排列方式,分子的运动速率,简而言之,就是《大黎明》中的整个世界——都在塌缩为更高密度的金属物质的物理进程上更进一步,直接指向场面调度的核心,也是它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清除所有多余的说明与交代、言语与动作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得出那个唯一的结论——梅尔维尔只保留必要的东西。
现在,拍摄已经完成,但直至放映终场我们仍不知道Crenna是如何牵头组织这一犯罪团伙的,他们的先前经历仅存于Delon调查过程中的只言片语里;而对于Delon与他的女友(也是Crenna的情妇)或异装癖的线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样所知甚少。所以与其说梅尔维尔摄制一部警匪片,一部黑色电影,毋宁说梅尔维尔所拍的是一部警匪片的骨架,一次对于警匪片这一类型进行的侧拍,我们必须与它离得够远才可看清它的全貌,因为梅尔维尔只关注那些类型片弃之不用的细节,当Crenna潜入一列行进中的火车时,速度与雾气的共同作用迫使其不得不放慢步伐并转而选择痛苦地匍匐式地前行,不像菲拉德的芳托马斯,Crenna的动作没那么迅捷,利索,也没那么优雅,在临近门前还需要停顿几秒,好像这速度引起的狂风就要淹没其呼吸那样。此时,我想再迟钝的观众都不难辨识出这是现实的阻力在角色身上留下的痕迹,也正是它们赋予《大黎明》生命,让它得以成为“电影”而不是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在拍摄《大黎明》时的梅尔维尔是否脑中会闪过一瞬间维果的《亚特兰大号》,毕竟他们在执导自己这最后一部作品时都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毕竟在疾病侵蚀身体的最后时光中,他们总结,也终结了一种类型,毕竟,还有,我虽然不想写得那么感伤,但我的确在他们的景框中看到了同样的氤氲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