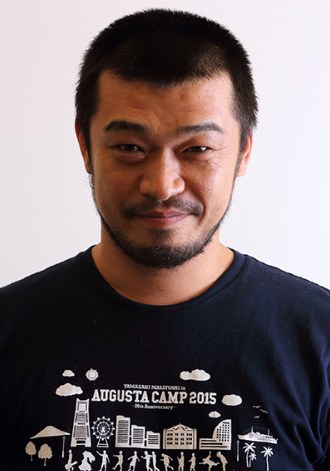永远的托词 永い言い訳(2016)
简介:
- 衣笠幸夫(本木雅弘 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和妻子夏子(深津绘里 饰)结婚多年,感情早已经由最初的炙热走向了平淡。尽管夏子一直以自己的温柔和坦诚包容着幸夫,但幸夫不仅不为所动,甚至以冷漠和粗暴回应,只因为幸夫的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福永(黑木华 饰)。
演员:
影评:

2016.10.24.
HKAFF;百老匯電影中心;
位置在第二排,仰頭看天的造型兩小時。
映后見到了西川美和,對她的了解始源與這一次的電影節。
相信看過的人都會有同樣的感受——是枝裕和的氣味十分濃重。算不是十足的是枝迷,那光和影、鏡頭的切換、以及說故事的速度、最重要是幾個典型意向的表達,都有著是枝的標籤感(以上解讀是個人對是枝裕和的理解,勿噴,多謝!)
劇情方面似乎可以歸檔為:他的改變。
男主角是一名知名的作家,生活體面。牛逼哄哄的樣子。
20年的婚姻下兩人之間的感情已入千呎冰封,沒了過往的羈絆。
只是妻子的驟然離世,生活秩序被打亂。
髒亂的房子。不得不應對的外人。
無處安放的孤單。
老婆尸骨未寒時還想著和情人纏磨。
根本不懂什麼是愛。
根本失去的愛的能力。
此時為了有素材而寫。進入了同樣喪妻的大宮家中。
這兩位喪妻的男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
作為知名作家,參與可笑的祭奠儀式電視拍攝,像個木偶一樣被拍攝內容牽扯著。悼念亡妻=工作,這可笑的定論。在看完妻子那條未發送的簡訊「我已經一點也不愛你了」。加上拍攝需要說句對妻子留下的信息。男主角直接暴走,被助理拖去河邊引發全場大笑。
和失去妻子的大宮只是簡短一句話「希望她回家」相比。
男主角幸夫在露出自己的不堪。
人的心有一天也會突然奔潰 ,這就是人。
人會瘋狂大笑,人會突感悲傷。人無法完完全全明白自己的情感。
他在混亂中,在與大宮一家三口的相處中,抽絲剝繭得理出了自己該面對的事情。
自己很喜歡的意向是1).男主變長變亂的髮型 。2)很討厭的名字_ 幸夫
在場外我向西川美和提問有關這兩個問題中,男主角的改變。
答案中透露著一個關鍵詞語:接受。
全篇最耐人尋味的場景便是最後男主角選擇走進妻子生前經營的理髮店,剪下自己一年多未剪的頭髮。他開始接受了別人的觸碰,與最初不願意他人的接觸到後來,自己主動去改變。
正如他自己寫的不知有多少百分比是真話的稿件:我對我妻子的懷念將持續在我這一生之中。
也是正是印證那句話「逃避越久越痛苦」。
這漫長歲月之後,只有自己獨身一人去贖罪,去面對。
他開始去面對。
當然也包括他非常討厭自己的名字幸夫,但是與他朝夕相處的大宮一家始終以此稱呼他,他也未作解釋也未顯得生氣。
到影片最後他說「別推開給予你愛的人,如果你失去,了也許終一生都不會有人再來愛你了」
這段台詞來此我笨拙的記憶。是男主角講給大宮的長子聽的。
因為幾句較勁的話,兒子差點會失去爸爸。這一句教導是要你明白;母親的離去是不可逆的,對父親的傷害尚可修補。
從這點開始,他已經改變了。
------------------家的意義 -----------------
最近一次進影院看是枝裕和的影片是「比海還深」
阿部寬與本木雅弘同是飾演的作家。前者頹廢找不到出路,以做偵探為生,卻似乎也存不下什麼錢,後者沉浸在名利的快感中,失去了對生命價值的把控。
同所謂喪失,喪失的是生活的快樂。而這個載體同樣來自于一個中心,那邊是:家。家被拆分了。前者是離婚。後者是喪偶。
在本片中,男主角是吃著便利店的飯,蠢得去問便利店員忌廉麵包里是否有蝦和蟹。卡車司機大宮,把二氧化碳和異味搞錯的八嘎,早熟的讀六年級的哥哥,完全不明世事也許還意識不到母親已離世的妹妹。
兩個鰥夫,和一對兄妹。組成的家庭樣式。
而回歸,而明白,而成長,全從家庭里來。
帶著孩子騎單車走過的路,陪著孩子從淘米開始做咖喱飯。
雖然對於這個形式的家已經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家庭,但是互相建立的羈絆,在幫助男主角找尋和找回自己內心低生活的態度,是一個最強大的力量。
生活總是在日復一日中找到陪伴和愛的意義。
------------------西川美和 -----------------
這是個非常值得收藏的細膩女導演。
女人說著一個男人的故事,認定會存在視角上的偏差。
敘事上有女性的柔潤和細膩,是能夠看得出來的。再加上男主角的很多心理活動的窺探。不難得出導演在男主轉變這塊花下的巨大功夫。
導演的回答都很耐心,喜歡她說話慢吞吞的語速,邊思考邊陳述的模樣,很具有魅力。
在現場回答的問題,分別來自演員選角、劇中著一對兄妹的拍攝、自己的拍攝契機和創作動機。
不出意外聽到了關於311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還有對自己新作的底氣和信心。
女導演會格外在意現場的氣氛,這點似乎與以前見過的男性日本導演有所不同。
------------------ 寫在最後 -----------------
想起自己在念中學時候對媽媽發了脾氣衝出家門,連早餐都不願意吃,去到學校覺得完蛋了,老媽一定會大發脾氣。結果媽媽把早餐打包好送到學校,待我回家之後也再也沒提這件事情。記憶中自己和媽媽道了歉,但這愧疚卻始終藏在心裡。那樣被女兒衝著發脾氣的媽媽是怎麼樣原諒我的,始終無法明白。但是媽媽一定很難過,很難過。
所以其實換句話說: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懂事了,都會覺得錯誤已經造成了。
因為愧疚你才懂得,因為懂得你才疼痛。可是如果可以的話,聽一句過來人的勸:別讓懂得來得太晚。
回到影片最後男主角帶著男孩子去找受傷的父親,其實便要教會他
「說重話了,馬上想起來,趕緊道個歉,那也好。起碼你還有這個機會。」
生命的不可逆轉,離去的不可挽回,生的人有著持續一生的痛,離去的人帶有無法挽回的憾。
我們害怕,故而說珍惜。
學不會離去的意義,起碼學會如何生,那便已是足夠了。
以上些許片段,個人不完全的感想,文筆拙劣,作分享和交流。2016年年底时分,影迷大都流连于是枝裕和的新作《比海更深》。深沉的父爱,精明的老母,平淡的讲述……是枝裕和差一点就要复制《步履不停》的巅峰,但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差了一口气。与此同时,观众却忽略了另一部优秀(甚至更优秀)的家庭剧——《永远的托词》。从2003年的处女作到2016年,女导演西川美和一共只拍摄了5部作品,但这五部作品真可谓各有各妙、成色俱佳,本次的《永远的托词》又得到旬报第五的好评,无疑显示出西川相当稳定的水准和极强的实力。
初看《永远的托词》,最让人惊叹的还是影片对人物的刻画。实际上,影片正是改编自西川美和自己入围直木奖的小说作品,因此也承继了小说文字的高超技巧和细腻质感。明线中,生活糜烂的作家衣笠幸夫(本木雅弘饰)在失去妻子之后为寻求心理补偿而帮助他人养育孩子,在此过程中开始重新建立起久违的友情以至亲情。繁复琐碎的情绪充斥其间,但又杂而不乱,让人无比动容。而在暗线里,幸夫经历的数次心理转变被完整地描绘出来,从对妻子的漠视到对亡妻的怨恨,从嫉妒他人到甘于付出,从自责到理解,一个个层次接连呈现,反思和失落则贯穿始终,叙事之巧,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片中种种情感往往意在言外,很多时刻很难用语言表达和形容,故而也为影像表达留出了丰富的空间。西川美和在一些访谈中也提到,自己并不想将电影拍成小说的浓缩版,所以增删了部分段落和情节,以期达到某种平衡。所有这些,无不考验着创作者的调度能力,同时也考验着演员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从成片看,无论是导演西川美和还是曾经在《入殓师》中饰演男主角的本木雅弘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呈现出的,是一个可恨、可爱又可怜的复杂生灵。更进一步来看,《永远的托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每个角色的复杂性和角色间复杂的情感交织。这是该片的过人之处,也是每一部成功家庭剧得以引发普遍思考和共鸣原因。
其实,从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以来,日本一直就是家庭片大国,但目前仍然在世且能在国际上打响名号的日本家庭片导演,无非就是山田洋次和是枝裕和两(代)人。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相较蜚声国际的是枝裕和,西川美和确实没有那么出名,但同为家庭剧创作者,二人却是惺惺相惜,并且长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里所谓师的关系,是指西川美和之所以走上电影制作之路,还端赖在一次电视台面试中被是枝裕和赏识。虽然面试落选,但是枝却邀请她加入《距离》(2001)的剧组,并让她做了自己的助导;两年之后,是枝裕和更是亲任西川美和处女作《蛇草莓》的制片。二人经历相交,题材也显师承,所以西川美和才有了“是枝裕和徒弟”之称。而说到友,是枝和西川每次写完剧本,都会互相寄给对方修改。有趣的是,西川美和在创作《永远的托词》的剧本时恰好收到了是枝裕和寄来的《比海更深》,发现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作家作为影片的主角,而且都在作家和儿童之间建立起复杂而有趣的联系。这固然是一种偶然,但也无疑可以让人管窥他们创作上惊人的一致性和相互影响的成分。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川美和绝不是是枝裕和的“六耳猕猴”。仅就《永远的托词》而言,该片注重的是角色内在的转变和情感的流动,而她的其他影片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和解和趋同的倾向;《比海更深》则延续着是枝电影一直以来展现的家庭成员的固态性格和性格经历间难以相容的对抗性。对于家庭的解体,西川惯于从每个人口中都有可能脱出的谎言(或本片所说的“托词”)介入,而是枝则更注重从性格本身入手描绘个性与血缘之间的张力。
西川之妙,在于她清楚地意识到 “心口不一”作为家庭粘合剂的矛盾属性,而且不管承认与否,这种矛盾便是东方家庭得以维系的内核。这一点在其处女作《蛇草莓》中就显出端倪:西川美和用一种阴冷诡谲、接近森田芳光《家庭游戏》的笔法(西川确实也当过森田芳光的助导,并且显然受到了很大影响)描绘了家人间的种种谎言,但她同时也通过妹妹这一角色暗示,一个不撒谎家庭成员,无论是出于何种考量,都反而会让家庭成员失去与生俱来的信任,从而造成家庭的解体。在其巅峰之作《亲爱的医生》(2009)中,西川美和更是野心勃勃地将这种有关谎言和信任的探讨推广到社群之中:在老龄化程度极高的穷乡僻壤,人们需要的固然是靠谱的真医生,但需要的更是呵护,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亲爱的医生》中有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场景:香川照之饰演的贩药商接受警方调查,被问及冒牌医生(也就是主人公)为何一直在小村庄行医,如果不是为了钱,难道还能是因为爱?贩药商坐着没言语,一翻白眼直接晕倒在地。两位警官见状赶忙将他扶起,贩药商说到,“你们扶我起来是因为爱吗?”
《永远的托词》亦复如是,它是《亲爱的医生》的延续,是西川美和的又一次温柔的阐释。它试图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称作“爱”或“信任”,而是情,是羁绊。只不过,西川美和在本片中选用了一个更加贴切的意象——头发——来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牵连具象化:妻子的职业便是理发师,而妻子的去世让幸夫再也找不到一个人帮他理发。“烦恼丝”的延长,不仅象征着烦恼的绵密,更表征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窘态,直到为妻子所写的“永远的托词”一书出版,幸夫才终于理去长发,留下了真正的思念与回忆。
影片结尾,衣笠幸夫拿出妻子为自己理发用的剪刀。指尖在刀刃上游走,眼神与刀叶反射的光相交,这场景仿佛二人又一次令剧中人心痛、令观众心碎的对望。不过,面对逐渐远去的死亡,幸夫迎来的,或许会是一轮新生。
(文/杨时旸)
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或者某种强大的外力迫使,他们会终其一生处于一种自我营造出的假象之中,并且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那种假象像是一种惯性,维系着这些人的虚荣,也铸就着他们逃避现实的通道。就如同《永远的托词》中的幸夫,作为一个三流小说家,已经多年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他变得势利又油滑,只依靠着曾经残留的名声,在电视台以嘉宾的身份插科打诨,卖弄小聪明为生。他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和名气重于其他任何一切东西,终日周旋于温柔宽容的太太和年轻的秘密情人之间,自鸣得意。妻子和闺蜜在外出旅行期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幸夫生活的惯性被彻底打破了,而这却让他意外发现了自我救赎的方向。
妻子的亡故,对于幸夫来说是一次难以名状的变化,或许,他都未曾料想到这件事会给自己的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葬礼上,这个男人更在意如何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镜头,如何扮演出一副真诚又标准的鳏夫的悲痛样子,致悼词之后,他在车上,下意识地对着后视镜整理着发梢,导演安排出的这个举重若轻的小动作渗透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残忍,妻子尸骨未寒,他却更加在意自己在镜头中的妆发是否整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幸夫一直处于一种空心化的状态里,他对妻子毫无感情,对情人也毫无感情,至于和后者的关系,与其说是肉欲不如说是逃离,用一具鲜嫩的肉体和对方眼神里的无限崇拜,摆脱自己空洞内心中的可怕回响。他一旦不纵情声色,不注重名声,就不得不与自己的内心对视,然后就会发现自己的逼仄,他拼命打磨外表,重视虚名,不过是为了掩盖内里的腐烂。
当妻子闺蜜的丈夫大宫前来和幸夫打招呼的时候,幸夫不会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和眼前这个粗糙的男人会成为朋友。但这个单身父亲和那个年幼懂事的孩子,却让幸夫一点点感受到内心的变化。
幸夫和大宫像一对尖锐的反义词。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底层劳工,一个在妻子在世时就长久地欺骗对方,一个在对方过世后仍然念念不忘,一个像悉心打磨的瓷器,一个如同从未雕琢过的粗陶,他们的存在,彼此映射和对照,也彼此反讽和矫正。大宫投入人间烟火的蒸腾,所有生活里的小确幸和小困境,他乐在其中也挣扎扑腾,而幸夫和真实生活的关系更像是磁悬浮,既无法投入生活丰沛的细部又无法真的超越一切琐碎。换句话说,他的生活虚假又充满矫饰,与现实关系脆弱。而他与大宫父子俩的交往,成为了他重新进入真实生活的过程。
最初是旁观者,后来是参与者,再之后,一点点变化,变成了大宫家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开始投入了感情,和孩子之间产生情谊,和男人之间也会争吵,这种争吵也是一种真实,相较于他当初在妻子尸骨未寒时整理发梢的自己相比,此时在路边发泄感情的幸夫更加可爱。这个过程,更像是慢慢剥开了一颗外壳坚硬的竹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柔嫩的内核。那些世俗声名、自负与矫情的包装都在真切的人间烟火熏蒸之下,一点点剥离殆尽,这犹如一次意外地提纯,一次代价昂贵地返璞归真,一场未曾预见的精神涤荡。
幸夫其实经受了两次外力的刺激,一次是发现亡妻手机中未曾来得及发出的短信,“我不爱你了,一点也不爱了”,那句话让他明白,看起来没有存在感的妻子对自己的一切其实洞若观火,第二次,则是大宫和儿子面对生活时的努力。前者是刺痛,后者是治愈,这个过程让他得以重整旗鼓。
最后,幸夫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书写和创作,在《永远的托词》中更像是一桩隐喻,它意味着心灵和现实的接通,意味着精神的灵敏度。他曾经陷入虚妄和虚伪,犹如行尸走肉,创作就一度暂停,什么都写不出来,而如今,却变得文思泉涌。与其说它重新获得了灵感,不如说他重新拥有了真实的生活。
作为是枝裕和的嫡传弟子,西川美和不仅从风格上一手继承其师细腻风格,在题材方面也是无限接近,比如今年师徒俩心有灵犀地将男主角定位于“作家”,只不过师傅聚焦于失意落魄的作家,而徒弟则将镜头对准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有趣的是,两位作家在自己笔下的文本真实与当下眼前的现时真实都不约而同地陷入迷失。《比海更深》和《永远的托词》两部影片均获得第29届日刊体育电影大奖四项提名,西川美和这部根据自己直木奖候选小说所改编而成的电影,亦得到是枝企画协助,更烙上浓浓是枝裕和的痕迹。 序幕卡司映现时,深津绘里的名字出现得挺晚,心里还奇怪这么一位大牌怎么卡司位排得那么后面,毕竟这次她与本木雅弘的合作,是继1995年《最高的单恋》之后时隔21年的再度共演,加上本木雅弘也是继《入殓师》后,暌违七年后重返大银幕,相当令人期待。剧情推进一刻钟后,心里大约有数了,如同西川美和酷爱的以死亡、葬礼、失踪或意外为正片引子一样,此番又是将死亡阴影先行笼罩全片。从处女作《蛇草莓》爷爷的葬礼开始,西川美和的惯用手法就是以死亡为分界点,倒叙回忆,贯通未来;《摇摆》以真木阳子不明真相的失足摔下吊桥,引发兄弟间看似牢固的情谊摇晃震荡;《亲爱的医生》则以笑福亭鹤瓶饰演的庸医伊野治失踪为悬疑倒置,众人记忆闪回拼凑出的往事拼图;《卖梦的两人》稍有变奏,不过也是一出异于日常的变故——一场将家产烧为乌有的大火,铺展开故事。深津绘里在平静甚至颇为冷淡地帮作家丈夫津村启剪完发后,就与闺蜜出发旅游了,关于她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摄影机慢慢贴近她的视线,变为主观镜头,望向白茫茫的车窗外,从深津绘里冷而麻木的眼神里,观众很容易被移情,为下文的悲剧有了一点点心理铺垫,甚至我会得出这样一个类似幻想的结论:夏子是否预感到了悲剧? 镜头切到正在偷情的丈夫那边,在凸显衣笠幸夫的行为于性格的目的功能上,能轻而易举达成,但这种大反差的偷懒方法和后面流于说教的桥段一样,往往不能满足观众深层次的情感需求,也让某些资深影迷对套路化的发展失去期待,可能这是西川美和与其师的差异所在。不过是枝裕和近年来也越来越温情化,越来越四平八稳,大波动大幅度的情节走向渐渐少了,《永远的托词》剧本反而有是枝裕和早中期的影子。 从拒绝夏子当众唤他“幸夫”开始,我们心里大约对这个人有了初步定位——虚荣自大,自以为是,无视妻子,忽略过往,功利性强。因此当出轨对象也讨厌起他时,性格的树立及发展已经完成大半,衣笠幸夫被年轻女孩指责“谁都不爱”时,茫然及麻木的神情十分到位,他其实就是一个躲在壳里的可悲自大狂,沉湎于光荣历史的人气作家,已然走上下坡路,编辑诘问他的话令他恼羞成怒,不过他依然十分享受扮演一个“沉浸于失妻之痛”的名人,葬礼上得体的致辞和诚恳的悲伤表情,内心不由对自己万分满意,竟忍不住在网上搜索起评价来。这些虚张声势,到底也抵不过内心发虚,搜索词的逐渐变化体现了幸夫色厉内荏的本质,人物形象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些细节铺设都是典型的西川美和风格。 与其完美公众形象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夏子闺蜜的丈夫——大宫,一个大大咧咧、动辄痛哭的粗鲁男人,性格简单直爽,感情充沛浓烈,阳一代表着衣笠幸夫不远回首的平淡过去,因此幸夫一度拒绝阳一的存在以及单方面闯入其生活的意愿。不过,当幸夫目睹阳一一家乱糟糟的生活时,或许是出于心底残存的一丝温柔,或许是怀着找寻素材的目的,也或许是想打破目前固步自封的状态,更或许是全因连他自己也无法察觉的某种优越感(两处住所的对比),他开始进入大宫阳一和两个孩子的生活。 西川美和在拍摄《摇摆》时曾表示:“兄弟,这仅仅是靠血缘,被连结在一起的两个人的关系,是多么的稀薄和危险。这就是我想要描写的。当然,这种关系也有发展的可能性。我个人的希望,是通过这部影片,能够发现人和人之间心的相连。”这番关于接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宣言可视作她所有作品的宗旨,也是她所有作品的素材灵感源泉。幸夫与男孩真平与女孩小灯之间的关系从不无对立到慢慢融合,通过几组有意思的镜头表现——深夜等候公交车、看动画片、吃饭、骑车上坡等。这个阶段的幸夫在外部行为上似乎有所改观,甚至在和大宫阳一一家去海滩时,幻觉中出现夏子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故意误导观众,仿佛幸夫内心的冰山有所融化,影片基调往“治愈”方向越靠越近,可是观众心里仍有疙瘩,毕竟幸夫至此一滴泪都未流过,即使他已不再爱妻子,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非正常的举动。这个奇怪的细节被两个人捕捉到——一个是夏子生前的理发店同事,质问幸夫“你想过她的生活吗”;另一个是幸夫的助手,池松壮亮的戏份不多,但对剧情有助推力,他不动声色地问幸夫:“老师你还没哭过吧?”。幸夫当然很尴尬,是的,尴尬混合着麻木,以“套中人”的乐观无畏扮演着保姆的新角色,并享受着与“失妻名作家”同样本质的虚荣角色。 如果这么拍下去,影片很快就要滑向平庸的深渊。西川美和抛出了戏剧转折,首先是破坏幸夫和大宫阳一一家以及小灯的老师共处的和睦氛围,西川美和再度运用其剥离生活真相的拿手好戏,在剥掉第一层“功成名就,岁月静好”的皮之后,继续剥第二层“互助即救赎” 的皮,这大概就是平庸导演与好导演之间的区别吧。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不提伤心往事、无视伤疤并未痊愈,而变得温馨美好,心病依然是心病,梗结依然是梗结,小灯生日会上无心的几句话,揭露了每个人其实仍停留在原地,问题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其次是破坏大宫阳一与真平之间貌似相互谅解的父子关系(之前几乎未正面提到),父亲独自沉浸在失去妻子的悲痛之中,却未意识到孩子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折射了妻子还活着时,他作为父亲缺席的事实。再次是继续破坏观众从影片第一幕获得的观感,幸夫从夏子手机里找到了最后一条未发出的信息:“我再也不爱你了,一点也不。”他的壳终于全碎了,所有的假装和扮演像是一出丑陋的滑稽戏,他照见了自己的丑陋和自私,他的无奈和绝望,他的无能和冷酷,以为站在世界巅峰,其实早已跌落谷底;以为可以装作和死亡共生,其实早已行尸走肉;以为人生很长,其实往往来不及告别,而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和死亡较量,已经无法说声“对不起”,这也是他终于撕碎温情面具的决心临界点,也就是他和大宫一家暂时断交的契机。幸夫也终于发现关乎妻子的记忆不仅单薄,而且充满疑窦,关于记忆的自我篡改及不确定性这一特质也是西川美和在历年作品中反复呈现的,如《蛇草莓》中哥哥十分确定找到的蛇草莓,妹妹却从未找到过,如《摇摆》中弟弟对哥哥是否故意杀人的判定,如《亲爱的医生》中村民回溯医生从医经历。你所看到的生活远非生活,你所听说的人生远非人生,记忆会说谎,记忆会欺骗,记忆交织着秘密与谎言,谎言与真实之间存在着暧昧的矛盾。幸夫在回忆的迷宫里再次丧失生活的动力(如果说之前担任保姆,让他至少在表象上拥有“治愈”的可能。),重新堕入毫无意义的生活。 这三个破坏是整部影片的转折点,并逐渐引发影片的高潮,让分崩离析的人物角色们再一次聚拢,彰显剧本的扎实与打磨功夫。大宫阳一由于和儿子争吵心烦意乱,开卡车出了车祸,剧情并未滑向进一步狗血,克制止步于轻伤,重点给到幸夫重新联络上真平,两人一起赶往车祸当地医院,一路上一大一小心结的逐渐解开,让影片的情感逐渐趋于高潮,而阳一和真平的相互谅解,让独自乘新干线回来的幸夫遁入光明,灵感突降,久违的文字重新落于笔端,他写道:“人生,就是他人。”我得承认,这句话非常说教,非常心灵鸡汤。可是我也要承认,真的被结结实实感到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容易理解,但如果是一个将自己隔阂于心灵之外、放逐自己于人伦之外的局外人,他的悲伤,可能要等许久许久才能软化、稀释成触手可及的温度,这种老生常谈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救赎」。那些曾放弃生活的人们,终于在历经误解与释然、落魄与奋起后,拐入意料之外,珍视生的每一刻与死的另一边。 影片的结尾,你尽可以贬之为可预测的鸡汤套路,但又有什么关系?纯净如冬日阳光的手嶌葵版《绿树成荫》,像远处春日汩汩流淌的山泉,将身心涤荡一清。以剪发开场,以剪发收尾,结构合拢,时光走了一圈,即使物是人非,即使谎言与真实继续暧昧继续矛盾,即使我们只能做远望的平行线,我们依然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