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此行(2023)
简介:
- 人这一生怎样才算不虚此行?闻善(胡歌 饰)在平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中寻找着答案。他是一个“掉队”的普通编剧,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改以撰写悼词为生。在与各色普通人的相遇里,闻善慰藉他人、也获得了温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演员:
影评:
《不虚此行》不太像是一部结构完整的现实主义电影,更像是一首浪漫现实主义散文诗,丰满简练的细节里装满了不同类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电影的最大魅力在于,每个观众,都能从这些故事里,窥见自己人生中的身不由己和言不由衷,深深与剧中人物共情。
闻善,名校研究生毕业的编剧,为人木讷,不善言谈,独来独往,在任何场合他都不可能是主角,是自动隐形的社恐人设。从写电影、电视剧的光鲜编剧到无业人口,给去世的人写悼词,这其中的落差与转换,不难想象。胡歌的表演给闻善这一角色的可信性获得了无限的可能。一个不善交际、有点“鼠眉”、不懂变通还高自尊高敏感的人,要想在影视圈里长久立足会是何等艰难。
当然这样的人,往往身上都带着一股子拗劲。即使工作地点换在了殡仪馆,工作内容从造梦人到用文字送人最后一程,他依然有一套坚守的叙事逻辑。写悼词,也不能糊弄,要去了解人,了解去世的这个人,在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多重角色关系里,他是怎么被身边人看待,了解普通人的一生,有多少秘密,又有多少言不由衷和波涛汹涌。
无论是为亲人预约悼词的王先生、万家兄妹,还是为离世网友讨要说法的邵金穗,为同事约写悼词的创业者老陆、为自己预约悼词服务的方阿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委托人,闻善都不是套用万能模板批量化生产悼词而混口饭吃。闻善搜集每个去世者的生前爱好,了解他们与家人、朋友的关系,甚至精细到捋清去世者生前人生轨迹线路图,最后,他比身边所有人更了解和靠近死者,可他们的家人并不关心,他一次都没有成为被邀请的人,出现在逝者告别的葬礼。
看到这,你是不是会问:闻善,打个工,你至于吗?
闻善的工作动机是什么?彷佛已经超越出了他工作内容的本身。
他失去编剧工作俨然很久了,但他没有告诉父母实话,父母眼中的大编剧,实际只是靠接写悼词的散活儿,在北京勉强生活。
朋友为他争取到一份稳定又契合他能力的工作,他又觉得,太稳定的工作不适合。
导师想拉他重拾编剧工作,他委婉拒绝,叹息离开这个圈子很久了。
闻善对剧作,不是没有野心,他一直坚持写观察日记,就连写悼词的工作,都是因为被人批评写剧本没有戏剧张力,所以才找到人世间最具戏剧张力的工作场景,试图理解什么是张力,融入生活,从而完成更好的写作。
闻善对于美好的爱情不是没有向往,那些逐一被删除的甜蜜微信,偷偷咽下的甘肃天水苹果,都带着心动的气息。
闻善不是不想改变自己,那些弱点和格格不入的地方,他比谁都心知肚明。
成为不了的人,以及内心无法触及的理想状态,使其外化了那个想象中的少年,即他笔下的人物小尹。小尹阳光率直,敢爱敢恨,是他的向往之身。
闻善AB面存在的对立和矛盾,是我们当代人的心灵折射,沦陷于普通与特别、平凡与伟大、现实与虚无、现在和未来的相生相克之中,像是漂流在孤岛的船,回不了此岸,又到达不了彼岸,无人渡我,孤独无措。
闻善的难题,已不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于接纳自我的终极命题;他通过不停地了解别人的一生,一些已经不存在的生命,但仍有余温的永恒瞬间,去完成对人生自我价值的体认。
看见归期无定但终有归期的方阿姨,自我定位为癌圈网红,用魔法打败魔法的乐观,活一天就有活一天的精气神和意义。
创业公司老总猝死。当员工们聊起他,一个普通得不像个老板的人,却有着说不完的细节和故事。那些微亮的记忆,让普通和伟大的分界,变得无效和模糊。
《不虚此行》不是商业类型叙事那一挂,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同时角色也比较内敛,矛盾都在心中,需要通过眼神、微表情加以外化。闻善这个角色不好驾驭,内心戏刻画得是一个有定力和内力的演员来驾驭。胡歌个人气质与闻善性格也有着巧妙契合,对这种既疏离又孤独的角色,把握起来恰到好处,不留痕迹。
木心说,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闻善的坚持,其实是在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处境里,探寻生命是什么的答案。而他恍然体悟,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生活,恰恰就就生命本来面目。
这部电影像是给普通人温柔的嘱咐:我与我周旋许久,宁做我,才不虚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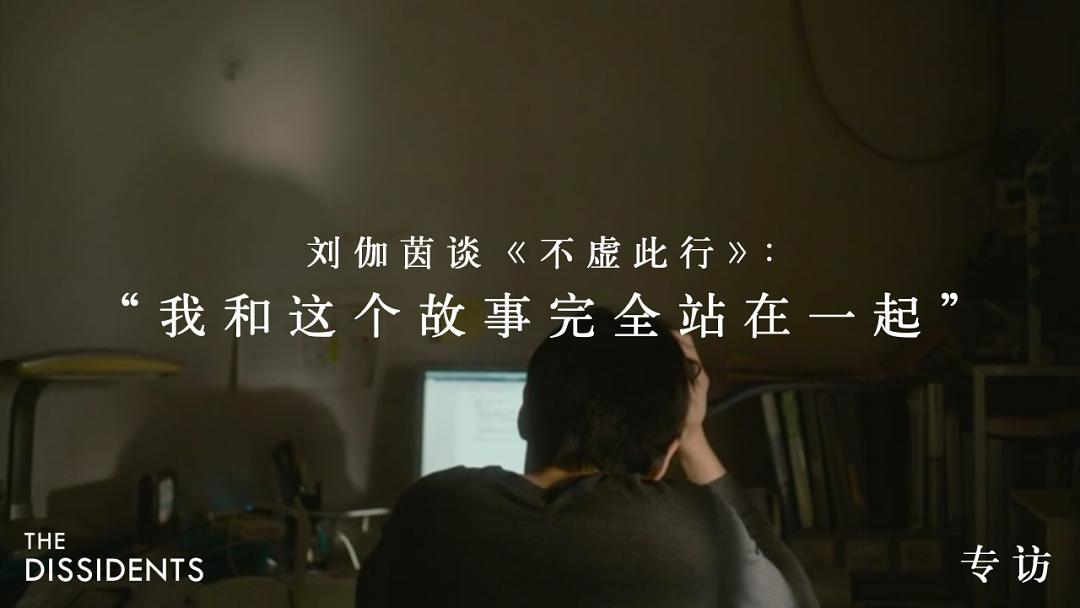
采访 / 异见者编辑部 受访 / 刘伽茵 稿件整理 / &
全文约8800字 阅读需要22分钟
在远离创作十多年后,刘伽茵,这位曾以两部独立电影令世界瞩目的电影作者,以一种谦逊而不失自信的姿态回归了:久违的新作《不虚此行》,一个关于写悼词之人努力与其委托者们建立“真正的交流”的故事,是她首次在常规的制片方式之下完成的作品。如果仅从风格层面来谈论一位作者,那么这部电影的确与理念极其鲜明独特的《牛皮》系列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正如导演本人所深信的那样,尽管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变化是必然的,但也仍有一些东西不曾改变:平视生活,爱自己的人物,不任意简化情感和现实,从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及最重要的,“和故事完全站在一起”,也即,选择与故事本身相符合的表现方式,而不是刻意强调一种高于故事的“个人化”标签。正因为这样的立场,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外显的风格,也能辨认出这就是她的作品。
借着《不虚此行》在内地院线公映的机会,异见者编辑部对刘伽茵导演进行了一次线上专访,她与我们分享了这部新作的创作理念,以及故事和技术上的一些具体细节。
异见者编辑部(以下简称 D ):您的早期作品《牛皮》和《牛皮贰》被广泛视为华语独立电影的里程碑,这两部电影仅由一个三口之家用极其简单的设备拍摄,但其粗粝的风格令人尤其难忘;而您的新片《不虚此行》选择了规模更大、更专业的制作,也采用了相对更为主流的电影手法。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伽茵(以下简称 L ):人处在不同的阶段,要表达的内容和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可能是一种规律,我自己也符合这样的规律。十几年前,我也并不是那么有意识地要用那种方式拍电影;在那个阶段,那样拍对我来说是其实是最恰当的方式,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并不是我被迫选择这样拍,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怎么看我、或者说想要成为做这件事情的人而选择这样拍,而是内外很统一、自洽的选择,特别自然。但回到2004年,很多人觉得你不可以这样拍电影。我拍完了之后,人们仍有可能觉得“这不是电影”。当然对我自己来说,这样的拍摄方式是可以的,所以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就这样去拍了,但是拍完了之后还是会听到一些反馈的声音。我并不拒绝听到其它声音,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干扰。
 牛皮 (2005)
牛皮 (2005)我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的创作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到了这个阶段,我就会想讲一个这样的故事,会想起这样的人,这部电影也比较自然地进入到了一个常规的制作方式中。虽然院线片在时长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这方面肯定与此前的作品有差异,但我在写剧本时完全是为自己创作,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改过这个剧本,这就是我现在的表达。但是这样常规的制作方式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各种工作环节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不过我仍然可以较好地完成这件事,因为除了创作本身的经验,人生所有阶段获得的所有经验都会用在创作上。
D:影片中,许多人物讲述了他们逝去的亲朋好友的故事,其中,齐溪饰演的邵金穗讲述的故事占据了影片结构最关键的位置。可以问一下您为何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全片重心吗?

L:我觉得在一个比较自洽的叙事状态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位置其实基本上是唯一的。邵金穗的这一段故事也几乎是它唯一能发生的地方。另外,邵金穗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其实更容易看到本质。并且邵金穗是一个言语非常快的人,别的人想说什么话之前可能先要想一想,而邵金穗就直接把话说出来了,这对于闻善这样性格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得到一个可以去说出一些话的情境;以前不能讲的事,现在可以讲了。
D:您刚刚提到邵金穗“更容易看到本质”,是否可以理解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讲述者,同时也是一个类似于闻善的观察者、倾听者?
L:是的,对于闻善来说,她是一个倾听者;而闻善又不太容易得到一个被倾听的情境。他这样性格的人很容易被人误解,而他又不爱去解释,所以说话——也就是关于自身的表达——对他来说其实是有风险的。只有邵金穗能给他一个完整的、不带太多成见的被倾听的情境,她让闻善能够不那么小心翼翼。
D:关于邵金穗,我还有一个问题:扮演邵金穗的演员齐溪,其表演方法更偏戏剧化,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似乎有比较大的差别。作为导演,您让这种舞台剧式的表演出现在最终的电影中,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量呢?
L: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在她自己的理解中呈现出来的邵金穗。她是非常生动的,和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每一个演员都会给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带来自己的理解,这是很好的。我不是特别理解你说她与其他人有比较大的差别。
D:您认为他们的表演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L:也不能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在电影里都是融洽的。因为有这样的邵金穗,我们才会看到这样双人关系里的闻善,他们的表演是互动的。对我来说,拍摄现场有着很多在好的演员之间才会有的那种相互影响、那种默契——你进一步、我退一步的默契。我觉得这恰恰是这样两个性格的人在一起时会有的一种感觉:邵金穗进入闻善房间之后,她会支配这个房间,就像这个房间的主子一样,她一屁股坐在了闻善的转椅上。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人会坐在闻善的转椅上。这是一种小小的冒犯,是一种支配。同样,在对话中她也是支配者。但正是这种支配给了闻善表达的自由。稍微有一点冒冒失失的性格反而会让闻善这样的人放松。

D:是的,邵金穗这个角色是带有一种幽默感的。这恰恰也是我们非常喜爱您的作品的一点——它们在悲伤之外总有乐观和幽默的一面。
L:对,潘聪聪也是。
D:《不虚此行》关于死亡的部分平静而沉重,但也有许多让人会心一笑的台词和动作。您的前作《牛皮》也是如此。您是怎样调和电影中的不同情绪,以至于它们明明在质上不一样,但却可以很好地共存?
L:我觉得这些不同的情绪在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那么统一的情绪。统一的情绪是简化的、标签化的,当我们要尽可能快地将它们描述出来、达成共识的时候才会采用:进商场时有着统一的开心,去饭店吃饭时有着统一的兴高采烈……但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比如我参加过的追悼会,大家都到得比较早,在等待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哭、都在难过,我们也会回忆起那些有意思的细节,我们也会笑,这样的笑我觉得是非常温柔和真实的。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被规定必须表现出统一的情绪;只是当我们要描述情绪、要用影像去呈现它时,才采用了统一的方式。

我也一直在写东西,我也写过不一样的东西,不同性质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要求和规定,这也是正常的;如果我去做那样的作品,可能也会选择统一。但对于《不虚此行》,我的态度就是不去统一、不去简化各种情绪,而是真正地表达它们。有了这样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具备把它呈现出来的能力和技术。如果呈现得不好,这样的效果也就没有了。
D:我很好奇您提到的能力和技术是什么,因为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会非常地惊叹,但是又不知道它是怎么生成的。
L:如果只谈剧本,比如对白写得是否到位、对话所发生的情境的选择、道具的使用、主题的传达,把它拆分成一个一个板块来说的话,那么这就是编剧该做的工作。你决定要写的剧本是某种风格,就会在这个风格里面去执行你的叙事。但另一方面,这也确实不完全是技术和经验。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去了解别人的人。电影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我生活中的人;并不是我认识这样的人,或者我采访了这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放进了我的电影。我就是我,我认真生活,这就是我的“采访”,因为所有这些情感和生活方式都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如果我要去写我人生经验以外的东西,那我当然要去做功课,因为我不了解。但是我写的这些,人物们所说的话、人物们的情感,是我了解的,我在写的时候,我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在说他们所说的话。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整个漫长的时间里,我在努力成为一个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人,我也在感受人和人的关系。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也许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D:您说您的电影来源于生活经验,如果用某种术语去描述这样的想法,也许就接近于我们所认为的“自然主义”。您怎么理解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L:《不虚此行》的剧本在气质上是单纯的,但在其它层面并不简单,反而非常复杂。所以它当然是虚构的,也包含很多技术和技巧。我觉得你所说的“自然主义”很难用在这部电影上,因为它涉及到的还是一个选择。我们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真实性、写实性,以及最重要的,平视生活。但是我们在讲故事,是在虚构,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这部电影是一部剧情片,从前到后都在讲故事,不能因为它注重细节,就说它是“自然主义”;细节原本就是要有的。
D:“自然主义”确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能我想说的是,在电影中,现实跟虚构之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它们共同连接在那个被称为“真实”的地方。然后像您提到的细节,我也不会认为它们标识出了所谓的自然主义,而是觉得它们类似于某种触点,通过这些触点,我们能够被拉进一个更广阔的真实之中。
L:我们很难在短暂的时间中对于真实性这样的词汇达成共识。并且,我要反复强调《不虚此行》是一部剧情片,它真的在讲故事,它选择了一个最适合这个故事的呈现方式,而这个呈现方式仍然是剧情片的方式。真实感,是因为之前的每个步骤都做到位了,才会呈现。假如什么都不变,换一个表演方式,或者假如我写的台词没有现在的完成度,还有真实感吗?但这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样做、那样做,它都是剧情片,都是在讲故事。
D:说到讲故事,在贯穿整个故事的现实主义基调中,小尹的出现带来了童话一般的奇幻性。将闻善笔下的角色具象化为一个真人,对此您是出于怎样的用意呢?

L:其实这也是比较现实的。写东西的人和自己笔下的角色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关系。这在别人看来是奇幻的色彩,而对我和闻善来说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D:也就是说,您笔下的角色会像小尹这样真实地出现在您所在的空间中吗?
L:对。生活当中我们也都会和自己对话,没有人觉得和自己对话这个事情很奇怪,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因为我没有觉得它是特别的,而是平常的,所以也没有刻意去强调它。对于写东西的人,这真的不罕见;罕见的可能是我没有故意让它显得特别。
D:作为一部以对话和讲述占据大部分篇幅的电影,《不虚此行》里的中文口语的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分享一下您在写作对白以及指导演员念白方面的经验和理念吗?
L:先说演员念白的部分。在与演员沟通的过程中,大家要对创作的风格、气质达成共识。因为对台词和对白的处理是涵盖在所选择的表演方式里的。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对人物的理解要达成一致,对电影的拍摄风格、审美要达成一致,然后在围读、拍摄时就不会有偏差,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取决于对人物和创作风格的理解。剩下的其实是对每句台词的非常具体的把握:用什么样的语气?用什么样的方式?这里面也包含了技术和技巧,因为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尝试,但这仍然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前提之下。
再说对白的部分。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言,对白就是会占较大的比重。让人物在情境下说出合适的对白,并且让对白完成它的剧作任务,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当然我也喜欢自己写的对白,但我的意思是,这其实不是额外的事,不是锦上添花的部分,而是主体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就是本分。我在写这些对白的时候会代入到人物的位置去想、去写,或者说是用心在写。我之前说了,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很多很多日子里,在很多很多的白天、下午、傍晚、夜里,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你终究是要写好,终究是要找到那句话,“要想声音变老,你得先活到老”,你会找到这个句子的。当然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句话,而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达。所以它也不只是台词,因为台词写作里当然有一些规律和技巧,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更习惯的方式。

D:您此前透露《不虚此行》是完全依据剧本拍摄的,而且这个剧本不是分镜头剧本,是文学本。请问在您的创作中,对影像的构思是在哪一个阶段开始的?
L:写剧本的时候,一些东西其实就已经在里面了。进入到电影的筹备阶段,自然就开始了这部分的工作,和摄影和美术指导去沟通:我们要什么样的画面,以及我们一定不要什么——有时候,不要什么可能更重要。美术和摄影两块工作实现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价值观、审美、风格气质的总体要求之下,大家逐渐能感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的轮廓。我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是不要的,这个部分是沟通中比较关键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工作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剩下的就是需要的。
此外,《不虚此行》的风格不是一个强调自己风格的风格,它比较像闻善的性格,不强调自己的存在感。但它是恰当的。而这一种不引人注目的风格,对于摄影和美术来说其实很难找到支点。强调任何一个部分,都会更容易得到一个支点;但是普通的生活不好找这个支点。“平视生活”不是很容易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能忘记你要去讲故事。但是最终,在所有这些原则之下,还是能够去实现我想要的风格,这其中大量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闻善住的房子是北京的出租屋的样子,这个户型,这个面积,在北京是特别普遍的,要想把它还原和写实要做很多功课。并且,在这是一部剧情片的前提下,是否要去简化、修饰它,换句话说,美化它?比如增加30平米?比如房子不要这么旧?比如家具要新一点?但不是。这就是北京出租屋的样子,屋子里就是有在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各个租客留下来的不成套的东西。

D:您刚才提到了摄影。我们也发现,《不虚此行》主要由固定镜头组成,有一种沉静的氛围;但许多镜头并非完全固定,而是在微微晃动,非常特别。请问这是有意为之吗?
L:这其实是按照闻善的心境来设计的,他比较有安全感时,画面会微微动一下;其它时候则是固定的。这也不是要特别去强调,但我们希望影像和主人公的心境是符合的。
D:所以这有点像主观化的表现。
L:对,是闻善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决定了外在。
D:在《不虚此行》对固定镜头-画外空间的运用中,我们能看见《牛皮》系列的影子,例如开场打断闻善和王先生对话的噪音、餐馆里进进出出的人物,还有闻善打电话时背后走过的北极熊……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L:我对声音比较重视。一些画外的信息量是要通过声音来塑造的。我比较看重这个部分,声音后期做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做声音后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和声音指导在一起,我特别喜欢在棚里做声音。其实我们不想去特别强调这些,但我觉得这样处理会更有质感,更有流动性。这似乎是比较本能的一个选择。北极熊刚好出现在闻善身后这件事情,是一个恩赐,不是我们的安排。我们没有拍很多条,去等北极熊出现在恰当的位置;那天北极熊就是在那儿走动。选择在那个地方拍也不是为了北极熊,而是因为那个长廊是蓝色的,那个空间很像给妈妈打电话时所在的空间。北极熊那天刚好也还没有回去,它一直都在后面走。闻善在前面走,它在后面走,确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我知道北极熊在那儿,但是我并没有想刻意去安排。这是一个很自然地形成的场面调度。
D:这是一种偶然性的馈赠。
L:对,所以也很弥足珍贵。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觉得很美好。
D:电影中的猫也是吗?

L:猫是原本就在剧本里面的。猫是按剧情“出演”的,它出现在电影中的位置和在剧本里出现的位置是一样的,剧情也是一样的。
D:我看了电影的片尾花絮,还以为它也是偶然出现的。
L:确实是偶然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有这只猫,而且它对我们很友好,所以我们不用去外面找一只猫。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只猫,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才有一只猫。它跟剧本是完全一致的。
D:那您最初在剧本里写猫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L:写猫就是因为我喜欢猫,胡歌也喜欢猫,剧本里也有这个余地。而且猫其实是很多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养不养猫。就算不养猫,大家也都在谈论猫,对吧?狗也是一样,但因为我喜欢猫,所以在电影里面就是猫。另外,猫也是小区的一部分,是很多环境的一部分。比如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流浪猫,好多人毕业了之后,怀念学校,怀念校园生活,其中就会包含学校里的流浪猫;很多小区都有流浪猫固定的住处,邻居会在那儿放些吃的东西。所以猫,其实是在一个环境、一个社区中很常见的存在。
D:《牛皮》系列采用宽画幅,机位常停留在手的高度;而《不虚此行》则采用了更窄的画幅,机位普遍更高,在许多外景中我们只看到人物的上半身。这样的改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是如何与您的摄影师合作的?

L:它就是更适合这个故事。不是说因为我想要这样的画幅和机位,才会这样拍;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故事。因为有这个故事,所以会有和故事相匹配的画面,而不是一种标签。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原则性问题。我没有必要放什么个人标签在里面:它就是我的作品,无论如何你都能看出来它是我的作品。这一次选择的风格,是与这个故事、和这个主人公相契合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不是我想要什么风格,而是这个故事想要什么风格。而我和这个故事是完全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的和它想要的不会矛盾。
这个故事的气质和闻善的那种状态就是不适合16:9,我和摄影师在这一点上很早就达成共识;我们要一起去找到适合这个故事的画框。现在这个画幅比,我们是在主场景,也就是在闻善家里决定的。这个画幅会显得比较“老实”,同时也没有那么主流。选择16:9的话有个别画面可能是适配的,但是整体的感觉就不适合了。我们也没有想用很特殊的画幅比,这真的就是在现场找到的,我们试了很多很多种,觉得这种比较接近,刚好是1.55:1。但是你说1.54:1行不行呢?其实也行。但是因为155是我的身高,所以这个画幅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
D:我突然想到,相比于《牛皮》系列,在《不虚此行》里我们更多能看到人物的脸孔,但实际上在看整部电影的过程中,会发现脸孔似乎不是特别重要,反而他们讲的那些话——或者说讲述这个动作——明显更为重要。
L:你其实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重要的是讲述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真正建立联结的过程。闻善试图和别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努力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去了解逝者,同时,他其实也是在了解他所对话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受他的工作方式。这些交流原本并不是真正的交流——如果你去回忆万晓勇、万晓梅、王先生和他对话的方式,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交流,是闻善在让这些成为真正的交流,哪怕非常短暂。闻善真的试图去了解别人,也许这就是他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顺利。但是在交流成为真正的交流的时候——按戴锦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这种真正的交流并不容易,并且很多时候,尤其在工作中、或者在城市生活里,它也被认为是不需要的。但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真正的交流的,它是好的。哪怕只有十分钟,这十分钟是好的,它会让我们的关系不一样。我体会过很多次真正的交流,所以我知道它很重要。

换句话说,讲述与倾听代表了人。人物是不是要给特写?如果没有这样的对话,我就给特写,那这就不会是你现在所看到和喜欢的电影。所以,人与人能建立联结,不是因为我能把你看清楚,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真正的交流。所以,当万晓梅和闻善能互相看见时,他们进行着这样的交流;而最后万晓梅没有看见闻善,但闻善在角落里看见万晓梅,这是真正的交流。万晓梅和她二哥也能有真正的交流。这是生命中特别可贵的事情,你会被这样的事情滋养;它会留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D:您认为交流是人的本质,换言之,人何以为人,其原因正在于交流。您这样的理解,更多是出于个人经验的吗?
L:我可能没有那么主动地去这样想,但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想要去了解别人的人。这是个人经验,但同时它也完全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这样,否则那些交流和沟通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有来有回的,它带给了我力量,对此我心存感激。
D:从《牛皮》到《不虚此行》这一段时间里,您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创作电影呢?
L:首先是,直到这个故事之前,没有那么想讲、想分享的故事。其次就是,你越不拍,你就会离它越远。并且你在生活中已经有了一些其它要做的事,在另外的一个轨道上也有收获和平衡。并不存在说因为我没有在创作,我就没有认真生活,我的生活就黯然失色;我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也做得非常认真。当然,我终究还是要回归创作,但是在人生价值这方面,拍电影和不拍电影,两者其实是平等的。
D: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为《不虚此行》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L: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没有这些感悟,我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毕竟我们都是被自己的经历所塑造的。你多活一天,这样的塑造就会继续,你就会明白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交流,看到更多的东西。在没有拍电影的这十几年里,我就是这样一点点变化了。我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变化,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当然我可能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比较认真。认真是一个我改不掉、也不想去改的一个属性。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在一些时候,认真变成了我人生中的障碍,带给我很多伤害,但我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型的人。而我也仍然会保持着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刻意保持——这种保持和它所带来的接受是一体的。
D:十多年来,您的电影理念相对于当年有着怎样的变化?
L:我不是完全清楚这算不算电影理念的变化,但应该是的。因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从二十多岁变成四十二岁,我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变化,但是所有人都会明白,这里面仍然有不变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有变化,同时又有不变的东西,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部作品。我觉得这两者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好的。
D:您受哪些作品的影响最多呢?
L:我看的东西特别多,我看电影,还看大量的剧集,还有书;更重要的可能是生活。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你。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对它有思考时,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剧集和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平等的。有那么多把故事讲得那么好的剧集,那么优秀的故事和讲故事的人。你会尊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能把故事讲得这么好的人,他们愿意去讲这样的故事。
相关文章
往期推荐


文 / Annihilator
全文约3500字 阅读需要9分钟
刘伽茵,这个凭借两部低成本电影在华语独立电影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名字,如何会与一部由胡歌、吴磊等一众明星演员主演的商业电影联系在一起?在真正观看她的最新作《不虚此行》之前,我们难免会产生上述疑问。
回到2005年,刘伽茵的第一部电影《牛皮》仅凭一台简陋的DV、三个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导演本人)和寥寥几个场景,便确立了一套兼具原创性和完备性的电影方法,足以使人确信这位彼时尚年轻的女导演与拍摄《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时的阿克曼拥有同等天才的创造力。18年过去,《不虚此行》褪去了首作中独属于青年电影人的桀骜不驯的激进性,换上了一层温和、主流的外衣——这难道意味着曾经的创造力也随着形式的更迭而一并消失了吗?绝非如此。《不虚此行》仍然是一部杰作,甚至进一步地说,它是一部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杰作:就像好莱坞制片厂时期那些最伟大的作品(霍克斯,希区柯克,尼古拉斯·雷…)一样,它向我们证明了一位作者的生命力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电影形态中生长,而并不必然地寄生于一个通过长年累月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所建立起的既定范式,这范式在影评人的标准话语中有另一个名字,“风格”。
 牛皮,2005
牛皮,2005刘伽茵迈向主流的选择,与大洋彼岸的另一位导演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产生了奇妙的互文,后者在拍摄了几部令其声名鹊起的激进独立电影之后,同样凭借2011年的《悸动的心》(Restless)回归主流美国电影的范畴——一个笼罩在癌症阴影之下的青少年爱情故事。和《不虚此行》类似的是,《悸动的心》也全然抛却了前作那种挑衅性的极简和即兴的风格,而选择拥抱传统好莱坞式的叙事和手法。但是,正如斯德潘·德罗姆(Stéphane Delorme)在《电影手册》的一篇社论中所言,我们不应以“风格”(le style)、而应以“姿态”(le geste)去定义一位作者——前者仅仅指向作品表面上的共同特征,而后者则关乎一种内在的笔触,它可以描绘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事物,但正是在对不同事物的处理方式的选择中,我们得以窥见某种一以贯之的理念和立场。从“死亡三部曲”到《悸动的心》,是什么姿态在风格的剧变之外延续了下来?对于青春生命的动人描摹(他的镜头下的每一个青少年都仿佛在闪闪发光),对逝去的记忆和时间的追溯,以及最重要的,对于死亡的平静书写。
 Restless, 2011
Restless, 2011《不虚此行》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但刘伽茵的编剧-导演身份为电影创造了一个更加巧妙的切入点,一个独特的、也许多少带有某种自传性质的主人公:独居的中年男人闻善(胡歌 饰),作为曾经的编剧、现今的悼词写作者,他总是背着包、骑着车,在一场接一场与委托人的会面之间奔波。要想写出最合适、最真实的悼词,所面临的挑战便是去了解这些素未谋面、且已经不在人世的陌生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亲朋好友的讲述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它也由此成为了贯穿《不虚此行》全片的核心动作:在公寓、快餐店、出租车、滑雪场,又或者是通过视频通话,人们点上一支烟,回忆的话匣子便自然而然的打开了,关于逝者的故事接二连三地流淌出来……这些故事,有些耳熟得让我们仿佛看见身边人的影子,有些又浮夸得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但当它们平静地在各式各样的嗓音和口音中娓娓道来时,总会有某些瞬间,一股纯粹的情感力量将我们牢牢抓住,故事的主人公也从一个个模糊的身份——父亲、哥哥、老板、朋友——变得逐渐清晰。
 不虚此行,2023
不虚此行,2023闻善是故事的倾听者(英文片名“All Ears”意为“洗耳恭听”);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提问者,一个循循善诱者,一个记忆的侦探——“能不能再说一些细节?”“你很讨厌你大哥吗?”“你觉得他是个普通人吗?”这是因为,无论有意隐瞒还是无意忘记,人们知道的总是比他们讲述的更多,就算是他们已经讲述的,他们也不一定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有时恰恰需要一些尖锐的问题将秘密和情感从话语的泡沫之下揭露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故事不只关于它的主人公,更关于讲述它的人们,这些人因故事主人公的离世而创伤(或者,创伤早在离世之前就开始了,离世仅仅是再次揭开了已有的伤疤),而对故事的讲述则正是对创伤的一种疗愈;和范·桑特一样,刘伽茵试图让电影变得具有启迪意义和布道作用(主流化的另一个体现),于是我们看到《悸动的心》中的男孩在陪伴女孩走向生命终点的旅程中学会了与死亡和解,而《不虚此行》中的人们则在一个个故事的分享、一篇篇悼词的撰写之间向逝者完成了最后的告别。
当然,如果故事单单只有人物的讲述,只可能导致一部依赖于表演和剧本的、充满说教意味的电影;真正赋予《不虚此行》中的一个个故事以生命力的,是导演的讲述,换言之,是导演如何组织人物和事件,如何构想和编排每一个情境,如何进行场面调度——正是这些方面体现出刘伽茵作为一个电影作者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从未动摇。毫无疑问,相较于《牛皮》系列在极限之中肆意炫技的影像,《不虚此行》采用了远为通俗的电影语言进行它的讲述;但是,那些沉静而拒绝操控性的固定镜头,以及每每在场景运转的中途(例如,人物刚刚抛出了一个问题,或做出了一个动作)便将其掐断的剪辑,让我们知道刘伽茵仍与18年前一样,在讲述的语法和讲述的语义之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在闻善第一次拜访王先生家的一镜到底的固定镜头中,二人交谈片刻,妻子回来了,拉开镜头右侧的窗帘,露出几盆稀稀拉拉的绿植,它们是逝者所留下的最后遗物;这难道不正是《牛皮》第二个镜头所奠定的理念吗?镜头始终没有动,但场景却借助精妙的设计将自身层层剥开,露出其最核心的东西——一沓红色的广告纸,或一块白板的背面。
 牛皮,2005
牛皮,2005在这些形式技巧的沿袭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尽管《不虚此行》始终在沉重的基调中前行,但它从未轻易地将自己定义为一部悲伤的电影。同样是在王先生家的场景中,人物们的讲述和询问总是被茶几上的两个手机的消息提示音不合时宜地打断,王先生放下一个,又立刻拿起另一个,对闻善的回答和对微信联系人的训斥几乎不分彼此;就像杜蒙《法兰西》(France)中屡次出现的蓝牙耳机一样,这里有一种雅克·塔蒂式的、关于现代科技的喜剧性。实际上,哪怕是在最为沉重的氛围中,《不虚此行》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制造幽默的时刻;并且,与作为一种商业电影惯例而粗暴插入的笑料不同的是,这些妙语连珠的台词(“我在癌症圈还算半个网红呢……”)和滑稽的人物动作(握手时抽出了错误的手)都来自于对生活的精准观察,它们在电影的情境中浑然一体地生成,构成了对作为影片之底色的死亡的一种超越。这无疑与《牛皮》系列一脉相承,在后者中,逼仄的景别与艰苦的经济条件并不影响一家三口在鸡毛蒜皮中找到生活的乐趣。

不妨说,刘伽茵的作者姿态的核心正是这样一种讲述的语气,它在悲伤与幽默的辩证交织中结构了自身,并最终让电影在沉重与轻盈之间取得一种奇迹般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又是微妙而脆弱的,随时会被打破,并在每个场景、每个情境中重新获得不同的比例。在闻善在动物园给母亲打的一通电话中,语气的平衡抵达了最大的密度:电话这头,闻善——以及作为观众的我们——忍不住开始哭泣;而电话那头,母亲还在说着逗趣的话,“你想回来就回来,还要预约啊”……这样的语气,难道不是一种由爱驱动的语气吗?是刘伽茵对人物的爱促使她从悲伤中发现幽默,从沉重中提炼出轻盈;也正因为同一种爱,使得《不虚此行》所创造的那些极其生动的人物中,尽管没有一个不是对应着某种“典型化”面貌(老领导、宝妈、程序员、配音博主……),但也没有一个因这些面貌自带的讽刺性而变得丑陋;相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可爱之处,哪怕是那个油嘴滑舌的火葬场经理。在当代电影所持有的那些讽刺的语气、漠不关心的语气、剥削的语气之中,我们必须谨慎的甄别、捍卫这种爱的语气,它不一定是杰作的充要条件,但却是我们喜爱许多电影——其中包括刘伽茵截至目前的三部电影——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在所有的逝者和生者之中,最特别的人物无疑是吴磊饰演的那个男孩。他穿着毛衣、戴着针织帽,静悄悄地出现在闻善的出租屋里,偶尔抽一根烟。一切迹象都在向我们暗示他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位面:他的动作和表情像鬼魂一样疏离;当他与闻善对话时,仿佛一个在前者脑内的分身。当那块白板被翻过来时,谜底揭开了:他是闻善在从前的编剧生涯中虚构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小尹”。但是,这个古怪的人物的存在意义绝不仅仅是制造剧作上的悬念和反转,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与结尾“普通人也可以当主角”的主题相呼应;他与《悸动的心》中扮演神风敢死队队员鬼魂的加濑亮一样,是影片的现实表象之下不断涌动升起的一层幻想的泡沫,为电影的语气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同样地,在闻善与母亲的电话的结尾,毫无征兆地,一头北极熊从闻善身后走过;我们立刻察觉到,这是与《牛皮》中窗外驶过的火车一样的神来之笔,它是使情境中的其它一切都黯然失色的最重音,同时又是一个无法被意义之网所捕获的超验的奇点。在这些与电影的现实主义基调完全异质的部分中,刘伽茵和范·桑特共享了同一种姿态,一种从现实中逃逸的渴望。

评分表

相关文章
往期推荐


01
《不虚此行》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的单纯。
很多人用“克制”来形容这部电影,我觉得用“单纯”还要更为准确。它就像是从生活的母体中剥离出来的片段,没有扣人心弦的开始,也没有荡气回肠的结局;它就像是无数偶然发生的小事件的集合,这些事来得突然,去得淡然,不一定都有答案,也不一定不会重来。
这是一部向生活低头的电影,所以它从不敢把生活当作剪辑的素材或是表达的论据,相反,它只能把生活像标本一样,钉在时间的刻度上。
也正因如此,本片的镜头几乎只剩下唯一的角度,那就是平视的、静观的、沉默的、凝滞的,仿佛唯有如此,生活的气味儿才不会被吹远。
02
这种单纯还体现在主题上。《不虚此行》是一部关于创作的电影。
近年来,这类电影特别多。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下创作资源的匮乏,使得创作者只好更多从自身经验出发——这样不仅熟悉,而且安全。
此外,这类电影的特点还在于,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它们要么借创作的艰难,发生活的牢骚;要么就是借由“创作”这样一种特殊的洞察生活的方式,来对现实问题做形而上的思考。

与之相比,《不虚此行》要纯粹得多。表面看,它除了讲创作,还在谈生死。它似乎是在透过一个写悼词的落魄编剧,透过他不断与死亡擦身,与生者相遇的经历,一边感悟生死,一边探讨创作。
但实际上,生死对这部电影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它仅仅作为一种相遇的契机和无常的氛围而存在。导演全片也没有给死者任何一个镜头,她小心翼翼地把死亡排除在观众的视野以外,以此告诉我们,这不是死者的哀乐,而是生者的骊歌。
因为对于生活来说,死亡并不特殊。它不过是一件每个人都必然会经历的事。而与确定无疑的死相比,意外不断的生更值得书写。
于是影片的主题得以进一步收敛,它讲的就是“创作”这件事。具体而言,它探讨的是为谁创作、为何创作的问题。
03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尤其被这一主题触动。
片中胡歌饰演的闻善,因不适应编剧行业的要求,转行帮人写悼词。他无疑陷入到了窘境之中,然而这种窘境却一点也不激烈、不强悍,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人的意志。
影片一直在强调“普通人”这一概念,而真正的普通就在于,连他所遭遇的困境都是那么普通,那么波澜不惊。他没有一个破烂的世界要救,没有一番恢弘的事业要闯,他只是被生活里的一个小坎绊住了。

导演像回避死亡一样,回避了闻善在编剧行业的遭遇,回避了那些被甲方刁难、被客户辱骂的糟心时刻。她借此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创作者的自怜自艾,不是对怀才不遇的慨叹,更不是对行业乱象的抨击。这只是一个人的内心危机,是一个创作者失去了创作的冲动。
所以我们看片中闻善的状态,他并不是被行业打压、被事业拖垮的颓丧态,而是始终处于惆怅和忧虑之间。而他所忧虑之事,其实是自己明明有想要创作的对象,却迟迟无法下笔。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既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身上,使他的每个动作都变得迟缓,又像一个黑洞,总要吸走他的部分注意力,使他时常失神。
在这之中,胡歌采用一种近乎零度表演的方式,使用驼背、慢行、涣散的目光、迟疑的表情以及慢半拍的动作,来表现闻善的自我封闭和潜意识里的自我厌弃。
由此再看闻善的转行,其实更像是一次漫长的拖延。他想要用一件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来抵消那种创作无能的失控感。同时,这件事也自然成了谋生的手段,但并不为赚钱,不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总是严格控制接单频次,主动降低挣钱的效率。他要给自己留出时间,观察生活,面对真正的创作。
只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次漫长的拖延中,救赎意外降临。
04
闻善在帮人写悼词的过程中,遇见了很多人。
通常这样的叙事结构都会把主角当作导游,换言之,主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他来请出其他角色。但《不虚此行》恰恰相反,那些偶然出现的角色,他们的表情、言行、态度,最后都或多或少作用到闻善身上,使他终于重新振作,拿起纸笔。

这又是导演所做的一次减法。她使得众生退到后景,把前景始终留给闻善一人。
至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化学作用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一般电影会给出充分的解释,导演会细心安排每个角色,让他们承担不同的戏剧作用,最后拼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告诉观众,主角就是这么被治愈的。
但《不虚此行》并没有这么做,它刻意模糊了明确的因果关系,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影响,处理成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片中出现的人,他们都面对亲友离世的悲痛,死亡犹如一根针,穿透了所有防备,迫使他们流露真情。
万家兄妹因大哥的死,不得已重新聚到一起,重新面对那份沉重又柔软的亲情;忙于工作、与父亲聚少离多的王先生,内心满是遗憾,但却来不及悲伤,因为还有儿子要照顾,因为在失去儿子身份后,他还要做一个合格的父亲;癌圈网红方阿姨,面对生死仍然谈笑风生,她在用当下最时髦的方式,化解着最古老的命题……
在这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角色,是金穗和那个神秘的猩猩饲养员。
如果说在所有人的生活里,闻善都是个闯入者,那么齐溪饰演的金穗,则是闻善的闯入者。这个大大咧咧、心直口快的女孩,闯到闻善家里,坐在他写作的转椅上,占据他的电脑。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冒犯”,但也恰恰是这种冒犯,这种口无遮拦的追问,让闻善无可回避,必须要面对内心的病因。
而猩猩饲养员的戏份很少,只匆匆露了几面,却极为重要。他每天都呆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而他这样做,不止是出于职业需要,更是因为他喜欢“和动物为伴”这件事本身。

要说这些人的出现,对闻善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其实不在于他们做过什么,也不在于他们是谁,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
这其实才是影片最想表达的,它实际在说,接触、面对面、与真实的人产生连接,这本身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它远比那些附加的意义还要重要。
再考虑到这是一部呈现疫情期间生活的电影,我们或许对此会有更多感触。
05
终于,闻善再一次坐在电脑前,拾起了他延宕已久未能完成的作品。他敲下了第一行字。这时演员胡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仿佛是被石化多年的人,突然察觉到身体内部的某一根神经开启了久违的跳跃。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非常能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对创作者而言,最致命的崩溃瞬间就在于意识到自己的“普通”。我不是天才,我没有迸发不竭的灵感,此时,一张空白的稿纸就成了最凶猛的噩梦。

而“普通”也正是《不虚此行》一直在玩味的概念。这部电影实际就是讲了一间普通的房子里,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一个普通的困境。
而这个困境的破解方法,同样非常普通。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意识到,普通本身就值得被书写,生活的褶皱本来就值得被细细摊开、娓娓记录。那里面不必有惊天动地的戏剧性,不必有全能的盖世英雄,不必有死亡威胁下的奋力一击,不必有生之灿烂、灯火辉煌……那里可以只有一个普通的主角、一段平凡的生活,和一些并不那么美好的世界突然闪动微光的瞬间。
只有肯定了这份普通,生活的回馈才会显现。
我想,这也正是闻善在邂逅了那么多普通人后,突然明白的朴素道理。
终于,经历了这次漫长的拖延,一个创作者复活了。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