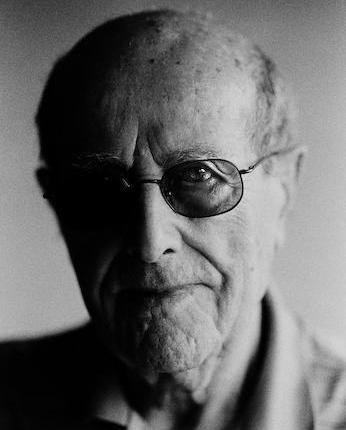里斯本的故事 Lisbon Story(1994)

导演: 维姆·文德斯
编剧: 维姆·文德斯
主演: 吕迪格·福格勒 帕特里克·波查 Vasco Sequeira 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 特蕾莎 萨尔圭罗
上映日期: 1994-12-16(葡萄牙)
片长: 100分钟 IMDb: tt0110361 豆瓣评分:8.3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 Thought was born blind,
But knows what it is seeing.
—— Fernando Pessoa
出于激动,也不知是因为佩索阿还是故事,就对这部电影给了很高的评价。
无疑是为了佩索阿而看的,觊觎了很久这部片子,也终于让我给下下来了。
里斯本的故事,佩索阿就是城市的幽灵,这种意义甚至更甚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基于此,文德斯也没有跳过他,而将他融进了里斯本和整个故事的主题之中。Friedrich的床头摆满了他的诗集,Winter从用佩索阿的诗集来打苍蝇,到每晚裹着床单读它们,任凭苍蝇在周围乱飞,到白天也读它们。最有感觉的一次是Friedrich背着录音机一边走一边读它们。佩索阿的诗句参与了影片的主题,文德斯选取了其中很接近故事情节的一些诗行。但他对于佩索阿的解读,并不那么令人满意,或者对他并不是那么熟悉。比如Winter把佩索阿1934年写的诗和他的死亡联系得太近,而明显在那个时期他写了很多作品;比如Pessoa的意思是Person而不是Nobody,Nobody来自另一个相似的词,由佩索阿的女友给他取的;比如最后Winter劝服Friedrich的时候所引用的他的诗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力度并不强烈。
当然在佩索阿包容性极强的作品中文德斯也肯定能够找到很切合的诗行,来渲染声音的意义。其实在Friedrich试图拍摄自己所无法看见的景象这一行为中,本身就蕴含了很深刻的佩索阿的性质。
里斯本的风景也感染了我。第一次跟着镜头近距离走进这座城市,却发现原来这一切是如此熟悉,佩索阿的幽灵仍然在那儿,或者也在我的心里,看倾斜的石板路,知道他曾每天走过,看街边的小店,知道他肯定常常路过,会去一家酒馆喝他那一直不变的酒,看高处的窗户,知道他曾经在这样一扇窗的后面写作,看那片大海,知道它一定还在他心中。影像中的里斯本老旧,又如油画般美丽,有些安静,又有些无序,典型的阳光照耀下的南欧海边城市,天空到处飘扬着彩色的三角小旗,有着一点早已不在的辉煌的遗迹,人们看似宁静地生活着。文德斯的镜头漂亮极了,关于城市的点滴,人物的特写的老胶片尤为精彩。
这还是一个关于收集声音的故事,无论是那些富有想像力的对特定声音的制造,还是用收声器所“拍摄”下来的城市的各类风情,都让人大开耳戒。片中的六人乐队的演出也很精彩,女声更是美妙,来自葡萄牙民谣乐队Madredeus,在片中非常出彩,因此此片的OST也非常值得一试。
电影在结构上看似随意简单,实则构思得非常精巧。开片几分钟的公路镜头在“公路之王”文德斯的手下完全让人陶醉,虽没看完过他的所有影片,也相信这几分钟的镜头绝对也算他的一个出色之作。镜头在行驶的汽车里跟着车的前窗一起忘着延伸出去的公路,周围不断变换着音乐,广播,从德语到法语,从法语到葡萄牙语,不断地驶进收费站,不断地到达没有更多变化的新地方,然后,镜头才慢慢切转过来,观众才看到了坐在司机座位上的Winter的脸。同样Friedrich的出场更是设足了悬念,在我们一次次以为他就要出现时,他都不在场,只留下自己的房子,影像,继而是声音,在影片进行到最后半段时一个毫无准备的瞬间,他来了,先来的还是读诗的声音,继而背影,直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他就是Friedrich,再后来,才发现影片隐藏到最后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关于艺术真实的主客观性的探讨。
假定里斯本是真实的自然的,用摄像机纪录看到的里斯本是主观中的里斯本,而将摄像机背在后背,纪录自己看不见的景物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Friedrich希望的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摆脱掉自己的动机性,这也是二十世纪许多艺术家尽力达到的一种效果,亦带着一种对主观局限的恐惧。在摆脱主观的聚焦后的影像似乎更为真实,然而这样,不过又陷入另一种主观性之中,摄像镜头不过是你背后的眼睛,同面部的眼睛一样地局限。在无目的的行为本身就蕴含了目的,如同盲人摄影抑或固定镜头的摄影,也都在这一行为本身中赋予了某种期许,因为摄影本身就是一个聚焦的主观的行为,如同绘画,写作。
不过这样一种背后拍摄的尝试本身并不是没有艺术价值,在这样包含了目的性的无目的行为中,主观的客观性行为中,亦已包含了一种艺术观的理解和实验的意义。个人一直对Friedrich所拍摄出来的那些背后的影像颇感兴趣,但文德斯在电影里却没有向我们揭露答案,也因为这个答案在电影中的不可揭露性。它们真的如同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Friedrich不让自己看到,文德斯也不让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种尝试,我在以前就曾有过想法将相机放在自己脑后抓拍,也肯定有好些艺术家们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或许包括文德斯本人。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够体验下这样的作品。而我想象中文德斯的版本,应该是摄像机固定在行驶的汽车的顶部,对着汽车的后面,它不一定有他架着摄像机拍摄时那么美,但也能够一路惊险,将倒退的事物都吸入到逝去的时间中,每分每秒,汽车还飚得够快,就像我们无法挽救的年龄。 - 在明亮的日光下,即使声音也熠熠发光。
-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张印着蔚蓝海景的明信片在镜头前翩然飘落,被逐渐堆积的报纸、信件、杂志淹没。一只手将它从这堆杂物中解救出来。明信片寄自里斯本。这只手的主人是一名音效师,明信片寄自里斯本,导演朋友的邀请他去为其纪录片收音、配音。这是电影《里斯本物语》的开头。然而,电影的前十多分钟却是一部十足的文德斯式公路电影。镜头被放置在车窗前,随着公路水平延伸。白天过去、夜晚来临,公路标牌、汽车旅馆、加油站,只有不断变幻的语言和电台音乐在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在遭遇了种种挫折之后,音效师终于来到里斯本,却不见朋友踪影,于是,电影又开始带上一丝悬疑片的色彩。音效师倒是天性乐观(纵使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的瘸腿),坦然在朋友家住下,晚上观看朋友留下的影像素材,白天就顺着这些线索去街头游荡,“搜寻”相应的声音。导演家的常客,两个对电影十足有兴趣的小朋友则成了他的跟屁虫。音效师还天性浪漫,与导演请来为电影配音的当地女歌者暗生情愫,并不无一厢情愿地说了一些浪漫的傻话。这是电影《里斯本物语》前一个小时的内容。影片从公路片变成了一部风光片,文德斯带领我们跟随音效师的脚步,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漫游、穿行,用半游客半审美家的视角去观察这座城市,去仔细辨听这座城市发出的声音。此时,片中的导演仍未出现。在一个希区柯克式的紧张桥段之后,导演朋友终于在城市的某个偏僻角落被发现。原来,导演正经历一段“创造性危机”,对自己从前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根本的怀疑,转而开始一种“将摄影机背在背上”的拍摄实践。至此,这部为纪念电影诞生百年而拍摄的文德斯影片才终于走向了正题。
如果说《里斯本物语》是一部探讨电影理念,影像真实,影像与声音关系等种种重要电影命题的电影,那么,这一切却是在一种舒缓以至松散的节奏中展开的。影片也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文德斯试图在这部电影中实现的,似乎是通过几种不同风格的影像表现的城市速写,用各种饱含生活之诗的声音细节,用葡萄牙乐队Madredeus的音乐,用生活在上世纪上半页的大诗人佩索阿的诗歌来勾勒里斯本这座城市的艺术形象与气质。通过影像、声音、诗歌和音乐的拼贴,通过它们之间的互文性而形成一种缓慢流动的诗意,将关于电影和艺术的探讨隐于这流动的诗意之后。可以说,这是我看过的文德斯最为轻松、随意、“自然”的电影。在看过两遍之后,我在想,这真的不是一部说教的电影,而是一部要用心去感受的电影。
多重时态的里斯本
里斯本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斑驳的白墙显露出岁月的痕迹,随着山势起伏,红色的屋顶错落有致,连接着蔚蓝的天和海。在地中海明亮的阳光下,天和海都显得更为蔚蓝,清澈,红色的屋顶和青色的石板街道都呈现出更为纯净的色泽。诗人佩索阿在大半个世纪之前曾在贝克萨区的道拉多雷斯就职,每天在里斯本的街头漫游,并写下了许多关于漫游的文字。我想在佩索阿生活之后的年代,拍摄一部关于里斯本的电影,要避开他的诗作,避开他在城市漫游的幽灵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像文德斯这样的导演来说。就像九年前,他怀着同样的朝圣般的心情,去东京寻找小津安二郎的幽灵,拍下了《寻找小津》这部电影。
在《里斯本物语》里,对于里斯本这座城市的呈现是多重的。首先,文德斯带领我们跟随音效师的脚步,以一个游客的视角获取了对这座城市的初步印象。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陡峭的街道和老旧的电车,看到古朴庄严的建筑和连锦起伏的屋顶。这里,画面带有鲜明的文德斯印记,明丽而低饱合度的色彩,制造出清晰的边缘和略带颗粒质感的画面,带来一种干净,清冷的效果。慢慢地我们和音效师一起看到的片中导演用老式手摇摄影机拍出的影像,泛黄的带有历史感的影像。我们看到他拍下水道桥,建筑工人,电车,洗衣的妇女,抱猫的小女孩,食品店,市场和市场里交谈、争吵的人们。这些片断式的泛黄的影像展现了一个宁静、陈旧、破败而诗意的里斯本,一个似乎未经现代性洗礼的欧洲城市。而贯穿这些影像的灵魂,则毫无疑问地是佩索阿那些无时间性的、深沉的诗句。
声音和声音的诗意
既然这是一部以一位音效师为主角的电影,电影重点向我们展示了声音这个在我们向来最容易在观影时被忽视的元素。这部电影仿佛在提醒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声音是多么美妙。在电影中,音效师收集了孩子的叫喊声,歌声,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声音,广场上鸽子成群振翅飞起的声音,电车经过街角的叮当声,磨刀的声音,妇人洗衣服的声音,街旁楼上传来的吉他声和歌声,轮船驶出港口的水声,还有教堂的钟声。当音效师带着耳机闭目聆听收集到的各种不同声响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十分专注和陶醉。此时,他一定在为这市声之美而赞叹不已吧。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时听到的声音,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些声音的包围之中。只是,我们是否对它们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我们是否对这些声音有足够的敏感和开放?比如,我们是否会在广场上鸽子飞起的时候感到一种无名的怅惘?我们会不会在听到二楼小酒馆传来的吉他声时突然驻足,为这些不期而遇的他人的情绪感到美好、伤感?我们是否思索过,港口的水声、教堂的钟声、电车的声音,楼下市集里嘈杂的人声其实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构筑着我们生活的秩序和节奏?我们是否对生活的这些庸常和细微之处怀抱了足够的热情和敬意?诗人和艺术家总是在要求我们要有一双敏感的“发现美”的眼睛,而文德斯或许是在要求我们要具备一对敏锐的“发现美”的耳朵吧。正如佩索阿的诗歌所揭示的那样:“在明亮的阳光下,即使声音也熠熠发光”。
当然,还有音乐。第一次听说Madredeus这个乐队。这个在葡萄牙家喻户晓的乐队,是在《里斯本物语》这部电影上映以后才获得了国际关注。他们的音乐带着弗拉门戈的明快热烈,却又时常透出婉转和沉郁,还有一种与他们的名字(中文翻译为圣母合唱团)相契合的宗教感。影片有一幕尤为动人。音效师与乐队女主唱互生情愫。在屋顶平台上,乐手们面对着一条流过里斯本市区的河,开始奏唱一首关于河流的歌。歌毕,女歌者问音效师,喜欢吗?音效师反问,你说哪个,这条河还是你们的歌?女歌者答:两者都是,因为它们是合为一体的。
不被观看的影像
导演弗雷德里克来到里斯本拍片的初衷,是用古老的拍摄方式,去对抗电影技术高度发展后,电影工业的堕落。因为影像已经成为被随意“出卖”的东西,而不再是对人类生活和心灵的纪录与表达。这当然是个有效的问题,是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工业的强烈谴责。然而,对抗这一潮流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弗雷德里克却对此产生了困惑。他先是试图退回到一种更为原始、朴素拍摄方式,但很快对此失去信心。“举起摄影机就像举起一把枪。每次我将镜头对准被摄物,物体就从我眼前向后退去,消逝。”而他找到的解决方式是:“只有未经人眼观看的影像才是真实、洁净、纯洁(innocent)的影像。是人的观看将影像污染……唯其没有被看,影像和被摄物才能达到浑然的统一。”这些理论,有些是弗雷德里克在摄影机上以“日记”的形式录下的,有些是他和音效师在录影棚里交谈时所做的陈述。我们注意到,在他滔滔不绝地搬出这套理论的时候,音效师一直心不在焉。因为,这个解决方式在他看来是那么可笑,他甚至大笑着从长椅上摔了下去。在留给弗雷德里克的录音里,他对好友这样说:“弗雷德里克,垃圾影像收集大王……回头吧,再次相信你的眼睛吧,它们不在你的背上!相信你的手摇摄影机吧,因为它仍能拍出动人的影像。当你能用心创造出有价值的影像的时候,为什么浪费时间去制造那些垃圾影像呢?……”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段对电影的讨论过分仓促、浅薄,过分轻易地分出了胜负,可是,我们能想像出对片中问题的任何其他的解答方式么?在电影技术高度发展且日益商业化的今天,电影所遭遇的问题不是“人的介入”,而是“人的缺失”,或者说,人的心灵活动的缺失。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将“人”抽离出去,还是将“人”重新召唤回来,答案应该显而易见吧。除了这个“用心”、“用灵魂”去观看、去拍摄的朴素的答案,还有别的办法么?然而对这个问题,文德斯并没有强迫我们去接受他给出的答案。在音效师试图说服导演的那个录音口讯中间,文德斯穿插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段落,将我们带入一种彻底展现电影之美的灵性时空,这也是全片最为动人的一幕——
歌手特里莎回到里斯本,在石阶上与音效师相遇。短暂重逢,聊聊数语,歌手便匆匆离开,去另一个城市录音,并告知音效师,两天之后回来。背景声里隐约有Madredeus的歌声,有孩子们在楼间平台追逐玩耍的声音,轻微的风声。一方明亮的阳光照在孩子们的身上,而女歌手匆匆离去的身影,轻快地没入了光线的暗处。 原文地址:
在明亮的日光下,即使声音也熠熠发光。 ——费尔南多·佩索阿
引用佩索阿的诗歌,在里斯本的阳光下,便成为一种熠熠生辉的声音诗学:维达读懂了佩索阿的诗歌,也读懂了这个世界在心灵的自由创作中拥有了友情和爱情,“电影现在也具有和刚发明时一样的魅力,现在也能让人们行动:你的朋友让我心动了;快来完成电影吧,你的朋友会帮你!”维达呼唤着朋友弗雷德里希,呼唤着用心灵拍摄的电影,呼唤着里斯本街头醒来的诗意,终于这种呼唤让弗雷德里希再次扛起摄像机,再次面带微笑看见阳光听见熠熠生辉的声音,再次用两个人的力量结合影像和声音完成电影:在小巷里,有时有轨列车跟在他们身后,有时他们坐上城市大巴,他们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被看见,他们也被听见,在微笑且用心地投入中,“里斯本的故事”成为最精彩的一部心灵电影,“就像头上长了摄像机。”
头上长了摄像机,就是摄像机和拍摄者、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而弗里德里希被维达叫唤着离开那个“垃圾收集车”,就是离开了一种偏执和逃避——那是缺少了一个轮子的车子,废弃在城市的角落里,弗雷德里希就是在这个缺失了完整性的车子里成为了“垃圾影像收集大王”,这一种告别就是回归自我,就是寻找完整,而其实这一种回归和完整不仅对于弗雷德里希具有新生的意义,维达也在走入里斯本的过程中拥有了心灵的自由,而这一切就是实现了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实现了从孤立到融合的转变,因为头上有摄像机,心里有永远的诗学,感受、创作和体验,从此告别了残缺,告别了盲目,告别了单一。
残缺、盲目和单一,是里斯本没有出现之前的一种生活病。第一个镜头是成堆的照片,是纷乱的信件,是杂错的明信片,它们呈现出的就是一种复数的“一束”,这复数的一束当然会湮没那些有意义的存在,湮没独具特点的个体。这时候一只手慢慢伸了进来,然后寻找,然后发现,然后拿起了一张写给自己的明信片:“维达,快来救我,我需要你,带着音乐器材来里斯本,没有电话和传真,用信件回复我。”这是弗雷德里希从里斯本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里面是呼救,只有将一只手深入到堆放在一起且纷乱的“一束”之中,才能从复数的世界里找到面向自己的信息:这是维达走出的第一步,也是他开始进入“里斯本故事”具有隐喻意义的一个动作。
维达上路了,车上是讲着不同语言的电台,车外是不断变换的风景,从白天到黑夜,从雨天到晴天,从城市到乡村,维达的行程其实也在某种“一束”的湮没中,他不断转动电台但是似乎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信息,各种风景从车外流过,他似乎从来没有用心观赏,在这样的行程中,维达也成为被湮没的存在——在5分25秒之前,甚至镜头里没有出现过正面的维达。这是一种被湮没而带来的残缺,而维达在这段旅程中的遭遇更是一种残缺:他行驶到半路,听到了轮胎爆破的声音,下来检查准备换上备用轮胎的时候,轮胎却不小心掉入了水中;没有水,没有电话,维达被抛入到一种无限的困境中,幸好有一辆中巴经过,上面的人给他的饮料终于让他为汽车加了水,但是继续前行,汽车的一个零件又掉了下来,用来抵达里斯本去拯救朋友的这辆车彻底失去了意义。
没有自由驾驶去往里斯本的车,这是维达旅行中的缺失,就像他受伤的脚一样,在厚重的石膏里,永远无法和另一只脚组合成完整的行走系统。坐上马车、搭乘卡车,维达终于来到了里斯本,终于找到了弗雷德里希的住所,但是当他进去,打开的门,亮着的灯,放着的胶片,似乎证明主人在场,但是这一切变成了某种虚幻:弗雷德里希根本不在,这是一种比残缺更甚的存在,那就是空无——残缺和空无组成了维达里斯本之行的困境,但是,真正的困境在于一种异化的存在:维达一直在等待弗雷德里希“回来”,但是弗雷德里希总是无影无踪;维达看到弗雷德里希拍摄的很多关于里斯本的胶片,看上去是一种在场,但是很多胶片没有声音;维达遇到了那些讲葡萄牙语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杰还是女孩苏菲亚,都拿着摄像机不停对准维达拍摄……
在场却不在场,这就是一种存在的异化,就像维达房间墙上的那句涂鸦的话一样,“啊,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看起来是指向了所有人,是一种丰富,是一个总体,但实际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就像是“一束”信件、照片和明信片一样,就是一种湮没的存在,它无法指向一种具体而真实的存在,它其实意味着残缺,所以他骂不停拍摄的杰是“愚蠢的拍摄傻瓜”,一种完全盲目的拍摄从来不是为了寻找意义。所以在“一束”的世界里,在不在场的异化中,需要的是那只伸进来找到自己需要的手。维达开始看房间里留着的胶片,那些影像没有声音,所以作为拯救者的维达,就需要制造声音:他向那些孩子展示自己拟音的技法,房间了出现了狮子的吼叫,响起了落水的声音,这些声音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维达拿着声音收集话筒,到里斯本大街小巷收集各种声音,它们是孩子们的叫喊声,是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声音,是广场上鸽子觅食飞翔的声音,是电车经过时叮咚的声音,是磨刀老人工作时的声音……这些都是里斯本人们生活中真实的声音,而且维达将这些声音收集来之后,开始为弗雷德里希留下的无声胶片配声——当影像开始发出和自己有关的声音,那些影像便开始活了。
维达收集声音,为影像寻找声音,这是一种拯救,但是在弗雷德里希并未真正在场的时候,这些声音的出现其实只是在技术层面完成了电影,甚至因为它们的真实,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失去了艺术之美,就像维达在夜间读诗的时候听到蚊子嗡嗡叫的声音,他只能用手上佩索阿的诗集去拍打蚊子,“啪”的一声,蚊子死了,嗡嗡声不见了,但消灭蚊子声音时诗集和墙之间的碰撞声也永远不是诗集中所说的那种熠熠生辉的声音。所以,维达寻找、发现和体验到的声音,只是声音最原始、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呈现,它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永远无法上升到艺术的自由。而这正是弗雷德里希不在场的一个原因,他留下了影像,这是他所谓的“实验影像”,“我是个失败者,我不想回家,我要融入这个城市,看见城市的一切,拍摄城市的一切……”弗雷德里希不想回家,是因为他要在街头寻找意义,而他制造的实验影像就是每天背着摄像机,完全以盲拍的方式记录里斯本的一切,这是一种自动拍摄,在弗雷德里希看来,自动拍摄就是真实拍摄,就是在找回电影失去的那部分。
维达收集的各种声音,和弗雷德里希自动拍摄的影像,都是在捕捉自然,不管是声音和影像,都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行动的一个意义是为了反抗电影的资本化和商品化,在维达跟踪邻居男孩终于发现自己也成为弗雷德里希自动拍摄的对象,当维达最终找到寄宿在垃圾车上捕捉真实影像的弗雷德里希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告诉他的是:“以前的电影讲述故事,给人们看某些东西,但是现在的故事却是为了卖出电影而被拍摄,一切都变了,影像背叛了世界。”电影不再讲述故事,故事变成了商品,这便是弗雷德里希对于电影的忧患,所以他用纯粹自动拍摄的真实映像来拯救电影,这些影像在他看来是不掺入感知的影像,是不被污染的影像,但是这种行为他又称之为“失败”,是因为他在自动的真实映像里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弗雷德里希在录音中曾经发出的疑问是:“摄像机捕捉了一瞬,用胶卷就能证明这一瞬的永恒?”
自动摄像的实验影像,是达到了真实,是对于自然的一种记录,但是它不是艺术,它无法达到永恒,这是弗雷德里希的困境,也是电影的本体论疑惑。所以在这种困惑中,维达开始了探索和寻找,他从声音的收集入手,是让那些无声的影像获得了声音;他看到了隔壁的乐队,听到了乐队演奏的音乐和那个叫特蕾莎的女孩唱出的歌声;他们还给了他一副望远镜,他看见了远处的湖远处的船,“河流和歌曲是一体的。”特蕾莎说,它们是在缓慢的流动,它们走向更远的未知,那里有友情,有爱情,有冒险——维达开始迷上了他们的音乐和歌声,当乐队开始了外地演出的旅程,维达开始想念他们,而特蕾莎留下的那把特殊的钥匙,并不是为了打开弗雷德里希一直开着的大门,而是打开了维达的心灵之门;而当维达在弗雷德里希的真实影像中陷入关于永恒艺术的疑惑时,特蕾莎回来了,但是她又要马上走了,当她和维达再次挥手告别时,维达才知道自己爱上了特蕾莎,于是他对弗雷德里希说:“电影让人们行动,你的朋友也让我心动。”只有在音乐、歌声以及如河流一样的旅行中,才会拥有真正行动的感觉,这一种心动便是触及了心灵,激发了自由,而声音也在从纯粹自然到心灵自由的过渡中达到了永恒意义。
里斯本有佩索阿的诗歌,佩索阿的诗歌里有“熠熠生辉”的声音,熠熠生辉的声音来自心灵深处,这用心的、诗意的声音和影像,便组合成了具有诗学意义的电影,于是弗雷德里希从垃圾车上下来,告别了自动拍摄的实验,于是维达受伤的脚康复了,在诗歌的感受中,在心灵的触动中,在自由的体验中,完成了关于“里斯本故事”最完整、最动情、最鲜活的文本,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而是“就像头上长了摄像机”。
- 越来越喜欢Wenders了!
也许《德州巴黎》、《柏林苍穹下》中大段大段的独白会让你觉得有些沉闷,但是你却不能不爱《里斯本的故事》!
无处不在的声音,风、走路、磨刀石、鸽子飞过、喷泉、搓洗衣服、教堂敲钟、电车启动......浅近、灵动的短诗,飞扬、婉转的歌声......这些被完完全全地记录在了尽职、坚定、可爱的电影收音师的设备中,也深深印在了看电影的人心中,我从未这样静静的捕捉过生活中的声音。
透过视线的镜头,就被污染了。导演(影片中的导演)放弃了自己原先拍摄的小镇纪录片,就连古老的手摇式摄影机都让他觉得无助,于是他将一部手提摄像机背在背上,任其自由记录。像是在和捡垃圾者抢生意,用随性的脚步记录下垃圾电影。
不知道片中导演的困惑是不是Wenders自己曾有过的困惑,而那明亮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声音正是打开自我之门的钥匙。纪录片似乎只是在捕捉现实而并非记录现实,而纪录片的形式与技巧本身也可能是一些难以觉察的传统惯例,这些惯例与虚构性剧情片的传统惯例相比并不具有更多内在的正当性。正是这些难以明确的“污染”,让人身陷其中,却又不知所措。
影片的结尾,导演(影片中的导演)重新选择了用眼睛捕捉镜头。这不是俗套,而是必然!
正如Wenders所说:故事是不可能表现真实的,而我们又不可能没有故事。
From my blog: